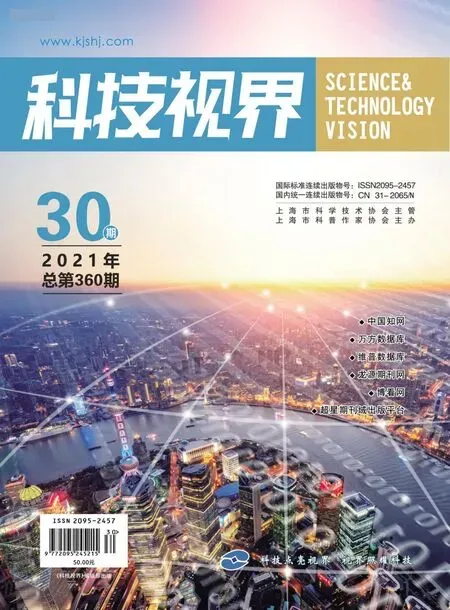民族地區獨立學院創造性建立教學督導機制的理論研究
陳量雄 簡德彬 朱嵐武
(湖南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 湖南 張家界 427000)
獨立學院是我國教育領域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型、獨特的辦學形式。它合理的,有效的開發和利用教育資源,既滿足了日益增長的考生入學需求,又為傳統高校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辦學思路。毫不夸張地說,獨立學院在中國高校發展史上有著特殊的歷史貢獻,而作為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更凸顯著其不可替代的意義:它推動了民族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促進了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繁榮,提升了民族地區的城市品味。調查顯示,不少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已然成為民族地區市民心中的一面旗幟,是城市政治、經濟、文化在精神特色領域的向導。悉尼大學校長Michael Spence曾經指出:“大學應該表現出這樣一種文化姿態,她必然地要影響著所在區域甚至更廣闊區域人群的生存狀態,發展模式和價值取向。”[1]而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理所當然地承載了大學的這一榮耀使命。因此,打造民族地區地區獨立學院的辦學優勢和特色,已經超越了教育本身的意義。
筆者所在課題組曾在《試論獨立院校建立教學督導機制》一文中明確指出:“積極引進和完善建設教學督導機制,無疑是當下民辦高校迅速提升教學質量的有效手段。”[2]然而民族地區外在條件的獨特性也注定了辦在民族地區獨立學院建立教學督導機制的區別性。
1 民族地區獨立學院創造性建立教學督導機制的必然性
民族地區由于地處偏僻,交通閉塞,信息滯后,與發達地區相比,各個方面都相對落后,教育層面自然也是如此。具體表現就是:
首先,民族地區師資力量建設相對困難。根據權威調查數據顯示:在職業規劃中有意向從事高校教師的各類在校生里,“62%的愿意選擇發達地區工作,27%的教師選擇二線城市,只有11%的教師愿意選擇民族地區工作。”[3]以筆者所在獨立學院為例,全院教師平均年齡只有32.9歲,我們不否認年輕教師特有的銳氣與發展潛力,但于教學而言,如此年輕的教師團隊必定缺乏教學經驗。最近幾年還出現了一種狀況,那就是民族地區獨立學院的不少教師積累一定教學經驗后,又通過考研、調動等方式離開了學院。另一方面,民族地區的整體教學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民族地區只有一所本科院校。以湖南省為例,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有兩所,一所是辦在常德的以湖南文理學院為母體學校的芙蓉學院,一所是辦在張家界的以吉首大學為母體學校的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常德也好,張家界也好,其城市教育力量并不強大,教育外部環境的薄弱讓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無法更大發揮高校間的師資共享、交流,更多時候都只能“孤軍奮戰”,其教學督導建立則必然苦難重重了。對比一下,我們更容易看到這種艱巨性,以辦在長沙以湖南師范大學為母體學校的樹達學院為例,其構建教學督導團隊時有非常大的選擇面,母校強大的師資就足以讓其組建一只高水平的教學督導團隊,即便某些專業有所缺失,樹達學院也能從臨近的湖南大學、中南大學選聘專家補充進來。
在對教師的督導方面,民族地區獨立學院沒有優厚的條件,而對學生督導方面,民族地區獨立學院也是苦難重重。獨立學院的專業設置較傳統高校來說靈活性更強,能更敏銳的貼近市場,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熱門專業”,而這些專業往往需要大量的實踐。我國權威教育數據咨詢公司麥可思近日公布了大學就業能力排行榜。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市校合辦的新型高校,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排名前列,超過了很多知名的公辦高校。在全國獨立學院中,其排名更是占得鰲頭。排行榜顯示,在全國非211院校中,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學生就業能力排名第12位,薪資水平居第29位。截至2009年,已有應屆畢業生11643名,其中61%以上留杭工作。[4]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績,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該學院督導在人才培養方案建設時加大了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而江浙一帶良好的經濟條件也為學校的這種育人理念提供了可能。在人才培養方案的宏觀調控下,該院的很多課程都是在實訓中完成講述的,或者教師講授完基本的理論后,就能迅速的按照大綱壓球安排學生走向企業進行實踐鍛煉。這樣的模式充分確保了學生一畢業就能迅速勝任職位,自然也就得到了用人單位的親睞。而民族地區獨立學院所處的城市無法充分滿足學生的實踐需要,在制定人才培養方案時就必然缺少對實訓的考慮。
總之,民族地區的現狀在客觀上制約了辦在民族地區獨立學院的發展,而這種現狀又是在短時間內難以解決的。教學督導的意義無須贅述,這就更需要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結合地域挖掘資源,創造性的搭建教學督導機制。
2 民族地區獨立學院創造性建立教學督導機制的可行性
盡管民族地區在諸多方面都落后于發達地區,但民族地區有著濃厚鮮明的民族風情和地域文化。這為民族地區獨立學院創造性建立教學督導機制提供了巨大的資源。所以民族地區獨立學院理應發揮這種優勢,本著以培養學生通識素養寬厚,專業基礎扎實,職業技能熟練的人才培養定位,加強民族特色文化的涉入與應用,促使學生在面對社會生存問題的解決方式上張弛有度。
因此,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首先要從思想上重視對民族文化的挖掘,在選擇教學督導成員時要有意識的選擇那些既有深厚理論積淀,又有豐富社會實踐,更有數次田野調查,深諳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專家學者,他們能敏銳地捕捉到高校與社會,高校與民族的有效結合點,將民族特色文化納入到人才培養方案中來。筆者所在的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在此就做了具有創新性的嘗試,在民間文學、民間文藝學等教學督導的幫助下,學院大膽開設了才藝課群,其中很多的課程就具有典型的民族性,比如有《桑植民歌》,通過該課程的學習,讓學生至少能獨立演唱十首桑植民歌,這將使學生在求職時掌握一項“獨門秘笈”。比如還開有《大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每周安排相關專家介紹湘西的文化,拓展學生知識視野。日前,學院也正在積極籌建大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通過實體展示,讓學生更深的了解魅力湘西。這系列嘗試的理論邏輯是,讓學生在職場做不了第一,就做唯一,使其培養的學生具有某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這樣的專家學者畢竟是少數,而且這少數的學者還兼有很多社會職務,無法全身心的投入到獨立學院的教學發展和建設上來,這種狀況導致的結果就是獨立學院無法從數量上搭建一個梯隊、結構比較合理的教學督導團隊,因此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還必須開拓思維,創新思路。正如前文所述,獨立學院人才的培養定位是有別于傳統二本和高職、高專的,其培養出來人才的規格既要有一定的理論功底,又要有較強的動手能力。基于這個前提,我們可以把督導選擇的范圍進行更大的拓展,比如,我們可以充分挖掘民族特色,在民間尋找那些具有一技之長的特殊“專家”充實到教學督導中來。比如音樂學專業,我們就可以聘請那些掌握特殊發聲技法的民間藝人前來指導;再比如舞蹈學專業,我們也可以將選擇的目光鎖定在當地民族歌舞團中的佼佼者;還比如旅游管理專業,可以聘請旅游協會的資深人士前來督導等等。當然,在這類督導的選擇構建上,高校要充分發揮其選擇的主導性,既要打破“唯教授論”,又要避免“唯本領論”,而是辯證的看待兩者關系,在充分研究人才培養方案的基礎上有的放矢,這樣的選擇才彰顯深遠意義。在這點上,筆者所在獨立學院的母體學校吉首大學就做得非常成功,該校的音樂學、舞蹈學、體育教育學之所以能成為湖南省重點建設專業就是因為其深深扎根民間,將諸多少數民族元素融入教學體系。民族地區獨立學院更應發揮這一優秀傳統,以彌補教學督導團隊的不足。
第三,民族地區有著奇麗的自然風光,也有著濃郁的民族文化,對諸多一線城市的人來說是旅行的好去處,對諸多學者來說自然也是訪學、采風的不錯選擇。筆者所在獨立學院就處于旅游勝地張家界,據張家界旅游局公布的數據,“2011年,前來張家界觀光的游客達到了350多萬。”[5]在這龐大的旅游人群中不乏知名高校的知名學者。以中文類專家為例,2011年來張旅游的就有華中師范大學邱紫華教授,浙江工商大學、西湖學者吳炫教授,湖南師范大學趙炎秋教授,吉首大學張建永教授等十余位在國內外都頗有影響的頂尖學者。然而,目前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更多的只是安排這些專家進行一次講座,缺乏督導的意義。筆者認為,這也為創造性的構建教學督導團隊提供了可能,比如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在設定督導構成時完全可以預留2—3個流動席位,這個預留席位就是給前來學院所在地旅游觀光的專家。當專家到來后,要充分發揮其前行的指督導意義,除了給學生講座還可以安排其對學院的人才培養方案進行審定,對學院的建設提出思路,安排專家聽獨立學院專職教師的課并給出意見,與青年教師座談等形式各異的活動。所有這些活動將讓督導具體化,而且專家的學術視野能迅速給急需成長的獨立學院教師智性引導。
“感性談生存,理性談發展,最終有特色的生存下去才是最高目標。”[6]辦在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必須在創造性的建設教學督導機制上下功夫,通過督導提升學院辦學品質,打造學院的特色,這樣才能使民族地區獨立學院發展進入良性循環,擁有廣闊的前景,使民族地區的獨立學院在激烈的教育資源競爭中居于不敗之地。
[1]王冀生.大學之道[M].高等教育出版社,P172.
[2]陳量雄.試論獨立學院建立教學督導機制[J].民族論壇,2012(07).
[3]中國教育網絡信息中心.高校畢業生職業選擇統計報告[S].2010,13.
[4]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zucc.edu.cn/index.php?c=index&a=detail&id=6601[OL].
[5]張家界日報[J].2011-12-26:第 3 版.
[6]沙麗娜,張愛軍.構建現代大學精神之我見[J].中國高等教育,2005(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