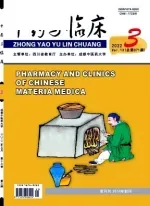非缺陷藥品侵權責任研究
鐘智英,宋民憲
藥品侵權責任應該分為缺陷藥品侵權責任和非缺陷藥品侵權責任,缺陷藥品是指藥品研究、生產、警示等方面對人體存在不合理的危險,本研究中主張為其危險超出合理預期,為照顧習慣仍然稱之為不合理危險。缺陷藥品侵權責任按照《侵權責任法》屬于產品侵權責任,實行嚴格責任。非缺陷藥品侵權責任是指藥品本身沒有缺陷,由于醫務人員或者藥品銷售者的過錯而造成人身損害時的責任。由于對缺陷產品責任研究和案例較多,本文主要討論非缺陷藥品所致人身損害的責任。
對于醫療機構,非缺陷藥品侵權責任屬于醫療侵權范圍,按照《侵權責任法》醫療損害責任中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并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并取得其書面同意。醫務人員未盡到前款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五十五條)。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二)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第五十八條)。非缺陷藥品涉及違反《侵權責任法》規定,造成患者人身損害承擔侵權責任的常見行為有:(一)擅自進行藥物臨床試驗;(二)非為患者利益的改變藥物適應癥、用法用量;(三)沒有依據的聯合用藥;(四)未盡到審慎義務(不良反應、過敏、療效、對藥物的認知程度);(五)其他用藥錯誤。
1 擅自進行藥物臨床試驗
將患者分為治療組、對照組,在隨機盲法等條件下,對一些已經上市的藥品或者自擬藥物處方及制劑進行前瞻性試驗觀察,主要包括了擴大適應癥、擴大適用人群、改變給藥途徑、聯合用藥、聯合治療方法等的療效、安全性觀察,此類藥物臨床研究最為常見,基本上醫藥學術類期刊每期都有文章發表。
一般情況下,患者與所就診醫療機構是一種合同關系,對患者進行藥物臨床研究顯然不是患者和醫療機構之間的要約和承諾,違背此目的,對患者進行藥物臨床研究可以認為是違法和違約行為。如果與患者簽訂藥物臨床試驗知情同意書,則可能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合同,即在充分保障患者權利的基礎上,與受試者簽訂和履行一項民事協議是合法的,雖然試驗結果也可能不一定對患者有益,但是患者自愿為了醫學科學作出貢獻,也應該是法律允許和鼓勵的。但如果沒有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屬同意,則可能構成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權,造成患者人身損害屬于醫療事故,沒有造成人身損害的屬于違約行為,造成人身損害和財產等其他損失的也可以以侵權為由請求賠償。
《執業醫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醫師進行實驗性臨床醫療,應當經醫院批準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屬同意。
《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第四條規定:所有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必須符合《世界醫學大會赫爾辛基宣言》,即公正、尊重人格、力求使受試者最大程度受益和盡可能避免傷害。第三章中規定了受試者的權益保障,其中第八條規定,在藥物臨床試驗的過程中,必須對受試者的個人權益給予充分的保障,并確保試驗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受試者的權益、安全和健康必須高于對科學和社會利益的考慮。倫理委員會與知情同意書是保障受試者權益的主要措施。
《侵權責任法》規定已如前所述。
醫藥期刊發表的對已上市藥品的前瞻性臨床研究文獻,除個別標明履行了審批手續、倫理委員會審查程序、知情告知等外,其他的藥品臨床研究文章不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涉及行政違法、民事違約、違反醫學倫理要求和侵權等法律關系。
2 非為患者利益的改變藥物適應癥、用法用量
2.1 超出藥品標準、藥品說明書標明適應癥、用法用量規定用藥,不一定存在違法或者過錯
規定用法用量、適應癥是《藥品管理法》規定的藥品定義之一,用法用量、適應癥同時又是國家頒布或者批準藥品標準或者藥品說明書的組成內容,是藥品生產、經營者必須遵守的強制性規定,違反者以生產銷售假藥論處是眾所周之的規則。但是,藥品標準或者說明書規定的用法用量、適應癥(以下簡稱為用法)對于醫師即藥品使用者是否是法定的,《藥品管理法》并未明確規定,而臨床不在藥品的規定用法用量、適應癥范圍內使用藥品是常見的現象。例如:抗感染藥用于預防感染,維生素類藥品沒有用于維生素缺乏癥而用于“保健”,根據不同病情在用量范圍外加大或者減少劑量等,類似情況在臨床中幾乎形成常規。
2.2 藥品標準、藥品說明書標明適應癥、用法用量的相對法定性
《中國藥典》一部凡例規定:藥材及制劑的功能與主治系以中醫或民族醫辯證施治的理論和復方配伍用藥經驗為主所作的概括描述,并在臨床實踐的基礎上適當增加了新用途。此項規定僅作為指導用藥的參考。由此可見對于臨床醫師而言,藥品標準規定的用法并非“法定”。對于藥品標準、藥品說明書中的一些錯誤,更不能“法定”,甚至是不能指導的。例如穿心蓮片、金錢草片治療毒蛇咬傷的描述即為錯誤。但是,對于藥品生產企業和經營企業對藥品標準、藥品說明書標明適應癥、用法用量是不能擅自修改的,如需修改必須經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
2.3 超出藥品標準、藥品說明書標明適應癥、用法用量規定用藥是常見的
在藥品說明書之外的用藥情況在世界各國廣泛存在,一般在7.5~40%之間[1],在個別專科用藥中甚至高達90%[2]。藥品說明書之外的用法概念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1982年美國FDA為此發表聲明稱:法律沒有限制醫師如何使用藥品,對于上市后藥品,醫師的治療方案、適應人群可以不在官方批準的藥品說明書之內。但是應該是為了患者利益,根據科學原理、專家意見或者臨床對照試驗獲得的,沒有欺騙行為[3]。其主要原因在于藥品上市前臨床研究是局限的,藥品說明書記載的用法往往滯后于科學發展和臨床實際。FDA鼓勵制藥企業對藥品說明書之外用法進行必要的臨床研究,使之成為新的適應癥,但是推廣藥品說明書之外用法是違法的。藥品說明書之外的用法概念具體含義包括了劑量、適應癥、給藥途徑和適應人群其對應的為不可接受用法、不正確用法、未被驗證用法、違法用法、過時用法等。與我國《藥品管理法》不同是很多國家并不將適應癥和用法用量納入藥品定義,與之對應的藥品標準中并不規定適應癥和用法用量,而是對上市藥品說明書進行審批。對應我國目前藥品管理此種情況應該稱之為藥品標準、說明書之外用藥。
藥品標準、說明書之外用藥在我國同樣廣泛存在,又未被法律正式認可的情況下,如果發生人身傷害,醫療機構或醫師是否應該承擔絕對的責任,其答案不是唯一的。如果是為了患者利益,有必要的科學依據、會診意見、充分的臨床實踐和證據,可以免責,反之應該承擔侵權責任。不是為了患者利益,可以認為藥品使用者知道或者應該知道產生的不良后果。沒有必要和充分依據在藥品標準或說明書之外用藥可以認為對不良后果具有過失,應該承擔相應責任。如將亮菌甲素注射液用于治療重癥肝炎、茵梔黃注射液治療新生兒黃疸,如果沒有依據亦屬于此,當事人可以請求醫療機構承擔侵權責任。
2.4 舉證責任倒置
關于藥品標準說明書外用藥之所以如此廣泛,主要原因在于臨床疾病的復雜性,例如:多種疾病治療時的聯合用藥或者藥物治療和其他治療方法并用,同一疾病不同并發癥時的聯合用藥,罕見的沒有明確治療手段和藥品疾病的用藥,比如“非典”和“禽流感”。那么醫師按照藥品標準說明書用藥,如果出現人身傷害的不良后果是否絕對的免責,回答也不是絕對的,由于不同人種、人群、年齡、體質狀況、并發疾病等,都需要醫師制定特定的用藥方案,所以藥品標準說明書外用藥在我國同樣大量存在,也就是說醫師如果存在過失,仍然應該承擔相應責任。由此看來,醫師在使用藥品時沒有絕對免責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應該在臨床中不斷補充醫學科學知識,研究臨床疾病治療轉歸,積累經驗,并且注意保留包括臨床用藥在內的病例作為證據,說明沒有過錯或者因果關系,否則有可能承擔舉證不能而敗訴的責任。
藥品標準、藥品說明書標明適應癥、用法用量之外用藥可能歸責于過錯責任,但是,過錯的認定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絕對地要求醫師按照說明書用藥不科學、不符合實際。衛生部《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試行)》中只是將無正當理由超說明書用藥列為不合理處方,只要符合“正當性”的理由不被認為違規,這是規范性文件第一次承認超出說明書用藥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3 聯合用藥的風險
醫療機構臨床中多為兩種以上的藥物聯合用藥,這是因為實際需要,臨床患者具體的疾病,既往疾病、伴隨疾病等很難遴選到一一對應的藥物,已有藥物不能滿足臨床治療需要,而臨床兩種以上藥品聯合應用是常見的,在醫療機構接近100%。藥品上市前臨床研究是有限的,大部分藥品的使用經驗積累是在上市以后。絕大部分藥品說明書只是對單獨使用安全性、有效性的說明,并不包括各種聯合用藥的可能,臨床醫師必須按照藥品說明書用藥的局限性觀點應該改變。衛生部《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試行)》中關于聯合用藥并沒有禁止,而是將不合理的聯合用藥分為了不規范和不適宜,關于聯合用藥不合理處方的認定標準是:不規范,單張門診處方超過5種藥品的。用藥不適宜,聯合用藥不適宜的;無正當理由,為同一患者同時開具2種以上藥理作用相同藥物的。結合法律責任和藥品實際,對聯合用藥可能存在的風險作如下分類:
3.1 藥物聯合使用是一個客觀事實
嚴格意義上,針對同一種疾病,使用兩種以上的藥物進行治療稱為聯合用藥,而針對不同疾病的用藥稱為合并用藥。《醫院處方點評管理規范(試行)》未將兩種情況加以區別,故本研究仍然統稱為聯合用藥。藥品說明書中聯合用藥的信息一般反應在藥物相互作用或者禁忌項目之中,大多數藥品說明書這部分信息有限或者直接標明尚不明確。醫師開具處方確定聯合用藥方案一般來說應該是以下目的:增強療效、降低或者減弱不良反應發生率或者程度,另一方面則存在相反的可能,即療效降低,不良反應增加等。醫師在聯合用藥時應該考慮藥品說明書、已有研究報道、專家或者會診意見、用藥經驗等信息,在用藥時間、劑量、療效及不良反應觀察等方面控制更為全面和精細。如果對疾病的一個聯合用藥方案在臨床沒有形成常規,或者沒有充分的依據或者經驗證明是弊大于利的,則所造成的人身損害責任由醫師所在醫療機構承擔。
已批準上市的中西藥、生物制品上萬種,同類藥品多至數百個,上市時間長則上百年,短暫剛剛上市。所以中西藥品、生物制品,新藥、老藥,同類藥品、不同類藥品可能的組合不下萬種,依靠制定聯合用藥的具體規則來規范的設想事實上是不可實現的。因此,聯合用藥所造成的責任風險完全要由醫療機構承擔。當然,醫師可以依靠藥品說明書處方,不超劑量、不超適應癥、避免聯合用藥來規避責任,但是其治療效果一定是有限的。在曾經作過的2次,共300余份醫師問卷調查中,有20%的醫師認為藥品依靠說明書用藥即可,這不得不對醫師的用藥水平擔憂。
3.2 聯合用藥的侵權歸責原則
醫師對患者實施聯合用藥,如果患者受到不應有的損害,應該屬于《侵權責任法》規定醫療損害中醫療技術損害責任,實行過錯責任,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侵權責任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并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并取得其書面同意。對于一些特殊疾病、危重疾病聯合用藥情況占多數,未履行知情告知屬于倫理過錯,適用過錯推定。聯合用藥中的技術過錯值得討論,一般認為,聯合用藥不符合用藥當時的技術水平則為存在過錯。但是技術水平的衡量標準則是隨時間、地域發生變化,可能存在的過錯情況有:1、沒有理由的違反技術指導原則,例如《抗菌藥物臨床用藥指導原則》;2、忽視最新的聯合用藥報道,例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辛伐他汀(包括含辛伐他汀的復方藥)與胺碘酮合用的安全性公告。公告稱,辛伐他汀與治療心律失常藥物胺碘酮合用時有導致罕見的橫紋肌溶解的風險,并可引起腎衰竭或死亡。這種風險的發生幾率與劑量相關,當辛伐他汀日劑量超過20mg時這種風險將增加[4],如果繼續聯合使用則應該承擔責任;3、超出執業范圍,在沒有會診等情況下,開具處方。
3.3 證據歸責
因聯合用藥引起的醫療侵權糾紛舉證責任與一般醫療糾紛相同,仍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4 未盡到審慎義務(不良反應、過敏、療效、對藥物的認知程度)
醫療機構中直接接觸藥品和將藥品用于醫療的醫務人員主要涉及醫師、藥師、護士。孫安修將醫療機構用藥錯誤分為醫師、藥師、護士用藥錯誤[5],分別是:1、藥師過錯:醫療機構制劑配制錯誤;調配錯誤。2、醫師過錯:違反醫療和藥物禁忌使用藥品;劑量不當;療程不當;給藥途徑不當;聯合用藥不當;選用注射溶媒不當;未盡注意患者既往過敏史義務;兒童老人用藥不當;孕婦用藥不當;超過適應癥用藥;醫療記錄中用藥記錄錯誤。3、護士過錯:用藥差錯;操作不當(皮試、注射、給藥速度)。
5 其他用藥錯誤
5.1 虛假藥品廣告的侵權責任
虛假藥品廣告一直是藥品監管治理中的難題,此類研究文章較多,但從侵權責任角度研究者較少。虛假藥品廣告在藥品管理的相關法律上沒有納入假藥或者劣藥的范疇,也未被《侵權責任法》納入侵權產品責任而可以提出侵權賠償請求。與其他產品虛假廣告區別是,其他產品如果不具備其宣傳的虛假功能,在法律上被認定為瑕疵,而不是缺陷產品,而藥品等功能即事關人體安全的產品是否沿用一般產品缺陷、瑕疵的概念少有探討,既然不是假藥行政上處罰有限,刑事上不能治罪,民事上無賠償責任,所以包括藥品在內的虛假廣告禁而不止。
虛假藥品廣告導致人身損害,應該包括延誤病情導致的人身、財產損害,并且可以按照《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藥品生產者、經營者、廣告經營者、醫療機構可能因此承擔連帶責任,而不是一般缺陷產品侵權責任中的不真正連帶責任。
5.2 違反藥品分類管理規定,無處方銷售處方藥
藥品分類管理的目的是避免用藥錯誤、藥物的濫用和誤用、藥物配伍禁忌、藥物的急慢性中毒等,其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做到處方藥在醫師處方情況下,零售藥店方可出售,以有效地加強對處方藥的監督管理,防止消費者因自我行為不當導致濫用、誤用藥物,危及生命健康,消除安全用藥的隱患。但是,該制度實施10年以來,并未真正有效推進,除了沒有解決醫療機構處方流動、醫藥分業等諸多問題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對其中的法律關系進行認真探討。
零售藥店沒有憑處方向患者出售處方藥,如果造成人身損害是否屬于侵權行為。《藥品管理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國家對藥品實行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制度。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其后,《藥品管理法實施條列》第十五條規定,國家實行處方藥和非處方藥分類管理制度。國家根據非處方藥品的安全性,將非處方藥分為甲類非處方藥和乙類非處方藥。經營處方藥、甲類非處方藥的藥品零售企業,應當配備執業藥師或者其他依法經資格認定的藥學技術人員。經營乙類非處方藥的藥品零售企業,應當配備經設區的市級藥品監督管理機構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直接設置的縣級藥品監督管理機構組織考核合格的業務人員。自2001年《藥品管理法》修訂以來,國務院并未制定藥品分類管理辦法,從法理學角度,既然法律明確授權國務院制定的規定,其他部門是無權制定的。除此之外,國務院并未對藥品分類管理作出進一步的規定。所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藥品分類管理的規范性文件是無效的。
零售藥店未憑處方向患者銷售處方藥,造成人身損害的是否應該承擔侵權責任未見到相關研究。如果因處方藥發生人身損害責任承擔原則可能是因患者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按照《侵權責任法》規定,可以減輕零售藥店的賠償責任;如果藥品生產企業直接將處方藥銷售給零售藥店,推定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藥品可能未憑處方銷售,亦存在過錯,應該與銷售者共同相應承擔責任。
非缺陷藥品侵權責任應該按照過錯責任原則歸責,無論是在醫療機構、藥品銷售中非缺陷藥品侵權是一種經常發生的侵權行為,有必要與缺陷藥品侵權責任一樣,進一步地深入研究。
[1]Gazarian M,Kelly M,McPhee JR,et a1.0ff-label use of medicines: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for evaluating appropriateness[J].Med J Aust,2006,185(10):544.
[2]Conroy S,Choonara I,Impicciatore P,et a1.Survey of unlicensed and off label drug use in paediat ric wards in European countries[J].BMI,2000,320(7229):79.
[3]Use of approved drugs for unlabeled indications[J].FDA Drug Bull,1982,12:4.
[4]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 警惕辛伐他汀與胺碘酮聯合使用或高劑量使用增加橫紋肌溶解發生風險[EB/OL].藥品不良反應信息通報,[2010-11].http://www.cdr.gov.cn/xxtb_255/ypblfyxxtb/201011/t20101117_2837.html.
[5]孫安修.用藥糾紛典型案例評析[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