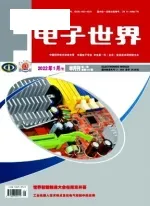數字化時代環境下的圖書館人文精神辨析
山東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 張延賢
21世紀伴隨著世界范圍內以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為特征的數字化革命的興起,人類已經步人了一個高度發展的數字化時代。圖書館也在面臨著數字化時代的沖擊,數字圖書館、復合圖書館、無墻圖書館等新型圖書館紛紛涌現,因此產生了許多新問題與新思考。在由“數字技術”給圖書館帶來的便利的背后,不斷產生技術與圖書館人——圖書館員與讀者之間的困惑與矛盾,僅靠所謂的技術主義、技術理性和技術至上論等,從根本上是無法解決的。因此圖書館界要對這些技術論保有清醒的認識、反思與批判,例如美國著名圖書館學家巴特勒、謝拉和戈曼就是批評技術至上論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認為企圖使技術合理化以及理論技術化的嘗試是不結果實的花朵;謝拉則一再告誡人們:圖書館學始于人文主義[1]。戈曼則借用西班牙畫家戈雅的一副版畫“理性沉睡導致邪惡的產生”來表達web2.0時代理性與秩序的告別,混雜與煩亂的產生[2]。國內也有學者指出:強調人文傳統是圖書館學理論的一個基本點;圖書館學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它的終極價值目標是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等等[3]。反思“數字化時代”圖書館的人文精神狀況——主要是種種失落及重塑,對即使是在數字化時代的迷局中,也要保持對圖書館人文精神的健康發展,就有了一種客觀的必要性。
1.數字化時代的圖書館人文精神
從概念的意義上來考察“數字化”,它最初是通訊和信息網絡運用數據符號,即以0和1組合的比特數據,通過計算機自動的符號處理,把信息、文字、圖像等作為自己的形式,進行信息交流的概括。而今,數字化已經遠遠地超過0和l的比特組合,不再是一種直觀的、靜態的符號意義[4]。而從技術維度界定數字化的概念與影響的范圍,可以說數字化是以發達的網絡技術為基礎而產生的一種管理信息與處理信息的方式。它將各類信息進行了數字化處理,用于計算機的運行體系,從而達到信息的可視化、智能化與網絡化,由此實現從數據到信息、從信息到知識,以及從知識到決策和財富的轉化,并達到信息的共建共享。數字化時代是以數字為中介、載體和體現方式的時代,是以純技術化的物質形態為標志而命名的。數字化時代是數字帝國時代,數字成為交往憑證和必要工具,人與世界通過數字化而日益親近和相互了解[5]。
圖書館的人文精神,在圖書館發展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圖書館文化中,都有不同的內涵。但也有共同的東西,那就是任何時候圖書館人文精神的核心是都是一種人文關懷,人文關懷的對象主要是讀者和用戶,是圖書館和圖書館人求真、求善、求美、求服務、求奉獻,是圖書館注重圖書館員與讀者,讀者與圖書館關系的協調,注重讀者與圖書館員的主體意識的感受等的一種精神追求。圖書館的“人文精神”一詞出現在圖書館專業文獻中,最早見于蔣永福先生的有關論述[6]。而“圖書館人文精神”于1999年由吳唏先生正式提出[7],此后,圖書館人文精神的概念不斷充實、明確,而圖書館人文精神在圖書館的服務工作中,被認作是圖書館的服務宗旨,得到較好的落實和體現。如今,圖書館的人文精神不但已成為圖書館現代化進程中的主要精神之一,成為圖書館數字化時代圖書館和圖書館人的一種重要的思想及精神價值觀,而且還是數字化時代圖書館存在與發展的一種與技術設備相對應的精神支柱。因此數字化時代圖書館的人文精神,不僅要體現對以往圖書館傳統即對圖書館歷史存在的認同,體現對讀者與圖書館員的人文價值和對圖書館未來命運與歸宿的思考與關注,而且要重點反映在圖書館的數字化平臺上,“人——信息——社會”這個大系統中讀者與圖書館員的地位與價值性。
2.數字化時代圖書館人文精神的狀況及分析
2.1 圖書館人的技術依賴與圖書館員的異化
在數字化時代的圖書館,電腦應用技術部分或大部分取代圖書館員的人工操作,導致圖書館尤其是圖書館員對技術的依賴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圖書館界越來越面對著“技術就是圖書館”和“機器就是圖書館員”的挑戰,圖書館員日益淪為電腦、知識、信息、高科技的奴隸。而與此同時圖書館學也過多的依賴上對圖書館的技術性認識,各種“技術至上”的主張紛紛涌現,事實上也是被技術異化了。如有學者指出:圖書館學技術理性的理論邏輯是先驗地認定圖書館學是技術性、應用性、實踐性的學科,把技術理性當作圖書館學與生俱來的基本特征,片面地認為技術性決定了圖書館學的質,技術性是圖書館學的科學性特征,圖書館學是以認識圖書館的技術為任務的[8];如:技術性是圖書館學研究的本質,圖書館學研究就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術性研究[9]。如:在技術理性論者看來理論研究只是曇花一現的“喧囂”,而技術的影響要長久得多[10]。再如:技術理性思維的錯誤在于技術對科學的僭越,技術理性對科學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僭越,把技術等同于科學,把科學與人文對立起來,把技術理性推上了“神”的位置。科學理性是人類認識世界、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種認識能力、思維能力和所持有的一種精神[11]。等等,一時間“技術決定論”頗有市場。
圖書館計算機的發展和圖書館文獻視窗系統的普及,尤其是圖書館服務工作的電腦操作和信息技術化,使計算機的初級操作越來越簡化,而易為圖書館員和讀者們所掌握,似乎一切都可以按操作行事,而操作只是一個個的符號而已。由于人們沉溺于數字化的環境,脫離“在場”的社會關系太久,將自己視為純粹意義上的“符號”——步人純粹的數字化過程,從而使自己成為片面的人。這樣長久下來,圖書館員與讀者就成了躲在各種各樣符號后面的一個次要性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似乎也成了人與符號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甚至成了符號與符號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圖書館員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似乎變得冷冰冰、機械和僵化,人文性欠缺。因此符號異化了人,從而使圖書館員與讀者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趨于喪失個性、真實感和豐富性。圖書館員和讀者們被遠遠地甩到了高科技發展的邊緣,他們只能按照少數人事先設定的程序和規則在僅有的范圍內去選擇圖書館產品,成為圖書館數字化產品的被動接受者。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動物。數字化符號的發明和使用使數碼成為人的替代品,各種各樣的卡號、密碼等數字代碼成為人的各種身份的表征,人的鮮活的個性都被淹沒在數碼的海洋里。“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豐富感情以及品質的主動擁有者,他感到自己只是一個貧乏的‘物’,依賴于自身以外的力量,他向這些力量投射出他生存的實質。[12]”
2.2 圖書館學的日漸衰微與圖書館人的思維退化
進入新世紀以來,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更名浪潮此伏彼起,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名稱和實體資源似乎所剩無幾,與圖書館所面臨的數字化時代的信息技術的沖擊很有關系。由于計算機文本已從最初的純文字逐漸向集字符、聲音、圖像、動畫、視頻等多種媒體于一身的多媒體技術發展,電子文化逐漸替代紙質文化,并一步一步消解和弱化人的理性思維能力和反思批判能力。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大量感性的、稍縱即逝的信息超強度地刺激大腦皮層,將改變頭腦的信息加工方式,使認知模式轉變為形象思維,使人更傾向于接受動態、感官的信息,而回避抽象的邏輯思考,放棄追溯本質的思維方式,因此對也是主要使用計算機的圖書館人的思維起到了同樣弱化乃至退化的作用。美國學者邁克爾·海姆認為,網絡的普及和蔓延使得人類不可能再有絕對的哲學與宗教,原因在于:一是電子文化世界沒有規則,人們處在高度的互動關系中,或然性支配一切;二是網絡文化的信息缺乏可靠的選擇渠道與驗證過程。大量虛假信息會使人們求真的哲學精神和理性興趣受到損害;三是鋪天蓋地的信息壓迫,讓人們的識辨能力和專注力大大降低,種種花里胡哨的活潑和脆弱不堪的時尚擠掉了內容的深度,深人持久的理性執著和關注讓位于快節奏的態度轉換[13]。在數字化時代所構建的極富感官的視覺形象面前,作為文學藝術的語言形象在后現代文化的沖擊下舉步維艱。丹尼爾·貝爾曾指出:“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14]”同樣也是面對數量日益增多、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甚至是應有盡有的數字化的資源,圖書館人作為個體對圖書館知識和理論的判斷思考能力也在逐漸的鈍化,對圖書館人文和圖書館哲學智慧的追求似乎也在日漸喪失,對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深度體驗似乎也日漸消失,在海量的信息海洋和便捷的信息化技術面前,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存在與發展陷入了低谷,人文精神茫然困惑,逐漸迷失了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家園,迷失了自我。
2.3 圖書館經典閱讀的弱化與網絡信息的快餐化
數字化時代是一個信息發達、傳播高效的時代,人們無論是出于政治、經濟的需要,還是科學的研究,人們總是希望能獲得最新、最完備的信息,互聯網技術、新興媒體的成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手段,因此,新型數字化、網絡化閱讀趨勢不可阻擋。目前大多數的網絡內容還是免費瀏覽,并且網絡閱讀空間極大。網絡檢索使信息獲取者能方便地得到大量的信息,對于市面上不易買到的書或是較貴的書刊,讀者也會選擇網上下載,閱讀獲取的成本比較低.獲取信息比較容易,使人們能有效地閱讀,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離開紙質讀物而轉投讀網和電子書。因此在很多學者看來,數字化時代多媒體技術集圖像、文字、聲音于一體,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動、感、視、聽于一體的信息世界,全面調動了人的各種感覺器官,使人類從讀寫時代進入視聽時代。而且虛擬實踐在人與感覺客體之間加入了一個數字化平臺,把人從感覺的直接性中解放出來,使人的感覺可以重復、可以再現、可以創造。這種通過虛擬平臺形成的人、機互動的新感性,打破了人類用直接的、單一的方式去感覺自然的有限性,開發出人的整個身體的開放性和敏感性,最大限度地發掘了人的感覺潛能和動能,為人們認識和感覺世界的多樣性與全面性打開了多種方式接觸的渠道。
在人們沉浸于電子音樂、動畫造就的動感十足的電子視聽世界的同時,這樣豐富多彩的信息化平臺也卻造成了讀者與紙質文獻,例如書籍尤其是圖書館經典書籍的疏離,讀者們在網絡虛擬世界中逗留的時間多了,走進圖書館大樓閱讀經典名著的時間卻少了。淺閱讀因此而產出現,淺閱讀是指閱讀的節奏快,不需要思考而采取跳躍式的閱讀方法,追求短暫的視覺快感和心理愉悅。目前普遍存在的網絡閱讀和數字閱讀,其具體特征就是:倡導“速讀”、“縮讀”、“讀圖”,崇尚“時尚閱讀,輕松閱讀”,是一種為應付需要對信息簡單占有的功利性閱讀。因此“淺閱讀”是在信息爆炸的沖擊下,人們對信息閱讀出現的一種應激反應,是信息時代人們閱讀方式迅速改變的產物。且網絡信息的快餐化一次次以商人的水準,靠現代科技加工著世人的趣味,把最富有創造性的文化創造過程變成一種流水線上的批量生產,然后把那些所謂的產品像棉絮一樣充塞著人的大腦,代替人們的思維,使人們的大腦逐漸喪失了活躍的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功能,成為信息和知識的容器,從而把信息的豐富性與敏感性衍變成了內容龐雜的快餐產品。
2.4 圖書館的信息鴻溝現象和信息公平的欠缺問題
在數字化時代由于信息技術的出現是一種全球性現象,因而對這類現象的批評和糾正亦具有全球性,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在建設信息網絡和數字圖書館時,就逐漸考慮到新信息技術條件下的社會公平問題,這些亦對我國圖書館產生著影響。便利的網絡與無所不能的信息服務商在信息服務中,承擔了許多以前圖書館所承擔的職能,但由于最需要得到信息保障的信息弱者缺少利用網絡信息服務的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因此這一社會群體的信息公平就很難實現。而以數字技術應用的程度為標準,可以把中國分為三個不同地區層。在核心層即最發達地區,數字技術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已經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們對數字編碼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在中間層即較發達地區,數字技術的影響相對較大。而在外層即欠發達地區,數字技術的影響較弱。這種信息鴻溝的出現,必然導致中國地區間信息公平問題的分層。在核心層,數字技術為社會生產、管理、文化的存在與運作模式搭建了新的平臺,高效、自由成為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本內涵,傳統人文精神受到挑戰。而在數字技術邊緣地區,數字技術平臺尚未搭建成功,信息貧困者生存、發展的權利受到限制,傳統人文精神色彩仍較濃重。正是這種在分配和有效使用知識、信息和通訊資源方面不同群體之間的實質性不對稱,導致了中國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發展機遇的不平等。
因此盡管在現代信息技術支撐下的網絡,給公眾提供了一個看似平等的文化和信息接受機會,但網絡空間實際上導致了全球新的貧富差距,最為典型的表現是“信息的鴻溝”現象,是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問的兩極化趨勢,也是指在分配和有效使用知識、信息和通訊資源方面不同人類群體之間的實質性不對稱,是有效獲得知識、信息、技術方面的差異。由于這種差異,導致了不同群體面臨的發展機遇不等。信息鴻溝既表現在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也表現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區域之問、城鄉之間、以及不同教育程度階層和不同收入水平階層之問的巨大差異。信息鴻溝的擴大意味著信息貧困者的生存權、發展權受到限制,并在數字化技術的激烈競爭中被愈加邊緣化。在圖書館界,人們也早已認識到信息公平的重要性,有刊物鄭重向圖書館界倡議:“在我國圖書館事業第二個百年來臨之際,展開一個21世紀新圖書館運動,以弘揚現代圖書館精神,協調圖書館與社會的關系,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走近貧民,關心弱者,平等服務,縮小數字鴻溝,建立一個信息公平和保障的制度。[15]”正如范并思教授所說:“公共圖書館要能夠成為維護社會信息公平的保障制度,它就必須以‘免費服務’和對所有社會成員‘無區別服務’為基本前提。[16]”
3.將圖書館的科學精神納入人文精神的軌道
圖書館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圖書館人在認識與改造圖書館、認識與改造圖書館學的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有關圖書館存在與發展狀態的一系列觀念、方法和價值體系。它們是貫穿在對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科學探索和人文研究過程中的一種精神實質意義上的東西,同時也是展現圖書館的科學研究和人文服務內在意義的東西。作為圖書館思想的兩個維度,二者的內涵和指向不同,但同樣在認識與理解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因此,對圖書館學科學精神的理解,不僅要看到其在圖書館工具和圖書館技術操作層面發揮的巨大作用,還要看到圖書館學的科學理念、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等真正體圖書館實質的人文內涵。圖書館的科學精神和圖書館的人文精神二者之間本來是相互滲透,相互包容的,這不論是從圖書館學誕生的現實需要還是從圖書館學應用的目的上,都能得到證明。圖書館人對圖書館認識的每一次深化與提升,都伴隨著當時的圖書館科學技術的突破和創新。所以離開圖書館科學精神的圖書館人文精神,實際上是一種殘缺的人文精神,而離開圖書館人文精神的圖書館科學精神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圖書館科學精神。愛因斯坦早就指出:僅憑知識和技巧并不能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
圖書館的科學精神以物為本,追求真實,推崇理性至上,從總體看,屬于圖書館的工具理性范疇;而圖書館的人文精神以人為本,追求美好,表現對人生終極意義上的關懷,屬于圖書館的價值判斷范疇。二者的統一是圖書館的真理與圖書館價值的統一,二者的關系如同圖書館的手段與圖書館目的的關系。圖書館科學的發展不能離開圖書館人——圖書館員與讀者的目的的參照,而圖書館人——圖書館員與讀者的關系問題的真正解決,也離不開對圖書館客觀規律的真理性探索,離不開圖書館科學之光的照耀。在數字化成為圖書館人文精神新的平臺的今天,圖書館必須發揮圖書館人文精神的包容性和整合力,將高科技和數字化技術的發展納入圖書館人文精神的軌道,發揮其推動圖書館事業健康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
[1]袁詠秋.外國圖書館學名著選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3).
[2]盧泰宏.圖書館學人文傳統與情報科學的技術傳統[J].中國圖書館學報,1992(2).
[3]徐引篪,霍國慶.現代圖書館學理論[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4]鮑宗豪.數字化與人文精神[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
[5]弗洛姆,孫悄譯.健全的社會[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6]蔣永福.圖書館學也是一種人學——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三[J].黑龍江圖書館,1991(6).
[7]朱國萍.圖書館人文精神的起源與發展[J].情報資料工作,2007(6).
[8]劉正偉.略論圖書館學的技術性特征[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0(4).
[9]林海青.論圖書館學研究的技術性特征[J].圖書館,2000(3).
[10]邱五芳.揮之不去的技術情結[J].圖書館,2002(3).
[11]黃健.科學理性的人文反思[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0).
[12]李倫.鼠標下的德性[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13]邁克爾·海姆.虛擬世界的形而上學[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14]丹尼爾·貝爾趙一凡等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北京:三聯書店,1989.
[15]南山圖書館等.以人為本,弘揚公共圖書館精神[M].圖書館,2005(5).
[16]范并思.公共圖書館精神的時代辯護[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