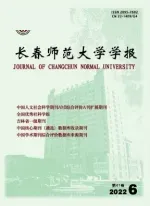湯顯祖“至情觀”辨析
唐衛萍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875)
湯顯祖“至情觀”辨析
唐衛萍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875)
湯顯祖的“至情觀”在其戲劇作品尤其是《牡丹亭》中展露無遺,然而“情”在湯顯祖這里至少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對“情”的承認和贊美,二是“理”對“情”的引導和收束。前者是論“情”的起點,后者則是“情”的落腳點。因此湯顯祖不僅是“情”的歌頌者,而且也是“情”的批判者。
湯顯祖;《牡丹亭》;至情;理
2004年4月由白先勇先生導演的青春版《牡丹亭》在臺北首演,9000張戲票被搶購一空,成為當年轟動臺灣的文化事件。5月,青春版《牡丹亭》在香港劇壇引起轟動。6月,青春版《牡丹亭》在蘇州大學存菊堂演出,再掀高潮。2005年4月8日起,青春版《牡丹亭》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演出,白先勇先生還舉辦了一些相關的講座和講演,在校園里掀起一股熱潮。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成為近年來中國戲劇界最引人關注的事件,尤其是在中國大學生當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正如朱棟霖先生所說,足可稱之為“青春版《牡丹亭》現象”。白先勇先生之所以選擇《牡丹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湯顯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愛情觀的認同。他牢牢把握一個“情”字,以“夢中情”、“人鬼情”、“人間情”為各本的主題,將杜、柳的愛情置于生死兩界和人間磨難的考驗中,體現湯顯祖所賦予《牡丹亭》的“情至”、“情真”、“情深”愛情理念。戲劇演出的轟動吸引人們把目光重新投向了湯顯祖,投向他所生活的時代。湯顯祖創作《牡丹亭》是否正如當代的人們所愿意看到的——對“至情”的大力歌頌和褒揚?本文將通過對《牡丹亭》文本的重新解讀來探討這個問題。
一、從《杜麗娘慕色還魂記》到《牡丹亭》
據徐朔方先生的考證,《牡丹亭》本事主要依據的是《杜麗娘慕色還魂記》話本。如果我們把湯顯祖處理文本的方式加以明晰地展現的話,湯顯祖所關注的問題庶幾得以顯現出一些眉目。因此,湯顯祖對此話本所做的改編是進入文本的一個切口。
兩部作品的旨趣在開篇詩當中就非常明晰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話本開場詩寫道:“閑向書齋覽古今,罕聞杜女再還魂。聊將昔日風流事,編作新文歷后人。”[1]從這首開場詩當中,我們可以獲得三個基本信息:第一,杜麗娘還魂了;第二,作者寫的是一樁具有傳奇色彩的風流事件;第三,寫作的緣由是閑話娛人。
湯顯祖創作《牡丹亭》的主旨則在第一出《標目》當中有非常明確的交代:“忙處拋人閑處住,百計思量,沒個為歡處,白日消磨斷腸句,世間只有情難訴。玉茗堂前朝復暮,紅燭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2]我們從這里大致可以得到三條基本信息:一是劇本因排遣自己的苦悶情緒而發,乃一己情懷之寄托;二是“情”乃其寄托懷抱的核心和載體。
由此作一比照,我們發現,話本中所謂極具傳奇色彩的還魂模式、才子佳人風流韻事的敷衍,與湯顯祖的旨趣似乎統統無關。于此還可提供一些佐證:還魂模式并不是湯顯祖的首創,早在元代的風月劇中就多有涉及,最顯莫如《倩女離魂》,較之杜麗娘的還魂有過之而無不及。
再從全篇情節安排來看,話本之中慕色而亡的杜麗娘不僅順利還魂,與柳夢梅結成夫婦之歡,而且毫無阻礙地得到父母的認可,以大團圓結局。而在《牡丹亭》當中,湯顯祖在強化癡情的杜麗娘的同時,對回生后的杜麗娘亦大花筆墨描寫其性格之轉變,歷經周折方才得到父母的承認,杜柳二人的婚姻勉強得到認可,以大團圓收場。而從劇本的篇幅安排來看,湯顯祖對還魂前后的情節安排可謂平分秋色。他的創造之處,或者說劇本用力之處顯然不僅僅集中在為情生死的杜麗娘,因此毋寧可以說,還魂只是全劇的前奏,好戲還在后頭。也正是源于此,探討湯顯祖在劇本前半部分所大力高揚的“情”,須從后半部分尋找落腳點。而這個落腳點便是湯顯祖創作的旨趣之所在。這一判斷將在下文對湯顯祖創作文本和理論文本的分析當中不斷地重現。因此“情”在《牡丹亭》中到底走向何方,是筆者通過文本解讀其旨趣的關捩。本文的文本分析也正是在此與其他《牡丹亭》文本研究的思路區分開來。
仍然要從《牡丹亭》的開篇詞當中尋其端倪。《牡丹亭》開篇第一句即為怨語:“忙處拋人閑處住”。此語一出,甚有不平之意氣,《牡丹亭》的誕生正與此有直接的關聯。
湯顯祖早年的科考經歷頗為曲折。從隆慶四年中舉人開始,一直到萬歷十一年,也就是經歷四次春試落第之后方在三十四歲以較低的名次考取進士。他的屢試不第與當時的首輔張居正有著密切的關系。《明史》卷二三〇本傳載:“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湯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湯顯祖后又不肯與張居正三子張懋修結交,云:“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1]言語之間頗為自負狂傲,因而春試又下第。張居正死后,湯顯祖以三甲二百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后因不受輔臣申時行、張四維的網羅,于禮部觀政一年后自請赴任南京太常博士。
而萬歷十三年,在太常博士任上,吏部司汝霖給他寫信,勸他和上級打通關系,可升為吏部主事,他寫信推辭了。在《與司吏部》一文當中,湯顯祖以父母年老、兒女尚幼、身體虛弱不服北地水土為由相推辭。明眼人一看即知這只是場面上的話。況且后來,即萬歷二十六年湯顯祖上京上計的時候寫過一篇《感宦籍賦》,在其中他所欣賞的宦吏是“寒暑侵而靡覺,骨肉怨而不辭。”[3]那么我們就會明白,湯顯祖不愿升遷另有其詳。真相在兩個小小的話語轉折之處透露出來。“仆縱北徙,止可得六品郎。”言外之意,升遷的品級還不足以讓他克服種種的困難北上。另外一句:“況夫近中軸者,不必盡人之才;游閑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長安道上,大有其人,無假于仆。”[3]大意是京城能夠當此任的人很多,也不缺我湯顯祖,況且我游閑度日,也不足以讓人詬病。言語之間頗自傲,似有牢騷。細究其意,他對于當時官場上巴結鉆營的風氣大為不滿,干脆認真地說:“人各有章,偃仰澹淡歷落隱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憐,成其狂斐。”[3]何其傲慢!然而他果真如自己所說,有淡薄隱映之致嗎?其實,他只是不想通過“與執政通”的方式來達到升遷的目的。
萬歷十九年春,湯顯祖接到吏部一份刊發了神宗圣諭的邸報。神宗在圣諭當中對大臣們風發言事、沽名釣譽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指責,并下旨對大小官吏奪俸一年。[3]湯顯祖一方面對“南都之臣”無端地和奸逆之臣一起受責罰感到憤憤不平;另一方面,他渴望皇帝借自省之機能進一步懲治奸佞;還有可猜測的一點是他想借此引起朝廷的注意,或可有重用之機。因此他慨然上書《論輔臣科臣疏》,希求皇上整頓吏治,以新時政。這份上書雖言辭激烈,然對政治情勢的分析確為中肯。神宗早已習慣了大臣對首輔們的彈劾,大多數時候,他對于這樣的奏章都是留中不發,安慰輔臣,最后不了了之。然而既非言官又非重臣的湯顯祖的這份上書卻觸怒了神宗,尤其是他對于兩任首輔輔政特點的概括實觸到了神宗的痛處:“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后十年之政,時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壞之。”[3]這兩任首輔可以說是神宗最為信任的輔臣,然而后來二人都未能得善終。湯顯祖這些清醒的肯綮之語被神宗歸為“訕上賣直”的浮言。湯顯祖上疏后,惴惴不安地等待回復。是年庚辰十六日,也就是上書兩個月之后,湯顯祖被貶為徐聞典吏。這次貶官對湯顯祖的政治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的仕宦生涯由此漸趨暗淡。
湯顯祖吏部告歸以后,即寫出《牡丹亭》;同一年春,兩歲的呂兒得痘夭亡;八月,方八歲的西兒夭亡。官場失意,加上喪子之痛,湯顯祖的告歸充滿了凄涼和悲哀。輾轉四顧,無處排遣自己的憂傷。所以在《牡丹亭》的標目中他才會感嘆:“百計思量,沒個為歡處。”這實在是切膚之語。對于自己遭遇的這些變故,晚年他在寫給伶人的信中提到:“……如今世事總難認真,而況戲乎!若認真,并酒食錢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為認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凄涼的心境加上早年對戲曲的愛好,使他選擇了戲劇作為排遣自己憂傷的渠道,并把這種起初看來僅僅是消遣娛樂的創作變成了實現個人野心的絕妙場所。
那么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問題是:湯顯祖所要表達的“意”是從哪一個角度彰顯出來的呢?“百計思量”之后,湯顯祖選擇了他認為是世間最難訴的“情”。從話本到《牡丹亭》最為核心的改造之一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意”寄托在了“情”上。在人物復雜的性格以及情節設計當中都試圖對這個“情”進行辯證、考量,尤其是其中“夢”與“情”的糾纏,勾畫出了湯顯祖心目中“情”的復雜內涵。然而這并不是終點。“情”到達終點以后,接下來面臨的是如何安頓“情”的問題。
二、《牡丹亭》文本解讀
杜麗娘無疑仍然是文本所關注的核心。很多評論家認為杜麗娘的性格當中存在很多矛盾的因素,并分析這種矛盾來自“情”與“理”(理的外在表現形式即“禮”)的沖突,并以此推導“情”受到了壓制和束縛,這是理學對人的自然欲望的戕害,杜麗娘是要求自由解放的青春和美的化身云云。最常選用的例子是杜麗娘回生后和柳夢梅之間的一段對話:
〔生上〕艷質久塵埋,又掙出這煙花界。你看他含笑插金釵,擺動那長裙帶。〔見介〕麗娘妻。〔旦羞介〕 〔生〕姐姐,俺地窟里扶卿做玉真。〔旦〕重生勝過父娘親。〔生〕便好今宵成配偶。〔旦〕懵騰還自少精神。〔凈〕起前說精神旺相,則瞞著秀才。〔旦〕秀才,可記得古書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生〕日前雖不是鉆穴相窺,早則鉆墳而入了,小姐今日又會起書來。〔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虛情,人須實禮,……[2]
在作出判斷之前,我們可以仔細體味一下這段對話的微妙之處。柳夢梅見到回生的杜麗娘時,麗娘“含笑插金釵,擺動長裙帶”,如同來到一個新的世界一樣,充滿了好奇與欣喜。柳夢梅因思度與麗娘冥誓,因此叫出“麗娘妻”。杜麗娘馬上做害羞狀。柳夢梅流露出真情,與麗娘敘衷情,而麗娘全然不顧,以救生之恩回避感情,柳夢梅并未意識到杜麗娘的用心,仍欲與回生的杜麗娘成夫婦之歡。杜麗娘于是以身體尚虛為名推辭。柳夢梅疑惑不解,杜麗娘終于吐露原委:“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杜麗娘說出的這番話令柳夢梅大惑不解,杜麗娘如何又“會起書來?”杜麗娘只好進一步解釋:“鬼可虛情,人須實禮。”回生之后的杜麗娘也就是夢醒之后的杜麗娘。夢醒之后的杜麗娘現在需要回到“禮義”了。作為“鬼”的杜麗娘和作為“人”的杜麗娘真的是由“情”與“理”的沖突導致性格發生分裂嗎?似不能如此下斷語。
不妨回到文本先追蹤一下杜麗娘“情”的發展線索,看看湯顯祖如何讓這個少女成熟的吧。杜麗娘人生的第一課便是《詩經》當中的《關雎》篇。湯顯祖安排《閨塾》這一出看似為戲劇隨意增加喜劇氣氛而設,然而卻大有深意。在這一出當中,春香是活躍在前臺的主角,杜麗娘并沒有過多的言語,舉止老成持重,但春香對老先生的發問卻句句打在她的心坎上。因為有了《關雎》的觸發,少女情竇初開,所以杜麗娘感嘆:“圣人之情,盡見于此矣。”只是這時候她并沒有一個實際的戀愛對象。及至游園,感物傷春,方有年華之嘆。但是杜麗娘動春心卻并不是“情不知所起”,常觀詩詞樂府中成雙成對的佳人才子便是她動“情”而傷春的一個重要來源。此時的杜麗娘很顯然是因感自然而發動了春情,夢中與柳生相會,進而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任由傷春的情緒毀壞了她的健康,最終奪去了她的生命。她的確是因“情”而亡。這段“情”通過“夢”找到了依托的對象,而回到現實的杜麗娘在“尋夢不得”之后終于傷夢而亡。
早夭后的杜麗娘作為“鬼”在陰陽兩世間徘徊,如在夢中一樣。她仍然不受人間禮法的約束,因此可以魂游而與柳夢梅幽媾,熱情大膽全然不似在人間,致使柳夢梅有兩次都懷疑是在夢中。①但是這段經歷卻因杜麗娘的回生而成為一片模糊的夢境。對柳夢梅來說,本是歷歷在目之事,在杜麗娘看來,回生之后這些事情都變得撲朔迷離。因為回生后的杜麗娘仍舊是女兒身,且并不認識柳夢梅的容貌。回生,對于杜麗娘猶如從一場夢中醒來(杜麗娘的這些感受直到第五十四出才由春香口中套出。〔貼〕還魂時像怎的?〔旦〕似夢重醒,猛回頭放教跌)。因此,直到回生之后,柳夢梅的形象在杜麗娘的心中才真正明朗起來。與柳夢梅行夫婦之禮,方才真正圓其春夢。也就是說,如果杜麗娘不回生,那么她的具有自然情欲性質的傷春之“情”就無法真正實現,這與湯顯祖“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3]的至情觀可以說是一致的,“回生”讓杜麗娘的“情”達到了頂峰。
回生后的杜麗娘見到了夢中的“柳夢梅”,夢中之“情”在現實中找到了依托的對象。此時,湯顯祖卻讓杜麗娘“會起書來”,因為回生后的杜麗娘自覺地重回禮義的規約之下。此時正是全劇另一個高潮到來的前奏。杜麗娘的個人情欲得到了滿足,接下來就是如何安頓“情”的問題,也即杜麗娘要為自己的“情”爭得合法的地位,重得做人的尊嚴。而只有禮法才能賦予她這種尊嚴。這個問題的難度和重要性在全劇中絲毫不亞于杜麗娘的重生。這可以說是回生后的杜麗娘在人間獲得合法生存權利的唯一途徑。
三、“至情觀”反思
為什么湯顯祖會讓他所高歌的“至情”回到禮義的規約之下呢?這里就涉及“情”和“理”的關系問題。“情”和“理”的關系一直是宋明理學所要辨析的重要問題之一,而此問題的本源在于對“性”和“情”的分疏。②“情”在《牡丹亭》文本中無疑屬于“食色之性”的范圍。(這與理學家們所談的“已發”層面上的“情”并不是對應的,“情”在這里是指發生在人身上的自然的情欲,杜麗娘的生死可以說都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核心。)運用理學家的話語,“情”只能列于“氣”的層面。而對于“性”的問題,湯顯祖在四十多歲的時候有一個自我反省:
或曰:“日者士以道性為虛,以食色之性為實,以豪杰為有,以圣人為無。”嗟夫,吾生四十余矣,十三歲時從明德先生游。血氣未定,讀非圣賢之書。所游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子曰天下士日泮渙悲歌,意何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杰之士是也,非迂視圣賢之豪。[3]
從這條信息里,我們約略可以看到當時知識界的風氣,圣人之學流入世俗日用之學(如食色),“道性”被“食色之性”代替。圣人不再被神秘而莊嚴的光環籠罩,取而代之的是對意氣豪杰之士的推崇。這種風氣的出現與當時盛行的王學左派有很大的關系。李贄在《與焦弱侯》一文中寫到:“古今賢圣皆豪杰為之,非豪杰而能為圣賢者,自古無之矣!”直接把豪杰和圣賢等同,而實際上他就是用豪杰代替了所謂的圣賢,以此在圣賢的血脈中注入了新的元素。湯顯祖對自己的反省實際上是對儒家所談的“性”有了重新的認識。
為更好地了解湯顯祖這番話的背景和含義,在這里有必要重現孟子和告子的一段爭論。告子認為,“生之謂性”,所以他說:“食色,性也。”而孟子從人與禽獸的區別出發,認為人的動物性的一面(人與其他動物相同的一面)應該被規約在“善”這個潛在的區分標準之內。因此孟子所謂的“性”就排除了告子所說的“食、色”之類的與動物沒有差別的自然欲望。所以孟子認為“性本善也”。宋代的理學家們如二程則立足孟子的“性善說”,認為“性即理也。”朱熹沿著這條路子把“理”放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到了明代,王陽明則提出“心即理”。雖然這些概念當中有很多糾結的矛盾,但我們仍然可以把握的是,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他們都不言自明地把孟子的“性善說”作為論說的前提。即便王陽明不再諱言聲色貨利之欲,但其并不認為這是“性”所本來具有的,而認為是已經被私欲所遮蔽,需要修養革除的。因此“生之謂性”是放在“氣”的層面來說的。③因此無論朱子一派和王陽明一派存在多么大的分歧,對他們來說,圣人至少是一個孜孜可求的目標。到了晚明,李贄更是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4]李贄的本意當然仍需要辨析,然其容易給后學者造成一種印象:前賢們所孜孜以求的圣人形象的神秘感被日用倫理消解殆盡。“圣人”成為一個虛化的概念,所謂的“義氣豪杰之士”反為時人所追捧。湯顯祖反省自己早年的迷誤也正在此。對于自己的親身生活經歷而言,他最為切實的感言便是:“知生之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也就是說,“食色之性”決不能和“道性”混為一談。如果一味追求“食色之性”,就會“迷性”。由此湯顯祖對自己的反省實際上是重新回到了孟子“性善論”的言說立場。因此雖然湯顯祖流連道學,出入佛老,但在對“性”這一根本認識上卻能修持住。也正是在思想上打開了這個關節,即便他在后來的《邯鄲記》、《南柯記》中流露出濃重的出世思想,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始終沒有走入佛門,也與后來的“復社”始終保持著距離。這一點對于理解湯顯祖對“情”的處理方法至關重要。
根據湯顯祖的這種反省思路,我們再回到文本中來看,杜麗娘的“春情”是值得反省的。春情的發生是人的自然本性,本無可厚非,然而她一味沉溺自然的情欲不能自拔,沒有加以疏導,導致“迷性”。因為生之為性并非食色之性,如果執著于此,達到極點,便會為此付出代價。杜麗娘的死,正是被“情”所迷而造成的后果。而湯顯祖卻屢次采用“夢”的手段為“情”作了一定程度的辯白,正是“夢”這個媒介讓“情”和“理”之間保持著一種張力的關系。當杜麗娘沉迷于情欲的時候,是夢給了她這樣的自由,讓她能充分地享受青春的快樂;而回生后杜麗娘與柳夢梅脫離了夢境真正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理”的外化形式“禮”就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夢”的職責,給了她在現實生活中的自由。杜麗娘自然發生的情欲經過“夢”到“禮”的轉換,在現實生活當中找到了歸宿。
從湯顯祖的這種處理手法看來,為情而生死固然令人嘆惋,回到禮義似乎才是真正的歸宿。而回到禮義就意味著為夢醒之前的“情”找一個歸宿。“情”的強烈感染力因為“夢”而被染上了一層迷離的色彩,而“夢中之情,何必非真?”似乎又極力地為“情”辯白。在此我們方真切體會到湯顯祖“世間只有情難訴”的感嘆。自然之情不應該遭到壓抑,但是若放任不顧,只會傷己傷人。若是能以禮義來收束自然的情欲,那么杜麗娘這個形象才是完整的。惟其如此,杜麗娘才是真正值得歌頌的至情女子。
可惜時人罕能識其真義,多為還魂所惑,曲家自不必說,斤斤于聲律詞藻,固守門戶。即使湯顯祖的知交如達觀,也是執著于湯顯祖的“情”,于此不能看透,汲汲于打破“寸虛館”,湯顯祖有口難辯。而如演員商小玲、民間讀者小青之類更是知錯了音、會錯了意,以為杜麗娘“守得個梅根相見”方是正果,竟為情而亡,不免令人嘆惋。由此反觀青春版《牡丹亭》所打出的“至情”口號,恐怕也需要重新來認識。
[注 釋]
①第一次是杜麗娘深夜初會柳夢梅,柳夢梅產生疑問:“小娘子夤夜下顧小生,敢是夢也?”第二次,杜麗娘告訴柳夢梅自己的身世之后,柳夢梅驚疑:“奇哉!奇哉!柳夢梅做了杜太守的女婿,敢是夢也?”(引文來自《湯顯祖戲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②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非常復雜,非本文所能及。因此僅就湯顯祖所關聯的具體問題來論述。
③“氣”在理學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朱熹、王陽明看來,其涵義主要聚焦在物質的層面,具有形而下的性質。“氣”則有清濁善惡之分,聲色貨利等都可以落在“氣”的層面來講。對于這一點,可參看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頁)及王陽明《傳習錄》 (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277頁)。
[1]徐朔方.湯顯祖年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9,53.
[2]湯顯祖.湯顯祖戲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33,395.
[3]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M]∥徐朔方,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54,1226,1226,1214,1214,1093,1166.
[4]李贄.李贄全集注[M]∥張建業,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8.
Discriminating Tang Xianzu’s View on “The Passion”
TANGWei-ping
(School of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TangXianzu’s viewon“the passion”in his dramatic works,especiallydemonstrated in the dramaThe PeonyPavilion.“The passion”contains at least twoaspects in Tang Xianzu’s context:on one hand,he sang for it;on the other hand,he emphasized that it should be ruled by the reason.The former is a starting point,while the latter is the end-result.Therefore,TangXianzu is not onlyan advocator for“the passion”,but alsoan objector.
TangXianzu;The PeonyPavilion;passion;reason
I206.2
A
1008-178X(2012) 01-0105-05
2011-10-11
唐衛萍(1984-),女,湖北荊門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