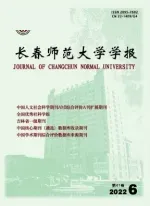論宋詞中“功用性亭”意象的抒情內涵及其藝術營構
王慧敏
(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蘇州建設交通分院,江蘇蘇州 215104)
論宋詞中“功用性亭”意象的抒情內涵及其藝術營構
王慧敏
(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蘇州建設交通分院,江蘇蘇州 215104)
“亭”是中國古代建筑中具有獨特風格與功能的建筑形式,它凝縮了我國古代園林建筑中形式美的精華,集實用價值與觀賞性能于一體,因而與文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長期的文學實踐中,“亭”逐漸變成一種具有獨特文化內涵與象征意義的意象。宋代詞人頻繁地以“功用性亭”意象入詞,并以之為核心載體,巧妙靈活地組合諸多傳統意象,或寫離別之痛,或訴相思之苦,或抒羈旅思鄉之愁,或道行人不歸之怨,營構出了種種凄婉動人的詞境,展示出了豐富的悲劇美學內涵,從而使宋詞更具感人的藝術魅力。
宋詞;功用性亭;意象;抒情內涵;藝術營構
一、“亭”意象在宋詞中頻頻出現的原因
“亭”在唐五代詩詞中已經是一個常常出現的意象,如:“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李白《菩薩蠻》);“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李白《勞勞亭》);“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憶江南》);“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題齊安城樓》);“嫩草如煙。石榴花發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淥。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歐陽炯《南鄉子》);“花滿驛亭香露細,杜鵑聲斷玉蟾低。含情無語倚樓西”(張泌《浣溪沙》);“輕輕制舞衣,小小裁歌扇。三月柳濃時,又向津亭見(牛希濟《生查子》);“暖傍離亭靜拂橋。入流穿檻綠搖搖。不知落日誰相送,魂斷千條與萬條”(孫魴《楊柳枝》)……“亭”意象在宋詞中更是頻頻出現,除了有具體名字的亭以外,還有諸如“長亭”、“短亭”、“離亭”、“旗亭”、“津亭”、“郵亭”、“驛亭”“風亭”、“危亭”、“江亭”、“小亭”、“虛亭”、“水亭”、“池亭”、“石亭”、“野亭”、“溪亭”、“閑亭”、“幽亭”、“涼亭”、“茅亭”、“梅亭”、“山亭”、“園亭”、“竹亭”、“林亭”、“草亭”等等。宋代詞人為何這么垂青“亭”意象呢?簡言之,亭是中國古代建筑中具有獨特風格與功能的建筑形式,它凝縮了我國古代園林建筑中形式美的精華,集實用價值與觀賞性能于一體,因而與文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長期的文學實踐中,亭逐漸變成一種具有獨特文化內涵與象征意義的意象,它不僅點綴著真實世界的人文景觀,也映襯了文學的優美境界,真可謂賞心悅目、怡情怡性。
具體說來,亭是最能代表中國建筑特征的一種建筑形式,也是中國人最為喜聞樂見的一種建筑形式。而且,“在所有的園林建筑中,亭最平民化、最具親和性。十里長亭,不管貧賤富貴都可以在那里惜別;山道路亭,無論樵夫騷客都可以在其中賞景。亭既可以尊貴地躋身于皇家園林中,又可以嫻雅地佇立于文人園里,更可以樸素地散布于山野村郭。”[1]明代計成在《園冶·亭》中說:“亭者,停也。所以停憩、游行也。”說明亭是供人歇息游覽的地方。實際上,這種現代意義上作為游覽和觀賞的亭,大致是魏晉南北朝才出現的,在此之前,亭的基本形制尚未成熟。據覃力先生《亭史綜述》[2]一文介紹,亭最早作為國防軍事建筑,始建于春秋戰國時期,皆設于邊疆要塞,作用有監視敵情、傳遞烽火等。秦漢時代,亭發展成一種多用途、實用性很強的建筑形象的統稱。按其功能可分為四類:一,城市中的亭,如街亭、市亭、都亭、旗亭等。這種亭非常近于城觀,與后來的市樓、樵樓、金井樓等亦有許多相似之處。二,基層行政單位的亭,按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由負責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亭長管理。《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史記》就記載劉邦“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三,邊防報警的亭,是在邊防城墻、要塞處設置的亭侯、亭障、亭燧等。除了以上三種功能的亭以外,對文學來說,更重要的是第四種功能的亭,即“驛亭”,或稱“郵亭”,它們設于交通要道,兼有郵遞、驛站和旅社等作用,所以又稱作“亭傳”。漢代以后,隨著私營的逆旅出現,亭傳逐漸廢棄,但民間仍有在交通要道和村口、路旁筑亭的習俗,以作為旅途歇息之用和迎賓送客的禮儀場所。后來就逐漸演變成了一種和離人、鄉思、旅愁相聯系的富有感傷色彩的象征性的建筑。而離情別緒、羈旅閑愁以及思鄉懷人等內容又是宋詞中重要的抒情主題,故而詞人們便常常不約而同地選擇“亭”這一意象來抒情達意。
魏晉以后,隨著園林建筑的發展,亭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其功用性減弱,逐漸出現了供人游覽和觀賞的亭。三國孫吳定都建業修建的勞勞亭,亦名新亭,已是一座帶有游覽性質的亭。《世說新語》記載曰:“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宴飲。”而晉時會稽山陰的蘭亭就完全是供人游覽和觀賞的亭了。(魏)酈道元撰《水經注》卷四十“漸江水”中記載:“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勖,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由此看來,蘭亭最初不過是一座建于湖口處“蘭上里”村頭的路亭,只是為了更好地觀賞湖光山色,才由太守王廙之移至水中,起筑山巔,由“功用性的亭”轉變為“觀賞性的亭”而王羲之等人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在蘭亭舉行的一次規模巨大的文朋詩友盛會,已傳為文壇佳話。這次文人聚會,共成詩37首,編為《蘭亭集》。蘭亭詩的內容,或抒寫山水游賞之樂,或直接抒發玄理,表現了文人們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審美情趣,“蘭亭”也成了宴飲聚會的代名詞。而在宋代享樂之風盛行的大背景下,詞人也多數具有追求宴飲之樂的文化心理,因而,“蘭亭”便作為一個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意象頻頻出現在宋詞中。隋唐之后,亭就作為一種景觀建筑常常出現于園林或風景名勝處。而且,“建筑藝術是空間藝術,亭的妙處就在于‘虛’,在于‘空’。它四面空靈,卻將其虛空的內部與周圍的空間環境緊密相連,納周圍如畫景物入亭中,使人來到亭內,仿佛置身于畫廊一般,因而從有限的空間進入了無限的空間。虛空納萬境。”[3]計成在《園治》中說:“軒楹高爽,窗戶虛鄰,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漫”。清人許承祖在《詠曲院風荷》一詩中亦說:“綠蓋紅妝錦繡鄉,虛亭面面納湖光。”都形象地描繪了亭的空靈意境。無怪乎張宣在他的《溪亭山色圖》詩中寫到:“石滑巖前雨,泉香樹杪風,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蘇軾也有“唯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象得天全”(《涵虛亭》)的感嘆。亭這種虛空、靈逸的特征,可以說是閑適、淡泊、超脫境界的象征,這正迎合了宋代部分詞人追求淡泊隱逸以求自適的心理,因而宋代詞人便愛在詞中運用“亭”意象來言志抒懷。
二、宋詞中“功用性亭”意象的抒情內涵以及巧妙的藝術營構
正如上文所述,亭是一種集實用價值與觀賞性能于一體的建筑,故宋詞中的“亭”意象按其性質也可分為“功用性亭”意象和“觀賞性亭”意象兩種。前者一般用于抒發離愁別恨、羈旅閑愁和思鄉懷人之情緒;后者則主要服務于宴飲唱和、詠物寫景、閑適隱逸之內容。下面主要來探討宋詞中“功用性亭”意象的抒情內涵及其藝術營構。
宋詞中“功用性亭”意象包括“長亭”、“短亭”、“離亭”、“旗亭”、“津亭”、“郵亭”、“驛亭”等,現實中的這類亭一般用于旅途歇息或者作為迎賓送客的場所,故宋詞中這類亭往往和行人、倦客、離人、游子、思婦等聯系在一起。詞人借助于這類“亭”意象,或寫離別之痛,或訴相思之苦,或抒羈旅思鄉之愁,或發行人不歸之怨……傳達出種種“特地魂銷”(歐陽修《浪淘沙》五首之二)的愁苦之情,從而使宋詞產生了令人黯然銷魂的藝術魅力。
好的詩詞作品之所以具有動人的藝術魅力,除了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情感特質以外,意象的選擇和組合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作家通過若干意象的精心選擇和巧妙組合,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意象體系,進而由意象體系的綜合效應產生了‘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意境。”[4]因而宋代詞人除了運用“功用性亭”意象為背景和布景來展開詞意外,還巧妙地組合其它意象,如“柳”、“草”、“酒”、“舟”、“淚”、“月”、“蟬”、“雨”等,來構筑出種種凄美婉約的詞境,給人以藝術美感。下面來看幾種意象組合。
1.亭與柳的組合
“柳”與“留”諧音,其長條依依的體形又是天生一副款款惜別的姿態,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魯道夫·阿恩海姆所言:“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并不是因為它看上去像是一個悲哀的人,而是因為垂柳枝條的形狀、方向和柔軟性本身就傳遞了一種被動下垂的表現性。”[5]因而古人在送行時往往要折柳贈別,久之便成為一種習俗。這種習俗始于漢代,據《三輔黃圖·柳》記載:“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到了唐宋,折柳贈別的風尚大為流行。唐釋慕幽《柳》詩云:“今古憑君一贈行,幾回折盡復重生。”宋晁端禮《朝中措》詞亦云:“短亭楊柳接長亭。攀折贈君行。”正因為古人有這種折柳送別的傳統習俗,因此文人們就很自然地把柳和離愁結合起來,并成為渲染離情別恨的最佳意象之一。那么,柳與作為具有送別等功能的亭相結合,便構成了更具豐富內涵的抒情意象,不僅使離情之苦傳達得更為淋漓盡致,詞境也構筑得更為凄美纏綿。如“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周邦彥《蘭陵王》)詞一上來便寫柳陰、寫柳絲、寫柳絮、寫柳條,先將離愁別緒借著柳樹渲染了一番,然后是虛寫,詞人設想,長亭路上的柔條年復一年地被人攀折,實是在感嘆人間離別的頻繁。詞人組合亭、柳意象,采用虛實結合的手法,寫得情深意摯,耐人尋味。又如“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云遮盡,目斷人何處?”(惠洪《青玉案》)在槐柳成蔭如煙霧籠罩的長亭驛道上,遠行之人即將別去,一片離愁別恨,在長亭和煙柳的襯托下,更顯情思婉約,凄切感人。另如“輕輕制舞衣,小小裁歌扇。三月柳濃時,又向津亭見”(晏幾道《生查子》);“柳絲挽得秋光住。腸斷驛亭離別處。斜陽一片水邊樓,紅葉滿天江上路”(陳允平《玉樓春》);“莫折長亭柳。折盡愁依舊。只有醉如狂。人生空斷腸”(舒亶《菩薩蠻》)等等,皆通過亭與柳的組合,營構出凄美纏綿的詞境。
2.亭與草的組合
芳草亦常與離情別緒連在一起。自從屈原在《楚辭·招隱士》中寫下“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這一借春草抒寫離情的名句后,歷代詩人就常常以芳草的萋萋綠色,寫照離人的別恨悠悠;以芳草的連綿不斷,象征離愁的無窮無盡。如:“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李煜《清平樂草》);“恨如芳草,萋萋刬盡還生”(秦觀《八六子》)……總之,草已被普遍用作傷離惜別的意象,它一經與“亭”意象組合,詞人的生命空間也染上了凄婉柔美的感傷基調。宋詞中這樣的例子很多,如:“又是離歌,一闕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林逋《點絳唇》);“綠楊芳草恨綿綿。長亭路,何處認征鞍”(蔡伸《小重山》) ;“碧草綠楊岐路。況是長亭暮”(梅堯臣《桃源憶故人》);“芳草遍長亭。東風吹恨生”(劉翰《菩薩蠻》);“燈火雨中船。客思綿綿。離亭春草又秋煙”(吳文英《浪淘沙》)……
3.亭與雨的組合
雨,是一種永恒的自然現象,和人類生活關系十分密切。然而“雨這種自然現象,常會給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受,細雨如溫柔的傾訴;暴雨象痛快的渲泄;煙雨蒙蒙,使人仿佛置身夢中,雨前壓抑、雨時舒心、雨后明凈。進入古典詩詞中的雨,已不是簡單的純自然的客觀物象,它已成為詩人某些情感信息的載體。”[6]因而,雨一旦進入人們的審美視野,便表現出或喜或悲的不同的審美內涵。正如康德所說:“審美意象是一種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顯現,它從屬于某一種概念,但由于想象力的自由運用,它又豐富多樣,很難找出它所表現的是某一確定的概念。”[7]但是雨意象多數情況下還是代表著無盡的離愁和纏綿的情思,這和“功能性亭”意象在古典詩詞中的意蘊是相通的,因而亭和雨組合,離別之愁、相思之苦自然倍增,非單個意象可比。如“宴闋。散津亭鼓吹扁舟發。離魂黯、隱隱陽關徹。更風愁雨細添凄切。”(朱敦儒《踏歌》)津亭處,扁舟催發,已經令人黯然銷魂,此時更兼瀟瀟風雨,其境自是凄苦異常。另有“飲散短亭人欲去。留不住。黃昏更下蕭蕭雨”(晏殊《漁家傲》);“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吹頰。淚珠不用羅巾裛。彈在羅衣,圖得見時說”(蘇軾《醉落魄》憶別);“風蕭蕭。雨蕭蕭。相送津亭折柳條。春愁不自聊”(劉克莊《長相思》餞別)等等,皆意境凄迷,基調傷婉。
值得注意的是,詞人們還往往將這類“亭”意象和上述眾多意象自由靈活地組合在同一首詞里,柳永的《雨霖鈴》堪稱這方面成功的典例: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此詞為抒寫離情別緒的名篇,也是柳永婉約詞的杰出代表。尤其是詞的上片寫分別時的情景,通過“長亭”與“蟬”、“雨”、“舟”、“淚”以及“煙波”、“暮云”等一系列意象精巧有序地組接在一起,將詞人離開汴京與戀人惜別時的真情實感表達得纏綿悱惻、凄婉動人,極富藝術感染力。又如晏殊的《采桑子》:
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長恨離亭。淚滴春衫酒易醒。 梧桐昨夜西風急,淡月朧明。好夢頻驚,何處高樓雁一聲。
詞的上片以“長恨離亭”、“淚滴春衫”、酒醉易醒”等感傷春日離愁;下片以梧桐西風、淡月孤雁等烘托秋日別恨,意境優美凄切,讀來哀婉動人。
概而述之,宋代詞人頻繁地以這類“功用性亭”意象入詞,并以之為核心載體,巧妙靈活地組合諸多傳統意象,或寫離別之痛,或訴相思之苦,或抒羈旅思鄉之愁,或道行人不歸之怨,營構出了種種凄婉動人的詞境,展示出了豐富的悲劇美學內涵,從而使宋詞更具感人的藝術魅力。
[1]張勁農.談“亭”[J].廣東園林,2005(6):14.
[2]覃力.亭史綜述[J].中國園林,1992(4):24-25.
[3]翦秀,何珊.古今亭話[J].長江建設,1996(3):44.
[4]何春環.傷別詞的意象藝術[J].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2):120.
[5][美]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滕守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624.
[6]袁盾,楊恬.四季風煙中的雨意情——試論中國古代詩詞中的雨意象[J].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8(4):63.
[7][德]康德.判斷力批判[M].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16.
On the Lyrical Connotation and Art Construction of Functional Pavilion’s Imagery in Song Ci
WANGHui-min
(Suzhou Institute of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s,Suzhou 215104,China)
Pavilion,an unique and functional architectural form among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compresses the formbeautyquintessence of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integrates practicability and beauty.As a result,it gets closely related to literature an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agery provided with distinctiv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long history of literary practice.The poets of Song dynasty frequently used‘the functional pavilion’as the core carrier in their works,as well as ingeniously combining with various traditional imageries to created a variety of racking imageries,such as the pain of parting,the suffering of lovesickness,the sorrowof home-sickness,and the resentment of pedestrians’non-returning,which expresses affluent tragic aesthetics connotations and makes SongCi possess more movingartistic charm.
SongCi;functional pavilion;imagery;lyrical;art construction
I206.2
A
1008-178X(2012)01-0101-04
2011-09-01
王慧敏(1974-),女,山東菏澤人,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蘇州建設交通分院講師,博士,從事唐宋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