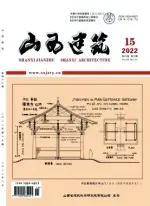鋼筋混凝土結構現代抗震思路的理解和討論
賈福東
1 現代抗震思路的發展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地震作為人類面臨的主要的自然災害,對人類的生產生活產生過巨大的危害,但由于實踐和認識方面的原因一直未能找到挑戰這一自然力的有效辦法。隨著生產力的大發展及人類文明進入工業時代,特別是城市化的發展,人們對居住條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筑結構的抗震研究也因此獲得了快速的發展。
世界各國最早提出抗震設計的是日本,規定取房屋重力荷載的0.1倍,即水平加速度為0.1g作為地震水平力,并將它按各樓層的重力荷載比值分配給各樓層。這種方法既沒有考慮結構的彈性動力特征,也沒有找出地震作用的統計規律。而1927年的美國UBC第一版也是取地震作用為0.1乘以房屋重力荷載。
自1933年美國首次記錄到地震的地面運動記錄以后,20世紀40年代Biot從結構動力學角度提出了彈性反應譜概念。50年代Housner發表了他用Duhamel積分作出的EL Centro地震的彈性加速度譜、速度譜和位移譜。雖然這個彈性反應譜揭示了結構在地震地面運動的隨機激勵下的強迫振動動力特性,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無法解釋實際大、中震作用于結構所產生的危害遠小于彈性反應譜分析結果的這一事實。20世紀60年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直接動力法作為一種新的地震反應計算方法得到了迅猛的發展。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Newmark等人才逐步提出了考慮結構非彈性性能的抗震設計思路。他認為設計結構時取用不大的地震作用只是賦予了結構一個基本的屈服力,而發生更大的地震時是靠結構必要的非彈性變形能力來抵抗足夠大的地震沖擊。Newmark還首次提出了延性(ductity)的概念。此后,Newmark又利用自己編制出的非線性動力反應程序和簡單的雙折線無剛度退化模型對不同周期的初始剛度相同的單自由度體系在多條地面運動輸入下的動力反應做出了初步系統分析,提出了“等位移原理”和“等能量原理”,揭示出了不同彈性周期的結構取不同的屈服水準值時,在同一個地面運動輸入下屈服水準與結構最大非彈性位移之間的關系。這既揭示出了延性能力和塑性耗能能力是屈服水準不高的結構在較大地震下引起了非彈性動力反應中不致發生嚴重損壞和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有力的回答了Housner彈性反應譜所帶來的疑問。
考慮結構非彈性性能的抗震設計思路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抗震設計理論,已成為現在各國抗震設計規范的基本理論依據。它實際上也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基于性態抗震設計理念”的基本依據和出發點。
2 現代抗震思路的核心內容
通過對R—μ—T關系的研究從而構建整套“抗震延性設計體系”,是現代抗震思路的出發點與核心內容。這里R為同一地面運動輸入下最大彈性反應力與非彈性反應屈服力之間的比值(R=pe/py),稱R為彈塑性反應地震力降低系數,簡稱地震力降低系數;μ為結構最大非彈性反應位移Δmax與屈服位移Δy之間的比值(μ=Δmax/Δy),稱μ為位移延性系數;T為按結構彈性剛度求得的結構自振周期。各國在這一領域中作了深入的分析工作。研究的對象是單自由度體系選用不同的滯回規律時,其屈服水準與彈性自振周期以及最大非彈性動力反應之間的關系;以及地面運動特征(包含場地土特征)不同時,給這種關系帶來的變化。
從非彈性動力反應分析中可知,鋼筋混凝土結構的R—μ—T三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對于彈性周期較長(大于1.0 s)的結構體系,彈性體系與彈塑性體系的最大位移反應可以認為是相同的,設計時用來確定結構承載力的水平地震作用Vep取值越小(即R越大),結構在非彈性動力反應中達到的位移延性系數μ(最大反應與屈服位移之比)會按同樣的比例增大;對于T較小(在0.12 s~0.5 s之間)的結構體系,R越大,位移延性系數 μ(按 R=以更快的比例增長;而對于T更小(小于0.035)的結構,則只能形成彈性反應,R只能等于1.0;而處在這三個范圍之間的區域的R—μ—T關系則處在相鄰兩個上述特征區的法則之間。
所以,以結構的彈性反映為準,如果我們把結構用來做承載能力設計的地震作用取的越小,即R越大,那么結構在相同的地震作用下達到的非彈性水平位移就越大,對結構的位移延性要求就越高,塑性變形能力就應越好;相反,當R取較小值時(即取較大的“小震”地震作用時)對結構的延性要求就可以越松。
形成上述R—μ—T關系,塑性變形能是個很重要的因素。它是由結構各構件的滯回耗能能力來體現的,從量上可以用力—位移曲線下包圍的面積來衡量。如果我們設計的結構足夠強,以至于在中、大震來了之后整個結構還處于彈性階段,則結構是以相對小的彈性位移和巨大的抗力(小R小μ)來作為代價的。這種設計往往造成“肥梁胖柱”的局面,既不美觀也不經濟。從周期T的角度講,因為結構還處于彈性階段,剛度未退化,周期未折減,由加速度反應譜可知此時結構受的還是一個最高的地震作用。如果按現代抗震設計思路設計同樣一個結構,取中震地震作用的一個折減值作為承載能力設計的地震作用(即R>1),那么相同地震作用下結構就會部分進入塑性變形階段。此時結構的滯回耗能能力(塑性耗能)起了耗散地震能的作用。而且結構一旦屈服進入彈塑性階段,其剛度立即折減,周期減小,從加速度反應譜可知作用于結構上的地震作用也會降低。而延性是保證這種良好狀態的最重要手段,因為延性的高低直接決定了結構屈服后繼續變形和塑性耗能的能力。所以設計承載力取得越低延性要求就越高(用μ來體現)。
根據上述的R—μ—T關系可以看到中國規范的抗震設防目標(即“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對甲、乙、丙三類抗震設防類別并非都是中肯的。在闡述理由之前我們先來個假定,即從純的R—μ—T關系上去考察中國的抗震設防目標,拋開中國規范地震力取得對不對,或中國規范的抗震措施對“μ”反映的到不到位等因素。中國規范對于甲類建筑規定其地震作用高于本地區抗震設防烈度的要求,即取較大地震力做抗震設計,根據R—μ—T關系可知若取較大地震力做抗震設計(取較小R),此時對建筑物的延性要求并不高,然而規范對甲類建筑的抗震措施卻是提出了比本地區抗震設防更高的要求,故可以看出規范對甲類建筑抗震設計的要求從概念上高于“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設防目標的標準。同樣的,規范對乙類建筑的抗震措施也是提出了比本地抗震設防烈度更高的要求,故規范對乙類建筑的要求也是高于抗震設防目標的標準。而規范規定丙類建筑的地震作用和抗震措施均應符合本地區抗震設防烈度的要求,符合普遍意義上的R—μ—T關系。故抗震設防目標就甲、乙、丙三類建筑來說,在概念上對丙類建筑才是最合適的。
而中國規范的現行抗震思路卻與國際上的這種主導形勢有著概念上的差別。中國規范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延性等級是按所處的烈度區來劃分的,規定各種結構,不論處在哪個烈度區都取用一個相同的C(C=0.35),得到一個統一的R=1/C=2.86,從而把用于結構截面承載力和變形驗算的“小震”賦予一個固定的統計定義。而按照R—μ—T關系,對統一的R值,也即用于設計的地震作用相對于該烈度區中震的比值如果不變,則對結構的延性要求也應是相同的(即μ的取值也應是相同的),而與處在什么烈度區沒關系。但實際上規范中規定的措施是9度區最嚴,8度區次之,7度區最松,也就是說9度區結構延性最強,8度區次之,7度區最弱。雖然中國規范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為了考慮各類結構及同一類結構中不同組成部分對延性的不同需求,建立了“抗震等級”的概念,但中國這套做法到底存在什么問題,在什么情況下會出現問題,只有針對各烈度區進行一系列非線性動力反應分析檢驗才能得出結論。
3 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核心抗震措施
抗震措施是結構延性能力的根本保證,延性要求越高,抗震措施越嚴。對于鋼筋混凝土,抗震措施主要包括內力調整措施和抗震構造措施。新西蘭知名教授Robert Park和Thomas Paulay首先對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抗震措施提出了較為系統的闡述,他們取名這套理論為能力設計(capacity design),現已被世界各國的抗震界普遍接受。其基本內容:1)人為增大柱子的抗彎能力,而不加大梁的抗彎能力,使得框架的塑性鉸更多的出現在梁端,而不是柱端,從而形成以梁端出鉸為主的塑性耗能機構,即“強柱弱梁”措施。2)人為加大柱端、梁端和節點的組合剪力值,也就是人為加大這些部位相對于正截面承載能力的抗剪能力,使得結構在大震引起的交替非彈性變形過程中其任何構件都不會先發生剪切破壞,即“強剪弱彎”措施。3)在通過第2)條防止了剪切破壞后,根據第1)條引導形成的塑性耗能機構,應通過抗震構造措施或限制條件來保證形成塑性鉸的部位具有足夠的塑性變形能力和塑性耗能能力,即保證足夠的延性。
中國規范雖然沒有直接使用“能力設計”這個詞,但上述三點內容已得到了體現,并成為我國鋼筋混凝土結構“抗震措施”的同義詞。由于抗震結構延性要求可能不同,因此上述“能力設計”三項措施的嚴格程度也就有所區別。雖然中國規范對鋼筋混凝土延性等級的劃分以烈度取為主要依據(如前所述這在概念上與R—μ—T規律相矛盾),但是還要考慮各類結構以及同一類結構中不同組成部分對延性的不同需求,因此中國規范建立了“抗震等級”(即抗震措施的等級)的概念,并將其分為一、二、三、四級。在對內力調整措施和抗震構造措施做出規定時只需按給出各抗震等級的相應規定就全部清楚了,這樣用起來會比較方便。所以也有人說中國規范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一種揚長避短的措施。
4 結語
基于以上對鋼筋混凝土結構現代抗震思路的討論,并通過對國內外現代抗震思路的發展的討論和總結,得出以下結論:
1)對結構抗震設計最有意義的是結構最大地震反應。振型分解反應譜法和底部剪力法都是計算多自由度彈性體系最大地震反應的方法。2)采用振型分解反應譜法計算結構最大地震反應精度較高,但計算量較大,必須通過計算機計算。
[1]白紹良.鋼筋混凝土抗震結構性能與設計[D].重慶:重慶大學土木工程學院,2005.
[2]沈聚敏,周錫元,高小旺,等.抗震工程學[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0.
[3]洪 鑫.建筑結構隔震減震技術研究[J].山西建筑,2011,37(11):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