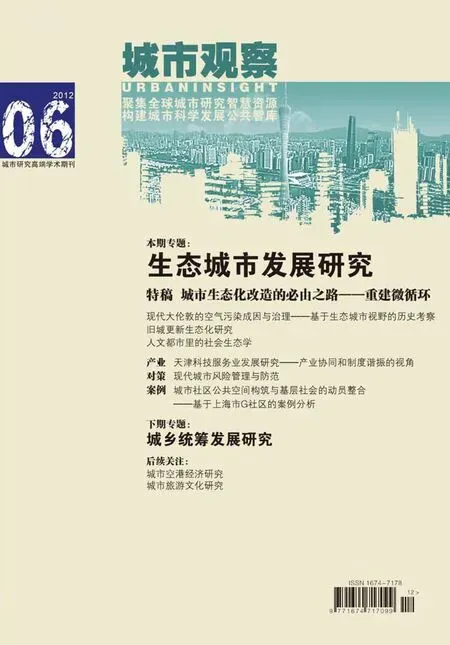從政府主導(dǎo)到社會主導(dǎo):城市基層治理單元的再造
——以新加坡社區(qū)發(fā)展為參照
◎ 袁方成 耿 靜
從政府主導(dǎo)到社會主導(dǎo):城市基層治理單元的再造
——以新加坡社區(qū)發(fā)展為參照
◎ 袁方成 耿 靜
在基層群眾自治中,社區(qū)作為城市基層治理的基礎(chǔ)單元,社區(qū)的治理和發(fā)展已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的實踐經(jīng)驗仍顯不足,社區(qū)自主性和政府治理功能的發(fā)揮,有待進(jìn)一步健全和完善,社區(qū)的自主性還不強(qiáng)。本文基于對新加坡社區(qū)的發(fā)展和建設(shè)過程的考察,從而討論和歸納新加坡城市社區(qū)治理的模式轉(zhuǎn)換及其特點,新加坡政府推動之下社區(qū)力量的崛起、社會自主性的轉(zhuǎn)換是城市基層治理的主要特點。新加坡在社區(qū)治理方面積累的豐富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對于推動我國城市社區(qū)治理的完善和發(fā)展,具有現(xiàn)實而直接的借鑒價值。
城市社區(qū) 基層治理 政府主導(dǎo) 新加坡
一、社區(qū)與社區(qū)發(fā)展:城市基層治理的基礎(chǔ)單元
正如研究城市社區(qū)的著作《跨越邊界的社區(qū)》中所言,城市社區(qū)猶如海洋上的一個個島嶼表面上獨立,但在水面下卻是相互連接著的——所有社區(qū)的社會組成方式都能夠發(fā)生溝通和相互交錯。社區(qū)與城市的關(guān)系同樣如此。“只有一個個社區(qū)和諧了,城市才能和諧,社會才能和諧”。城市基層治理的基礎(chǔ)單元是社區(qū),它不僅是社會的細(xì)胞和基礎(chǔ),也是國家治理的細(xì)胞和基礎(chǔ),更是社會現(xiàn)代化和城市現(xiàn)代化的重要基礎(chǔ)。社區(qū)是聯(lián)系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直接紐帶,社區(qū)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直接影響到城市治理的良性運轉(zhuǎn)與可持續(xù)發(fā)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的城市基層治理體系進(jìn)行了一系列改革,實行黨政分開、政社分開,取消了街道革委會和革命居民委員會,恢復(fù)了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以居民委員會為載體的社區(qū)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成為實現(xiàn)我國城市基層民主治理的正當(dāng)性路徑選擇①。在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城市基層治理問題被提升到黨和國家的發(fā)展戰(zhàn)略高度,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關(guān)乎我國城市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大局,成為既事關(guān)長遠(yuǎn)又非常緊迫的現(xiàn)實課題。我國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然而客觀上看,發(fā)展過程中也面臨著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一是社區(qū)內(nèi)部組織體系較為單一,政府仍主要以強(qiáng)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對社區(qū)進(jìn)行管理;二是社區(qū)公共服務(wù)和管理的能力不足,削弱了社區(qū)居民對社區(qū)和基層政府公共權(quán)威的認(rèn)同度;三是社區(qū)居民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的積極性不高,各類社區(qū)和社會組織在社區(qū)治理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發(fā)揮。
從學(xué)界的研究來看,隨著國家對社區(qū)建設(shè)的推進(jìn),“社區(qū)治理”、“善治”等新詞匯的使用頻率不斷增加,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日益豐富,對社區(qū)治理中政府與社會關(guān)系的認(rèn)識也在不斷深化。“政府—社會”互動的社區(qū)治理模式②日益受到學(xué)者們的關(guān)注和青睞,俞可平(2000)指出,基層治理要強(qiáng)調(diào)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良好合作,治理離不開國家,更離不開社會,治理的最終目標(biāo)是善治,意味著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③;治理理論凸顯了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實現(xiàn)非零和博弈關(guān)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種新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guān)系范式(郁建興、呂明再,2003④;蘭蘭、趙妮婭,2004⑤);魏娜(2003)則認(rèn)為社區(qū)治理是通過政府與社區(qū)組織、社區(qū)居民、非營利組織的共同努力改善社區(qū)環(huán)境,促進(jìn)社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提高社區(qū)居民生活質(zhì)量,最終走向“善治”的過程⑥。
在各國社區(qū)治理的實踐中,新加坡無疑是突出的典范之一。由原來破舊的組屋經(jīng)過三個五年計劃已經(jīng)變成令世人羨慕的花園城市,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區(qū)組織也不斷地向現(xiàn)代社區(qū)體系轉(zhuǎn)變,社區(qū)的快速發(fā)展成為新加坡發(fā)展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新加坡堅持“政府主導(dǎo),強(qiáng)化組織;統(tǒng)一指導(dǎo),民主自治;以人為本,社會參與”的理念,著力建設(shè)文明和諧社區(qū),有效地實現(xiàn)了政府對社區(qū)建設(shè)的科學(xué)管理,呈現(xiàn)出環(huán)境優(yōu)美、文化繁榮、關(guān)系融洽的良好景象。新加坡政府對于城市社區(qū)初期發(fā)展的主導(dǎo)和扶持、社區(qū)力量的動員和培育以及政府與社會力量的良性互動成為其社區(qū)治理成功的基本經(jīng)驗。因此,有必要對新加坡城市社區(qū)的發(fā)展歷程和建設(shè)模式進(jìn)行研究,從而發(fā)掘出推動我國城市社區(qū)治理的有益經(jīng)驗和借鑒。
二、政府推動下的社會崛起:社區(qū)組織體系的構(gòu)建
(一)組屋社區(qū)的全覆蓋:政府“造房”占主導(dǎo)
在新加坡社區(qū)建設(shè)的歷程中,不管是組屋的建設(shè)還是后來的翻新工程,政府是主要的規(guī)劃者與實施者,“組屋”計劃的發(fā)展即是新加坡的社區(qū)發(fā)展史,原有的鄉(xiāng)村社區(qū)也在政府的主導(dǎo)下悄然改變,在新加坡從農(nóng)村走向都市的過程中,城市社區(qū)的雛形便顯現(xiàn)出來。新加坡的“社區(qū)”可以這樣定義:由政府引導(dǎo)規(guī)劃固定范圍內(nèi)的社會成員生活、居住、互動的固定場域⑦。
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新加坡160萬人口中只有不到一成的人家有自己的房子,超過50萬人居住在狹小擁擠的陋屋里。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開始執(zhí)行“居者有其屋政策”,設(shè)立了建屋發(fā)展局,給了它充分的財政、法律和政治支持,開始大興土木地為民眾建造公共住房。新加坡政府對社區(qū)有著比較嚴(yán)格的規(guī)劃和劃分,一般是以公共組屋⑧區(qū)為單位,由6—10座組屋(15000—25000戶)居民組成一個社區(qū),每個社區(qū)都設(shè)有一個自主管理組織——居民(鄰里)委員會,每座組屋還成立有業(yè)主管理委員會,由業(yè)主投票選舉委員會成員⑨。這是現(xiàn)今新加坡社區(qū)的典型形態(tài)。1960—1975年間,新加坡政府實施了“組屋”建設(shè)的三個五年計劃,由政府主導(dǎo)實施“居者有其屋”政策,其間共修建公共組屋55000套。在第一個五年建屋計劃(1961-1965年)完成時,55000套公共組屋拔地而起,比殖民政府改良信托局建造的房屋多兩倍,二十五萬人的住房問題得到解決。第二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為35萬人新建了6.7萬套住房,環(huán)繞新加坡市區(qū)的貧民窟在這個時期基本消失,1974年3月底,在市中心或是中心邊緣的貧民窟已經(jīng)有75%被清除⑩。第三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新建了十萬套住房,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建造的組屋社區(qū)內(nèi)。
1980年前后,新加坡政府為了給居民提供更高質(zhì)量的居住環(huán)境,開始更加注重住房修建的規(guī)劃,同時對過去修建的房屋進(jìn)行翻修,政府不間斷地對年久的組屋加以維修,基本上是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另外是相配套的公共設(shè)施的修建,在組屋中間都要有綠色人行通道、綠地、停車場。為了促進(jìn)族群之間的融合和生活和諧,新加坡政府規(guī)定凡是遷居到組屋區(qū)的各族居民必須采取抽簽制,以確保每一座組屋都有比例均衡的各族居民。從1989年開始,新加坡政府在組屋區(qū)更是實行了種族限額制,規(guī)定每個組屋鄰里和各座組屋的各族群居民必須達(dá)到一定的比例,以鼓勵各族居民之間互相交往,避免出現(xiàn)單一族群聚居的現(xiàn)象。每座組屋都有大小不同的面積,讓不同收入的各族家庭生活在一起,共同使用兒童游樂場和健身園地等公共設(shè)施。
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一直沿用至今,迄今已建造了90萬套公共住房,8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積從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方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狀況得到實質(zhì)改善。通過政府主導(dǎo)的“組屋”社區(qū)計劃,原有的傳統(tǒng)社區(qū)形態(tài)被改變,新的現(xiàn)代社區(qū)體系也逐步在建立,社區(qū)組織越來越發(fā)達(dá),鄰里間關(guān)系也越來越和諧。
表1 新加坡建屋發(fā)展局“居者有其屋”計劃實施情況(1980—2008)

表1 新加坡建屋發(fā)展局“居者有其屋”計劃實施情況(1980—2008)
修建的組屋數(shù)量 售出的組屋數(shù)量 居住在公共組屋的人數(shù)比例(%)1980 18421 23234 73 1985 46370 34856 84 1990 13739 13692 87 1995 26185 27776 86 2000 27678 26329 86 2005 5673 10101 83 2008 3154 8537 82
(二)規(guī)模設(shè)置與組織體系:社區(qū)和社會力量的崛起
新加坡社區(qū)建設(shè)的特點及優(yōu)勢所在,即在政府主導(dǎo),尤其在社區(qū)的規(guī)劃與設(shè)置上,顯得層次性非常清晰,規(guī)模設(shè)置上同質(zhì)性比較明顯。在社區(qū)建設(shè)的組織體系方面,除了政府內(nèi)部的社區(qū)管理與指導(dǎo)組織發(fā)達(dá)之外,還格外注意社區(qū)自組織的培育,管理組織和社區(qū)自組織形成了有效的網(wǎng)絡(luò)化管理模式。
新加坡居住區(qū)規(guī)劃建設(shè)理論主要源自20世紀(jì)30年代歐美“鄰里單元(Neighborhood Unit)”規(guī)劃理論,通過近40年的實踐,新加坡形成其居住區(qū)規(guī)劃結(jié)構(gòu)模式,并嚴(yán)格執(zhí)行。嚴(yán)格意義上來說,在新加坡,標(biāo)準(zhǔn)的社區(qū)指的是鄰里中心,其標(biāo)準(zhǔn)在8000戶左右。目前,全國共有組屋社區(qū)493個,從其內(nèi)容結(jié)構(gòu)來看,一個鄰里組團(tuán)中心,一般由4—8幢組屋組成,約1000-2000個住戶,在這里設(shè)有兒童游樂場、便利店等;一個鄰里中心一般含6—7個鄰里組團(tuán),約6000—12000個住戶,根據(jù)居住人口的數(shù)量,一般建有一幢建筑面積5000—10000平方米的綜合樓,內(nèi)設(shè)有商場、銀行、郵政、診療所等。
新加坡的社區(qū)管理組織,要求實行以社區(qū)全體成員的積極參與和靈活分散為主要特點的網(wǎng)絡(luò)管理方式,其顯著特點是:民眾參與度高、專業(yè)的分工管理與服務(wù)、事權(quán)與責(zé)任明晰。這對社區(qū)管理來說是一種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的現(xiàn)代化管理方式。新加坡的社區(qū)管理組織是非常多元的,既有政府下設(shè)部門,也有官方組織,還有群眾性組織,三者有機(jī)互動,形成了對社區(qū)的“網(wǎng)絡(luò)化”管理和服務(wù)。社區(qū)自組織是政府培育的新的社會力量,嵌入社區(qū)內(nèi)部的基層組織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公民咨詢委員會(也稱居民顧問委員會),這是政府指導(dǎo)下的機(jī)構(gòu),每一個選區(qū)設(shè)立一個公民咨詢委員會,它在社區(qū)組織中的地位最高。其主要職責(zé)是:負(fù)責(zé)社區(qū)內(nèi)的公共福利服務(wù),協(xié)調(diào)另外兩個委員會(居民聯(lián)絡(luò)所、居民委員會)和其他社區(qū)內(nèi)組織的工作;公民咨詢委員會根據(jù)社區(qū)內(nèi)居民的要求與政府溝通,在涉及社區(qū)的重大問題時,如公共交通線路的設(shè)置與走向等,向政府作出建議,維護(hù)居民權(quán)益;在選區(qū)里組織、領(lǐng)導(dǎo)和協(xié)調(diào)社區(qū)事務(wù),還會把居民的需要和問題反映給政府,也把政府的有關(guān)活動安排和政策信息傳達(dá)給居民;負(fù)責(zé)募集社區(qū)基金,用于增進(jìn)貧困和殘障人士的福利、提供獎學(xué)金和援助其他社區(qū)項目。二是民眾俱樂部(也稱社區(qū)中心管理委員會),民眾俱樂部的活動經(jīng)費來源于民間,民眾俱樂部的主要職能有:民間籌款興建各種體育或休閑活動設(shè)施,制定從幼兒體育活動到中青年計算機(jī)培訓(xùn)等的一系列計劃,組織舉辦諸如文化、教育、娛樂、體育、社交等各種有益的活動,以增進(jìn)社區(qū)和諧。民眾俱樂部的活動經(jīng)費來源于民間,人力來源于民眾的志愿性參與,這是社會力量興起和發(fā)展的有力表現(xiàn)。三是居民委員會(相當(dāng)于我國的社區(qū)居委會),在所有的公共組屋區(qū)都設(shè)有居委會,通過組織形式多樣的活動來促進(jìn)鄰里和睦、種族和諧和社會團(tuán)結(jié),這些活動包括:組屋舞會、鄰里守望、民防演練、家政課程、教育旅游、民眾對話會、唱歌、社區(qū)聯(lián)歡會等。這些活動使居住在同一組屋區(qū)的居民彼此增進(jìn)認(rèn)識與了解,更好地理解和響應(yīng)政府的政策措施。在新加坡,組屋社區(qū)的三個自組織的工作者承擔(dān)的工作完全是兼職的、義務(wù)的,這樣也節(jié)省了大量的費用。
新加坡政府統(tǒng)一實施組屋社區(qū)發(fā)展計劃,使原有的鄉(xiāng)村社區(qū)在建設(shè)大潮中悄然改變,城鄉(xiāng)融合步伐大舉加快,原來的農(nóng)村區(qū)域也逐漸被開發(fā)成“花園城市”的一部分,現(xiàn)代化的高樓組屋取代了傳統(tǒng)的村落,與此同時,政府也特別重視各民族的融合和居民對社區(qū)和國家認(rèn)同感的培育,這正是政府鼓勵居民、家庭共同參與到社區(qū)建設(shè)中來的有力措施。由此看來,新加坡社區(qū)不管是翻蓋還是內(nèi)部融合,以及社區(qū)的結(jié)構(gòu)和體系的構(gòu)建,政府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是新加坡建設(shè)初期的主要力量,同時也在有意培育社會力量的壯大,政府推動下的社會崛起正是新加坡社區(qū)建設(shè)過程的有力體現(xiàn)。
三、社會自主性的轉(zhuǎn)換:社區(qū)功能擴(kuò)展與資源配置
新加坡從國情出發(fā),提出了具有親和力的社區(qū)建設(shè)理念:個體——具有社會責(zé)任感;家庭——溫馨而穩(wěn)固;社群——積極并有愛心;社會——富有凝聚力和復(fù)原力,旨在打造“溫馨”的家園共同體。在社區(qū)的建設(shè)初期,大力扶植社區(qū)組織力量的孕育和發(fā)展,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到社區(qū)的建設(shè)中。隨著社區(qū)功能的不斷擴(kuò)展,以及社區(qū)資源配置方面作用的日益發(fā)揮,社區(qū)和社會組織的自主性逐步凸顯出來。
(一)社區(qū)的功能擴(kuò)展:社會共同體意識的凝聚
社區(qū)是居民生活的共同體,具有滿足居民生活的各種功能。其一是服務(wù)功能,如社區(qū)基礎(chǔ)設(shè)施的供給與維護(hù)、家事服務(wù)和保健服務(wù)等。家庭服務(wù)中心是一個以鄰里為基礎(chǔ),提供家事服務(wù)的福利性機(jī)構(gòu),承擔(dān)社會事務(wù)和社會福利工作職能(類似民政工作),開展個人與家庭輔導(dǎo)、信息與中介、家庭教育、專業(yè)服務(wù)及義工培訓(xùn)等服務(wù)。新加坡社區(qū)醫(yī)院作為輔助醫(yī)療設(shè)施,是國家醫(yī)療保健體系的補(bǔ)充,收費低廉,重點滿足老年病人的需求,社區(qū)醫(yī)院一般與區(qū)域醫(yī)院為鄰,在某種程度上與區(qū)域醫(yī)院共享醫(yī)療資源,病人康復(fù)護(hù)理可轉(zhuǎn)入社區(qū)醫(yī)院。
其二是綜合管理功能,新加坡社區(qū)管理的組織者由兩方面組成:一是選區(qū)層次上的社區(qū)事務(wù),由市鎮(zhèn)理事會組織,其成員主要由公民咨詢委員會和管委會成員組成。二是居民區(qū)層次上的社區(qū)事務(wù),由居委會組織,這是一個民間性質(zhì)的組織,給了居民一個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的平臺,新加坡社區(qū)管理的內(nèi)容主要有對區(qū)內(nèi)大型公共設(shè)施的管理、美化公共居住環(huán)境、維護(hù)社區(qū)治安環(huán)境、開展社會公益活動、增強(qiáng)社區(qū)凝聚力,密切鄰里關(guān)系等。
其三是價值引導(dǎo)功能,新加坡領(lǐng)導(dǎo)人特別注重與強(qiáng)調(diào)通過社區(qū)組織來培育民眾的國家意識和公民意識。通過社區(qū)組織的宣傳教育,潛移默化地使具有不同種族、不同社團(tuán)和不同區(qū)域的居民相互交往,相互關(guān)心,遵循得到國家倡導(dǎo)和社會明確的價值觀和模式,保障社區(qū)中各個階層的民眾和諧生活,因此,新加坡的社區(qū)組織在新加坡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演變的過程中功不可沒。
其四是政治聯(lián)絡(luò)功能。實際上,新加坡社區(qū)組織如人民協(xié)會和民眾聯(lián)絡(luò)所的建立與發(fā)展就是在人民行動黨上臺執(zhí)政初期與下層華人社會聯(lián)系渠道中斷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因此它們的成立被賦予更多的政治含義。人民行動黨上臺執(zhí)政初期,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時,便決定建立人民協(xié)會,當(dāng)時給人民協(xié)會制定的宗旨便是協(xié)助政府,聯(lián)合民眾克服多種困難,促進(jìn)人民的和諧共處、社會的安寧與繁榮。最初,人民協(xié)會的主要基層組織便是民眾聯(lián)絡(luò)所,它通常成為向民眾解釋政府政策,傳播正式信息的主要場所和渠道。隨著新加坡民眾公民意識的不斷增強(qiáng),聯(lián)絡(luò)所的工作也更加有序和規(guī)范化,而且具有極強(qiáng)的政治色彩,因為民眾聯(lián)絡(luò)所從表面上看來不是一級政府或政治機(jī)構(gòu),只是一個社區(qū)的文娛交流中心,但實際上,政府在相當(dāng)程度上就是想通過這種渠道來吸引民眾、組織民眾、教育民眾和導(dǎo)向民眾,從而來擴(kuò)大人民行動黨的社會基礎(chǔ)。
(二)社區(qū)資源配置和管理:社區(qū)自主性的轉(zhuǎn)換
新加坡社區(qū)規(guī)劃建設(shè)中使用的一些關(guān)于設(shè)施配備的標(biāo)準(zhǔn)。如新加坡人用餐的“飯攤”,按規(guī)劃標(biāo)準(zhǔn),每個住宅單位要配備一組約時“飯攤”。而在新城建設(shè)時,“飯攤”要設(shè)在新城中心。同樣,有關(guān)宗教活動的設(shè)施,如清真寺,按照規(guī)劃標(biāo)準(zhǔn)每座新城要建一個,每9000個住宅單位要建一個佛教寺廟,每萬個住宅單位要有一座教堂,每兩座新城要有一個興督教寺廟。而在公共組屋區(qū)的兒童游樂場、健身角落和燒烤設(shè)施等,在新加坡建屋局建設(shè)組屋時已同時興建,在使用過程中市鎮(zhèn)理事會還會根據(jù)居民的意愿改造或新建。
新加坡通過多種渠道并以法律形式使社區(qū)建設(shè)、發(fā)展和管理的經(jīng)費來源得到保障。社區(qū)活動經(jīng)費主要來源于政府撥款和社會贊助。政府撥款包括行政經(jīng)費、活動經(jīng)費及專項經(jīng)費,行政經(jīng)費主要用于維持人民協(xié)會和民眾聯(lián)絡(luò)所(民眾俱樂部)的日常運作,舉行大型活動或其他專項支出由社區(qū)組織申請,政府根據(jù)需要補(bǔ)助。社會贊助款項主要由企業(yè)、其他組織機(jī)構(gòu)贊助以及個人募捐獲得,為了鼓勵社會對社區(qū)活動的贊助,政府制定了經(jīng)費配搭計劃(政府按捐款額度1:1比例配套,如果是長期固定捐款,政府則按1:3比例配套),鼓勵企業(yè)、社會機(jī)構(gòu)和個人對社區(qū)活動進(jìn)行長期贊助。社區(qū)公共設(shè)施建設(shè)和維修及組屋中期翻修等經(jīng)費則由政府按計劃列支,組屋內(nèi)的翻修和設(shè)施的改建則按照居民自愿的原則主要由居民籌集,政府給予適當(dāng)補(bǔ)助。社區(qū)活動各項經(jīng)費支出均有嚴(yán)格規(guī)定,必須經(jīng)相應(yīng)的理事會、委員會或所有居民討論通過,同時幾乎所有開支項目都是按費用最節(jié)約的宗旨實行市場化運作。政府撥款和社會贊助重在養(yǎng)事,除社理會和民眾俱樂部的全薪人員(占社區(qū)服務(wù)和工作人員的極少數(shù)工資)由政府負(fù)責(zé)外,其余社區(qū)組織理事會、董事會、委員會成員及工作人員等均是自愿者,不領(lǐng)薪酬。
由此看來,新加坡社區(qū)的服務(wù)和管理功能、資源的配置和管理都充分尊重民意,并且從意識層面對居民進(jìn)行引導(dǎo),鼓勵社會力量的壯大,政府允許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建設(shè)社區(qū),此時的社區(qū)發(fā)展已經(jīng)不同于社區(qū)建設(shè)初期,政府與社會的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發(fā)生改變,在社區(qū)的發(fā)展過程中,社區(qū)社會力量逐漸壯大,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自我修復(fù)的能力大大提高,社區(qū)的社會力量已經(jīng)逐漸在進(jìn)行自主性的轉(zhuǎn)換。
四、多元服務(wù)與協(xié)同管理:社區(qū)發(fā)展的機(jī)制創(chuàng)新
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新加坡社區(qū)發(fā)展的新面貌逐步顯現(xiàn)出來,一個個充滿活力、和諧文明、關(guān)系融洽、環(huán)境優(yōu)美的城市基層單元成為新加坡社會發(fā)達(dá)程度的重要標(biāo)志。政府依法指導(dǎo)與社區(qū)高度自治之間實現(xiàn)了有機(jī)而密切的結(jié)合,發(fā)展機(jī)制的創(chuàng)新程度達(dá)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新加坡社區(qū)以建設(shè)“服務(wù)型社區(qū)”為目標(biāo),逐步形成完善了“以政府為主導(dǎo),法定機(jī)構(gòu)組織、民眾參與”的社區(qū)管理機(jī)制。新加坡政府在社區(qū)主要是本著“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的理念,貫徹“建立賦有結(jié)合力及復(fù)原力的社會,具有人民歸屬感的社區(qū),賦有社會責(zé)任感的個體”的指導(dǎo)思想,大量開展為“社區(qū)居民的基本日常生活服務(wù),解決生活便利問題”的社區(qū)服務(wù)。所謂以政府為主導(dǎo),即由新加坡社會發(fā)展、青年和體育部下屬的5個社區(qū)發(fā)展理事會對全國社區(qū)管理總負(fù)責(zé),開展社會援助服務(wù),進(jìn)行行政管理,發(fā)展社區(qū)社會公益事業(yè),維護(hù)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同時民眾也積極參與社區(qū)事務(wù),積極參加志愿者活動,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具有歸屬感和社會責(zé)任感的社區(qū)生活。
其次,將“行政管理市場化運作”與“基層社區(qū)服務(wù)義工化”有機(jī)地結(jié)合起來,形成了“和諧社區(qū)”建設(shè)的長效機(jī)制。新加坡政府在社區(qū)建設(shè)中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幾個單位有:建屋發(fā)展局、市區(qū)重建局、市鎮(zhèn)理事會等法定機(jī)構(gòu),既代表政府行使本部門的行政管理職能,又是適應(yīng)政府調(diào)控市場、市場引導(dǎo)經(jīng)濟(jì)這一干預(yù)模式的產(chǎn)物,是獨立核算、自主經(jīng)營的國有經(jīng)濟(jì)實體,這使得它們既注重滿足民意又注重控制成本,既注重有效管理又注重為居民服務(wù),既注重社會效益又注重經(jīng)濟(jì)效益,責(zé)任、利益十分明確,同時政府在財政預(yù)算充分保證供給法定機(jī)構(gòu)用于社區(qū)的建設(shè)資金的基礎(chǔ)上,也鼓勵社區(qū)組織采取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從社會組織、企業(yè)、個人處募集社區(qū)建設(shè)資金,使社區(qū)建設(shè)的投入、產(chǎn)出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huán),有利于長效管理和發(fā)展。同時在社區(qū)基層各個法定機(jī)構(gòu)和社會組織中工作的一些主席、委員、工作人員,有不少人是不收受報酬只愿為社會和居民服務(wù)的義工,他們既降低了基層組織的運行成本,也弘揚了一種“人人關(guān)愛社會”的精神,為社會和諧增添了不少溫馨,有利于長效機(jī)制的形成。
新加坡社區(qū)建設(shè)一方面注重政府的主導(dǎo),在政府部門設(shè)置相關(guān)的社區(qū)管理機(jī)構(gòu),并有相關(guān)半官方組織參與管理;另一方面,新加坡組織注重培育民間力量,使其發(fā)展壯大,并參與到社區(qū)管理中去。政府的指導(dǎo)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政府加強(qiáng)宏觀政策上的落實和發(fā)展方向上的正確引導(dǎo)。在新加坡,政府通過對社區(qū)組織的物質(zhì)支持和行為引導(dǎo),把握社區(qū)活動的方向,而且社區(qū)的相當(dāng)一部分活動本身就是政府發(fā)起的,其中某些環(huán)節(jié)還受到政府的資助。其次,制定和指導(dǎo)科學(xué)的、前瞻性的社區(qū)統(tǒng)一規(guī)劃。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負(fù)責(zé)制定社區(qū)發(fā)展計劃和評估標(biāo)準(zhǔn),社區(qū)發(fā)展理事會、民眾聯(lián)絡(luò)所、居民委員會等機(jī)構(gòu)在政府指導(dǎo)下自主活動,并及時向政府反饋民眾意見。各政府部門根據(jù)社區(qū)居民需要,調(diào)整規(guī)劃和管理方式,按照是否達(dá)到社會服務(wù)的標(biāo)準(zhǔn),評估各自治組織的業(yè)績,下?lián)芑顒咏?jīng)費。政府行政部門、社區(qū)管理機(jī)構(gòu)、基層自治組織及社會團(tuán)體之間職責(zé)分明,上下貫通,形成了科學(xué)、合理、靈活、自治的社區(qū)建設(shè)模式。此外,政府充分給予社區(qū)自治組織發(fā)育空間,社區(qū)民間組織發(fā)育完全,通過自助和他助,分擔(dān)了政府和社區(qū)居委會的大量管理和服務(wù)工作,具體來講就是,國家統(tǒng)一規(guī)劃,政府有關(guān)部門負(fù)責(zé)制定社區(qū)發(fā)展計劃和評估標(biāo)準(zhǔn),居民聯(lián)絡(luò)所、居民委員會等機(jī)構(gòu)在政府的指導(dǎo)下自主活動,并及時向政府反饋民眾意見。
新加坡從多元種族、雜亂無章、一盤散沙的局面到如今多民族和睦共生,從建國初期多數(shù)民眾的棚戶生活到現(xiàn)在“花園城市”中社區(qū)居民的安居樂業(yè),無論是物質(zhì)文明建設(shè)還是精神文明建設(shè),無論是行政體制改革還是基層民主政治的完善,其社區(qū)發(fā)展的成就彰顯于世間。綜合看來,政府和社會在社區(qū)建設(shè)和發(fā)展的不同階段發(fā)揮了不同的作用,由初期的政府主導(dǎo)的造房和社區(qū)規(guī)模和組織體系的建設(shè)到社區(qū)功能和機(jī)制的更新,社區(qū)的發(fā)展從政府主導(dǎo)到政府推動下的社會崛起再到社會力量的自主性轉(zhuǎn)換,這是社區(qū)發(fā)展良性的連續(xù)統(tǒng)一,這種發(fā)展路徑完全適合新加坡城市的基本國情,只有政府與社會共同參與到城市基層治理的任務(wù)中,才能真正地使各項利益最大化進(jìn)而達(dá)到善治。
五、推進(jìn)我國社區(qū)建設(shè)和發(fā)展的啟示與借鑒
隨著經(jīng)濟(jì)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jié)構(gòu)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diào)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在我國已進(jìn)入發(fā)展的關(guān)鍵時期、改革的攻堅時期和社會矛盾頻發(fā)時期,社區(qū)建設(shè)作為一項基礎(chǔ)性、綜合性的工作,蘊(yùn)涵著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桶l(fā)展空間。在充分挖掘我國社區(qū)建設(shè)潛力的同時,借鑒新加坡社區(qū)獨特的成功經(jīng)驗,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第一,構(gòu)建完善的社區(qū)治理框架體系,充分發(fā)揮政府的宏觀指導(dǎo)和引導(dǎo)作用。新加坡政府在城市社區(qū)的翻新和維護(hù),以及社區(qū)服務(wù)和管理方面都始終起著引導(dǎo)和指導(dǎo)的作用。在社區(qū)建設(shè)和治理過程中,政府要做好自己的宏觀指導(dǎo)和規(guī)劃職能,首先制定社區(qū)發(fā)展的相關(guān)政策,為社區(qū)發(fā)展提供健康的環(huán)境,確保社區(qū)治理參與主體的法律地位;同時建立健全社區(qū)內(nèi)部的各項制度,使所有治理主體都能依法進(jìn)行。其次要尊重民意,及時了解居民的需求,政府掌握著大量的資源,有能力組織人力及物力開展社區(qū)調(diào)查研究以及信息收集工作,便于根據(jù)居民需求進(jìn)行社區(qū)規(guī)劃;同時強(qiáng)化社區(qū)服務(wù)功能,做好社區(qū)發(fā)展的協(xié)助工作,社區(qū)的發(fā)展能力有限,政府必須協(xié)助社區(qū)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促進(jìn)社區(qū)的發(fā)展。只有充分尊重居民,才能樹立和鞏固“社區(qū)是我家,建設(shè)靠大家”的社區(qū)公共觀念,社區(qū)和政府的威信才能提高,社區(qū)居民才能積極參與到社區(qū)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的隊伍中來。再次,政府要注重社區(qū)其他力量的培育,鼓勵更多的社區(qū)成員和組織參與到社區(qū)建設(shè)的隊伍中來,城市社區(qū)不同于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社區(qū),城市社區(qū)的居民歸屬感較低,居民對社區(qū)秩序和權(quán)威的認(rèn)可度較低,參與積極性程度不高,政府要注重與強(qiáng)調(diào)通過社區(qū)組織來培育民眾的國家意識和公民意識,通過社區(qū)組織的宣傳教育,潛移默化地使具有不同社團(tuán)和不同區(qū)域的居民相互交往,相互關(guān)心,保障社區(qū)中各個階層的民眾和諧生活。總之要充分發(fā)揮政府在社區(qū)組織和建設(shè)的宏觀指導(dǎo)作用。
第二,動員和引導(dǎo)社區(qū)與社會組織力量積極參與,逐漸實現(xiàn)社區(qū)自主性轉(zhuǎn)換。正如新加坡社區(qū)建設(shè)的過程來看,社區(qū)居民和社會組織力量在政府的培育下參與意識逐漸變強(qiáng),組織形式豐富多樣并真正致力于社區(qū)的管理和服務(wù)中來,社區(qū)和社會組織力量的發(fā)展以及功能的發(fā)揮成為新加坡社區(qū)建設(shè)和發(fā)展不可缺少的因素。隨著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時期的到來,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各類社會組織的興起,參與社區(qū)治理的作用不容忽視。社會組織日益在基層社區(qū)建設(shè)方面發(fā)揮出較大作用,社區(qū)民間組織在社區(qū)建設(shè)中的作用能夠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得到充分體現(xiàn)。從宏觀層面來看,社區(qū)民間組織的發(fā)展能夠提高社區(qū)內(nèi)的組織化程度,能夠形成分工合理的社區(qū)治理體系,與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動,分擔(dān)社區(qū)治理的責(zé)任和功能,提高整個社區(qū)的運行效能。從微觀層面來看,民間組織在維護(hù)公民利益,吸取建設(shè)資金、完善社區(qū)內(nèi)基礎(chǔ)設(shè)施和各種社會制度和規(guī)則等方面能夠發(fā)揮政府組織不可代替的作用。社會組織的志愿性參與成為現(xiàn)階段社區(qū)治理不可缺少的力量,社會組織要充分發(fā)揮自身的動員力量和建設(shè)職能,在社區(qū)的建設(shè)中抓住機(jī)遇,自我強(qiáng)大、自我修復(fù),在對社區(qū)的服務(wù)和建設(shè)中獲得社區(qū)居民和政府的認(rèn)同,提高自身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的合法性,從而實現(xiàn)社區(qū)自我轉(zhuǎn)型,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在這種互動關(guān)系下,社會組織能夠充分發(fā)揮其自身的能動性和自主性,強(qiáng)化自身合法性地位,成為居民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的橋梁,充分發(fā)揮出其在社區(qū)建設(shè)中的作用 。
第三,創(chuàng)新城市社區(qū)的治理機(jī)制,實現(xiàn)城市基層社會發(fā)展的善治局面。新加坡的社區(qū)管理組織形態(tài)非常多元化,既有政府下設(shè)部門,也有社會組織,還有群眾性組織,三者有機(jī)互動,形成了對社區(qū)的“網(wǎng)絡(luò)化”管理和服務(wù)。政府組織和社會組織共同融入社區(qū)的管理,合作協(xié)同,這就需要轉(zhuǎn)變地方政府職能和觀念,首先要求地方政府對社區(qū)的管理職能和權(quán)限不斷向社區(qū)轉(zhuǎn)移,地方治理形成權(quán)力下放、地方自主管理的格局,社會事務(wù)的管理則更多地由社區(qū)組織承擔(dān)起來,由大政府、小社會的社區(qū)治理模式向小政府、大社會的多元互動治理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整合市場組織、民間力量參與社區(qū)治理,釋放公民社會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的能量,其次非營利組織要加快自身在社區(qū)中的發(fā)展壯大,充分抓住政府建設(shè)社區(qū)的機(jī)遇,爭取有利于非營利組織發(fā)展的社會氛圍,在社區(qū)服務(wù)和建設(shè)過程中,與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動,在注重自身強(qiáng)大的同時進(jìn)行自主性的轉(zhuǎn)換,獲得自身合法性。最后,培育對社區(qū)多元互動關(guān)系的社區(qū)公民認(rèn)同。社區(qū)居民共同體意識和參與意識的提高是社區(qū)治理的當(dāng)務(wù)之急,只有提高社區(qū)居民的參與意識,讓更多的社區(qū)居民參與到社區(qū)的建設(shè)中來,才能與政府與社會組織形成良好的互動,社區(qū)治理主體才能爭取廣泛的社區(qū)居民認(rèn)同,獲得有效的社會基礎(chǔ),贏得廣闊的生存空間。只有明晰政府、社區(qū)和社會組織在社區(qū)治理中的權(quán)利、責(zé)任與義務(wù),整合社區(qū)資源,共同為社區(qū)居民服務(wù),才能更好地滿足社區(qū)公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形成社區(qū)的合作治理局勢,在社區(qū)建設(shè)中,真正達(dá)到善治。
簡言之,充分借鑒新加坡社區(qū)發(fā)展的有益經(jīng)驗,重構(gòu)新型的城市基層治理單元,構(gòu)建政府與社會之間優(yōu)化的治理結(jié)構(gòu),形成多元互動的治理機(jī)制,對于進(jìn)一步推進(jìn)我國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和發(fā)展,保障社會的和諧運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質(zhì)量,將發(fā)揮積極而顯著的作用。
注釋:
①康宇.中國城市社區(qū)治理發(fā)展歷程及現(xiàn)實困境[J].貴州社會科學(xué),2007(2):66-67.
②何海兵.“國家—社會”范式框架下的中國城市社區(qū)研究[J].學(xué)術(shù)綜述,2006(4):96.
③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0.
④郁建興,呂明再.治理:國家與市民社會關(guān)系理論的再出發(fā)[S].求是學(xué)刊,2003.
⑤蘭蘭,趙妮婭.治理視野下我國國家與社會關(guān)系的重構(gòu)[J].行政論壇,2004.
⑥魏娜.我國城市社區(qū)治理模式:發(fā)展演變與制度創(chuàng)新[J].中國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 2003.
⑦Kong L. & Yeoh, B. S. A.: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s in Singapore: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⑧組屋,全稱組合房屋,是由新加坡建屋發(fā)展局承擔(dān)建筑的公共房屋,現(xiàn)今為大部分新加坡人的住所。
⑨引自新加坡政府網(wǎng)http://infopedia.nl.sg/articles/SIP_1589_2009-10-26.html.
⑩Yeh, S. H. K. ed.: Public housing in Singapore: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for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1975.
[1]孫代勇.新加坡加強(qiáng)社區(qū)組織建設(shè)與管理的啟示[N].新重慶,2008.
[2]王世軍.新加坡的社區(qū)組織與社區(qū)管理[J].社區(qū),2002(3):43.
[3]王劍云,韓筍生.杭州與新加坡的城市社區(qū)組織模式比較[J].城市規(guī)劃匯刊,2003(3):28.
[4]羅光華.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模式創(chuàng)新研究[D].武漢大學(xué),2011:118.
[5]張照陽,郭繼遠(yuǎn).政府在城市社區(qū)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法制與社會,2006(19):135.
[6]王靜,張蓉莊,龍玉.民間組織在城市社區(qū)治理中的作用——政府與民間組織互動關(guān)系分析[J].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6(1):93-94.
[7]毛勁歌.基于和諧社區(qū)構(gòu)建的中國城市社區(qū)治理多元互動模式研究[J].湖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 2006(6):64-66.
[8]姚華松,羅萍.新型城市化的建構(gòu)過程與廣州實踐——兼論建設(shè)“智慧廣州”[J].城市觀察, 2012(3):33-36.
[9]袁方成.政府與社會:“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的一種繼替性表達(dá)[J].社會主義研究, 2007(3):62-64.
[10]張靜.國家與社會[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1]Skocpol ,The da.1979.State&Society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and China. Cambridge [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om Government-led to Social-led Reengineering of Citizen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Yuan Fangcheng, Geng Jing
Speaking of citizens’ autonomy,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base unit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At present, 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lack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autonomy and function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Singapore, the paper discusses its characteristics. Promoted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he subject shift of autonomy is the main feature. Lessons from Singapore are of valu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urban community; citizen governance; government-led; Singapore
book=124,ebook=126
C912.81
10.3969/j.issn.1674-7178.2012.06.012
袁方成,華中師范大學(xué)政治學(xué)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中央編譯局博士后,《社會主義研究》編輯部編輯,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地方治理與政府改革。耿靜,華中師范大學(xué)政治學(xué)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責(zé)任編輯:盧小文)
中國博士后科學(xué)基金第五批特別資助項目(2012T50117)、霍英東教育基金會基礎(chǔ)性研究課題(131092)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一般項目(10YJA81003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