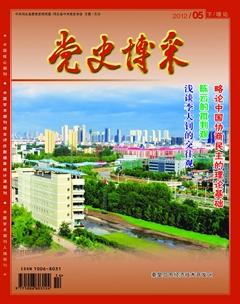紅軍進漳為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奠定的基礎
陳賢濱
[摘要]八十年前紅軍進漳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重要事件,為緊接下來的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經濟、軍事和政治等方面。同時,周恩來在這次戰役中充分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也在客觀上為第四次反“圍剿”勝利提供領導力量上的準備。
[關鍵詞]紅軍進漳;第四次反“圍剿”;基礎
1932年4月20日,毛澤東同志率領由中國工農紅軍一、五軍團組成的東路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擊垮國民黨第49師張貞部隊,一舉攻克漳州,取得了重大勝利。漳州戰役是敵人的“圍剿”與紅軍的反“圍剿”斗爭史上的一場重要戰役,中央蘇區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又進行了贛州、漳州、水口、樂(安)宜(黃)、建(寧)黎(川)泰(寧)和金資等六次進攻戰役,但是漳州戰役對戰略全局影響最大,是毛澤東同志所謂的“一個勝戰”在“關照全局”的重要戰役。楊成武同志曾談到:一九三二年漳州戰役,是紅一、五軍團利用第三和第四次反“圍剿”之間的空隙,為了擴大蘇區、擴大紅軍、籌備物資而打的。[1]而談到為什么要撤出漳州指出:因為第四次反“圍剿”要開始了,要準備進行新的反“圍剿”戰爭……隨后我們部隊就由贛南向宜黃、樂安前進,打下了樂安,至此四次反“圍剿”就揭開了序幕。[2]羅明同志也曾談到:紅軍攻打漳州和勝利回師,正是在粉碎了敵人第三次“圍剿”之后,為了擴展勝利的成果,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發展閩南地方游擊戰爭,收繳敵人的軍事物資,準備進行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軍事戰役。[3]由此可見,漳州戰役是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進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戰役,為緊接下來的第四次反“圍剿”奠定了各個方面的良好基礎,鞏固和發展了中央蘇區,對紅軍粉碎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試從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論述紅軍進漳對第四次反“圍剿”勝利所做出的貢獻。
一、經濟準備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國民黨在軍事上對蘇區進行“圍剿”,在經濟上進行封鎖,造成蘇區根據地內物資緊張,財政十分困難,而沒有根據地戰略后方的支持,蘇區紅軍是無法開展軍事斗爭的。紅軍攻克龍巖后,還向當地商會借款5000塊銀元,待攻克漳州后歸還,可見當時中央蘇區財政困難的程度。漳州是福建較為富庶的地區,攻克漳州有利于籌集款子和物資。紅軍攻克漳州后,共籌款100多萬銀元,繳獲敵人步槍2331支,還有機關槍、山炮、迫擊炮、平射炮等,步槍子彈133200發、炮彈4942發,炸彈242枚、飛機兩架及電話機10部、電臺等軍用物資。做到給每個紅軍戰士發兩雙鞋子,更新一套軍裝,如此整齊的服裝在紅軍史上也是第一次。紅軍將籌集到的銀元、糧食、布匹、藥品等物資運回蘇區,還在長汀舉辦“金山銀山”展覽會,此后又建一座熔銀廠,將銀元重新熔鑄為蘇區貨幣,從而緩解了蘇區財政困難的狀況,穩定了蘇區金融。[4]反“圍剿”斗爭勝利的程度是和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系著的。[5]漳州戰役的勝利,從經濟方面保證了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建設,為紅軍粉碎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資基礎。
二、軍事準備
毛澤東對反“圍剿”的準備工作是有著深入思考的:有時準備過早,會變為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的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系著眼。一般地來說,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后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為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于不敗之地。紅軍的準備退卻是在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6]毛澤東在長汀就東路軍行動問題致電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時提議“政治上必須直下漳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正是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中“創造戰場”的鮮明體現。攻克漳州之后,1932年5月3日毛澤東在復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指出:在三次戰爭以后,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御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包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此次東西兩路軍的行動完全是正確的。東路軍深入漳州決不是主要為著籌款,西路軍的分出也沒有破壞集中的原則。我們已跳出敵人的包圍之外,突破了敵人的東西兩面,因而其南北兩面也就受到我們極大威脅,不得不移轉其向中區的目標,向著我東西兩路軍的行動。[7]由此可見,毛澤東率領紅軍抓住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和第四次反“圍剿”尚未到來的間隙,審時度勢,認識到根據地人民的力量,遠離根據地開展外線作戰,不但未造成對整個戰局發展的不利影響,而且調動了敵人,“撿弱的打”,打亂了敵人的部署。
紅軍進漳后,乘勝追擊,連克龍溪、海澄、平和、漳浦、長泰等縣鎮,幫助閩南黨組織打開革命斗爭新局面,并逐步以龍溪圩為中心,向南靖、平和、漳浦、云霄、龍溪五縣擴大游擊戰爭,創造小紅軍,建立小蘇區。閩南地方黨組織也積極配合紅軍,深入發動群眾,擴大農民武裝,建立紅色政權。紅軍進漳還有力推動了閩南游擊戰爭的開展,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即紅三團。發揮其在中央蘇區前沿,牽制敵軍進攻,配合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重要軍事作用。
同時,紅軍東路軍攻取閩南重鎮漳州,支援了東江根據地人民的斗爭,打亂了廣東軍閥的軍事部署,不得不調整兵力部署,不能舉全力進攻東江,緩和乃至暫時停止了軍事進攻,不僅有力支援了東江軍民的反“圍剿”斗爭,為東江人民革命斗爭造成了有利形勢。東江特委吸取紅軍東路軍的成功經驗,開辟了揭普惠和潮普揭游擊區,并建立了潮澄饒地區第一支紅軍武裝,在潮汕國民黨統治心臟地帶開展游擊戰爭,為東江蘇區與閩西、閩南、中央蘇區打通,完成閩粵贛蘇區連成一片打下了基礎。紅軍進漳贏得了各個根據地鞏固和發展的有利時機,為紅軍順利完成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三、政治準備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斗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紅軍進行軍事斗爭的輿論支持。我們要明確、堅決而充分地告訴人民,關于敵人進攻危害人民的嚴重性,紅軍的優良傳統,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愿,我們工作的方向等。[8]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之后,使中國國內出現了新的政治形勢,《淞滬停戰協定》簽訂不久,蔣介石又宣布“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基本國策,立即部署對南方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四次“圍剿”,并將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軍調往江西參加“剿共”。紅軍進漳后的抗日宣傳,以開展民族革命戰爭為號召,首次把反“圍剿”與抗日聯系起來,聲明:要不是國民黨軍閥集其全力來進攻蘇維埃區域紅軍,蘇區工農勞苦群眾與紅軍早已與抗日的英勇士兵和義勇軍站在一起直接對日作戰了,所以不推翻國民黨統治,就不能實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戰爭。[9]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在全國范圍內第一次明確的把對日作戰和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歷史任務結合起來,代表著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旗幟的正確方向,為第四次反“圍剿”奠定了政治輿論上的合情、合法、合理的基礎。
漳州靠近廈門,暢通海外,華僑眾多,通過進漳紅軍聲勢浩大的政治宣傳,擴大了我黨我軍抗日反蔣的政治影響,震動了全國。特別是對前來“圍剿”的十九路軍影響很大,在第四次反“圍剿”時,十九路軍有一個師開到漳州,但士兵不愿意打,上面壓他們打。后來在連城被我們紅軍和地方游擊隊配合消滅一個旅。[10]漳州各界人民也積極參加到抗日救國、民族革命的洪潮中,踴躍參加紅軍,其中參加主力紅軍900多人,參加地方紅軍600多人,擴大了紅軍的隊伍,也為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作了一定的人力準備。
此外,紅軍進漳客觀上也為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提供了領導力量的準備。第四次反“圍剿”時,毛澤東雖然已經離開了軍事領導崗位,不能親自部署、指揮戰斗,但第四次反“圍剿” 的勝利,卻是在周恩來、朱德等人指揮下取得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周恩來,而周恩來的作用因素則離不開毛澤東的影響。贛州戰役的失敗給周恩來一個深刻的教訓,促使他的思想認識有了進一步的轉變,并積極支持毛澤東攻打漳州。漳州戰役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和毛澤東默契配合,是中國革命史上兩位偉人相互支持配合取得輝煌勝利的第一個戰役,也使周恩來在軍事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和理解了毛澤東革命戰爭戰略思想和軍事戰術原則,并促使自己對黨內意見分歧的選擇逐漸偏向了毛澤東一邊。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致信中共蘇區中央局,針對中央局仍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作進一步陳說: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信中堅持由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懇請中央局再三考慮前方意見。[11]1932年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周恩來不同意中央對毛澤東的過分批評,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于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12]這兩次都體現了周恩來頂住“左”傾錯誤對毛澤東的支持。之后,臨時中央還是撤銷了毛澤東所擔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決定這一職務由周恩來兼任。但是寧都會議后,紅一方面軍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的指揮下,堅持主張,采取出敵不意,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等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是周恩來、朱德等運用和發展以往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從實際出發,沒有機械執行蘇區中央局進攻南豐的命令的結果,并且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伏擊殲敵的范例。[13]這次戰役雖然不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但恰恰是周恩來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戰略戰術的影響下取得的勝利,而非周恩來等人根據蘇區中央局“左”傾錯誤所指導取得的勝利。
總之,漳州戰役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符合毛澤東正確戰略布局的一次重要戰役,為中央蘇區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和準備工作,80年來仍然閃耀著她熠熠生輝的光芒!
注釋:
[1]福建省龍溪地區中共黨史研究分會《中央紅軍攻克漳州》資料選編(下),P5
[2]福建省龍溪地區中共黨史研究分會《中央紅軍攻克漳州》資料選編(下),P10
[3]福建省龍溪地區中共黨史研究分會《中央紅軍攻克漳州》資料選編(下),P17
[4]《紅軍進漳論文集》[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0,P391
[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P202
[6]《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P201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8,P374
[8]《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P202
[9]福建省龍溪地區中共黨史研究分會《中央紅軍攻克漳州》資料選編(上),P27
[10]福建省龍溪地區中共黨史研究分會《中央紅軍攻克漳州》資料選編(上),P67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8,P380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8,P390
[1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 [M]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1,P355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 [M]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版.
[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毛澤東年譜》(上卷)[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4]福建省龍溪地區中共黨史研究分會《中央紅軍攻克漳州》資料選編(上、下)1982年版.
[5]《紅軍進漳論文集》[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6]羅斯·特里爾(美),胡為雄,鄭玉臣譯:《毛澤東傳》[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