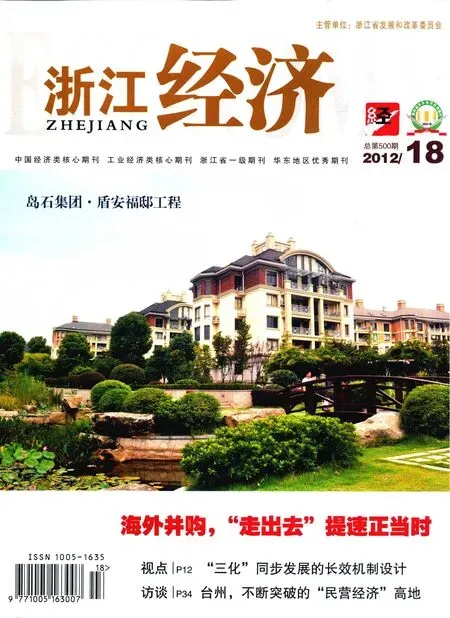把脈浙江城市化
□ 文/吳可人
把脈浙江城市化
□ 文/吳可人
破題的關鍵,是要充分認清產業結構偏低是造成浙江城鎮流動人口量大而質低的深層次原因所在
浙江城市化走在全國前列。最近中國社科院一項研究成果顯示,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占比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51.3%,名義上實現社會結構以城市為主的歷史性跨越。而早在10年前,浙江就已經實現這一重大轉變,2001年,浙江城鎮人口首次超過常住人口比重的半壁江山,達到50.9%。2010年,浙江城鎮化率更是提高至61.6%,高于全國平均11.7個百分點。從數據上看,浙江社會結構已經進入到以城市社會為主體的新的城市時代。
雖然城市化對于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意義毋庸置疑,但我們不能忽略掉一個重要數據,在城鎮化水平大大領先于全國多數地區狀況下,浙江城鎮的流動人口規模亦居全國各地前列,且這一群體仍在以較快速度擴張。2010年,浙江城鎮流動人口規模已達1616萬人,占城鎮全部常住人口的48.2%之多,大大高于全國34.4%的平均水平,僅次于北上廣。也就是說,若去除這部分流動人口,浙江城鎮化進程遠沒有數據顯示的那樣樂觀。以流動人口為主要支撐的城市化進程,對于浙江城市化發展極為不利。
一是流動人口難以成為有效的消費群體,不利于提振城市消費,進而拖累城市服務業發展。由于流動人口大多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收入較低且穩定性不高,加之多數流動人口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和很多公共服務之外,因此流動人口消費能力低、消費意愿低,對服務業需求幾乎微乎其微,難以形成支撐服務業較快發展的市場需求。浙江11個設區市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8.3%,僅略高于同期世界低收入國家地區(46.9%),大大低于其他各收入水平國家地區,就是一個佐證。在浙江,越是制造業龐大,外來農民工多的中小工業城鎮,第三產業比重越低。這種人口結構不改變,城市發展服務業就非常困難。

二是流動人口難以成為有專業技術能力的勞動者,阻礙城市人力資本積累,制約城市創新能力提升。受產業結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影響,流入浙江城鎮的流動人口知識水平、勞動技能、專業素養均較低。2010年,浙江城鎮流動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占比高達69.3%,在全國僅次于西藏居第二位;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5年,低于全國9.3年的平均水平;而浙江文盲率3.4%,為全國最高。當前,浙江萬人專業技術人員數居全國第16位,浙江的人才資源儲備與整體經濟實力不相稱,難以適應浙江轉型發展人才需求。
三是流動人口難以形成穩定的公共服務需求,加大城市公共服務供給難度,影響城市功能提升發展。鑒于流動人口普遍流動性較高,其公共服務需求規模變化較大,加之在現有中央和地方稅收分成格局下,目前城市政府仍不愿拿出太多錢用于提供外來流動人口服務,進而影響城市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而在公共服務供給出現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城市人均享有水平勢必大大下降,出現城市道路、綠地、垃圾污水處理等設施和服務難以滿足城市常住人口需求的狀況,制約城市功能提升和社會良性發展。
四是流動人口難以充分融入城市,導致城市社會結構兩級分
化,加劇社會矛盾。流動人口與城市戶籍人口之間,職業分化和貧富分化明顯,收入差距、社會地位差距均較大。這種狀況加大了流動人口在建立社會網絡、積累社會資本方面的難度,進而影響他們獲得較好的工作、融入城市主流的機會,使他們陷入“邊緣化——缺乏社會交往——更邊緣化”的惡性循環。
讓城市成為“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的城市,而不僅僅是城市人的城市”;讓居住在城市的來自農村地區、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流動人口,成為有資產者、有專業能力的勞動者,順利融入城市,將是未來一段時期,浙江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重要課題。
破題的一個關鍵是,要充分認清產業結構偏低是造成浙江城鎮流動人口量大而質低的深層次原因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千方百計加快城鎮產業轉型提升,加快高新產業、高端服務業發展,以更高層次人力資本需求替代低層次勞動力需求,尤為關鍵。同時,著眼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落腳于政府推進社會發展的主要工作,著力打造高品質人居環境,創造和拓展人的發展機會,全面推進人的城市化,也將是一項重要工作。
(供稿: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