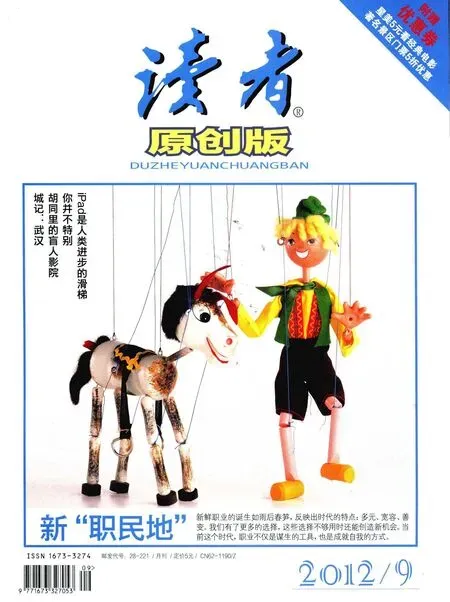被『突然』捉弄的孩子
文 _ 張麗鈞
王小妮在《上課記》中講了這樣一個例子:她帶著學影視編導的學生們欣賞凡·高的油畫《午休》—一對青年男女倚著麥垛睡著了。王老師布置的作業是在這個畫面的基礎上擴展出一個小片段,題目叫“午休·突然”,寫一個突發事件的降臨。同學們請求用表演的形式完成作業。幾天后,8個小組分別呈上了他們的作業。令王老師驚訝的是,這8個小組無一例外地都將“突然”設定成了“災難的突然降臨”。王老師問自己:難道現實生活不能給予這些孩子安全感嗎?于是,她問他們,為什么“突然”發生的都是壞事?80個學生聽了面面相覷,他們心里分明也有個聲音在質問王老師,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的心在寫有這個故事的那頁書上盤桓了許久,仿佛那張紙有著異乎尋常的分量,讓我翻書的手感到了一種沉重。
習慣性地將一種叫“不美好”的液體注入一個叫“臆測”的罐子,已成了我們太多人的集體無意識。電視連續劇《感動生命》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外科醫生馬博銘在為一個小患者實施心臟手術的過程中遭遇了一個“突然”—他的兒子出了車禍,急需實施開胸手術。馬醫生面臨著兩難選擇:是繼續手術,還是撇下小患者去搶救自己的骨肉?馬醫生選擇了前者。電視劇播出后,許多觀眾認為這個情節不真實。這時候,編劇兼導演陳燕民站出來了。他激動萬分地說,這個情節百分百來自生活,并且說他本人曾被故事的人物原型感動得涕淚橫流。但是,這樣的解釋反而為質疑這個情節的人火上澆油,他們說,快別見誰都說長得像雷鋒了!誰見過醫生待病人勝過親人的?馬博銘的“道德秀”讓人反感!……如果馬博銘們連“秀”道德的熱情都消失殆盡,如果柳葉刀通通變成了索命刀,這樣的“真實”才讓你覺得舒服?
我愿與你共同回憶那個聽起來極不真實的故事:一個喪心病狂的大學生,在連續開槍射殺了32名本校同學之后自殺身亡。這個“突然”后面發生的事震驚了全世界—學校舉辦的悼念儀式上放置了33塊半圓形的石灰巖悼念碑,敲響了33聲喪鐘,放飛了33個氣球;在兇手的悼念碑旁同樣擺放了玫瑰、百合、康乃馨等鮮花和紫色蠟燭,同樣有悼念便簽—兇手也被看成是一名“遇難者”,心靈嚴重扭曲的他走得那么痛苦,引來了太多人的同情與悲憫。一個叫勞拉的人在給他的便簽上寫道:“希望你知道我并沒有太生你的氣,也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這些人把那個叫“突然”的臭球接得那么完美……這個故事2007年發生在美國的弗吉尼亞大學,兇手是美籍韓裔學生趙承熙。
塵世中的每個人都是被一個又一個“突然”捉弄的孩子。“突然”降臨的瞬間,我們會晤的其實是自己真實的靈魂。在虛構的“突然”里,美好都搶不到一席之地,那不是美好的悲哀,是虛構者的悲哀。當“突然”裹挾著不美好跋扈地劫持了現實中的人,我們又怎能指望熱衷于虛構不美好的人趕過來營救呢?
美好可以是麥垛旁的天使飛臨,可以是無影燈下的慈悲眼神,可以是悠悠升天的第33個氣球給予生者的無邊撫慰。一個擁有正能量的人,不會甘當負面事件的信徒,相信美好是向拯救美好邁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