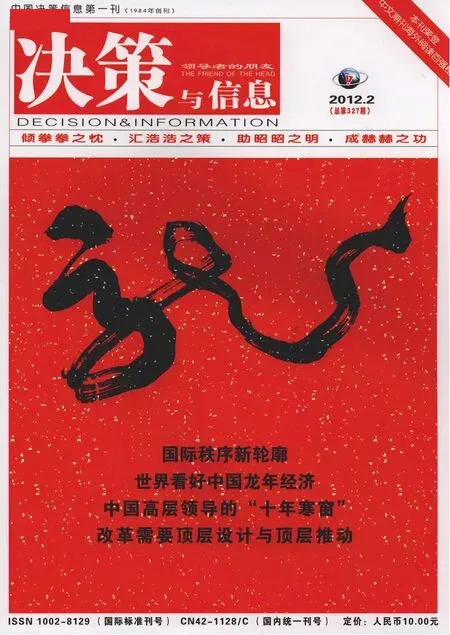清代官員的灰色收入
文/宗承灝

索賄送禮是中國官場的一種特有現象,不僅是某個時代的產物。康熙時期的吏科給事中林起龍就曾經說,一個州縣官員到任之后,“參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年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任,則備別禮”。一句話就是,新官上任所要燒的三把火,最大的一把火就是權力系統內的人情之火,靠人情之火來熔化權力的剛性。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剛剛從前線擊退廓爾喀入侵、平定西藏戰亂而凱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煩心事。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往戶部遞交了軍費賬冊,以便能夠早日報銷軍費開支,不料卻遭遇戶部書吏索要“部費”,也就是要賞錢。這些小小的戶部書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奧秘就在于官員的隱性利益。
官員的隱性利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隱性特權。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規范的缺失,當時的大小官員往往會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權,來謀求諸多顯著高于社會一般成員的非正當性收益以及依靠權力延伸出來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門供職的書吏,雖然不能與那些地方官員獲取的收益相提并論,可也有獲取隱性利益的巨大空間。既然地方官員的“炭敬”(冬天取暖費)、“冰敬”(夏天消暑費)之類的賄賂砸不到他們的頭上,那么他們就因地制宜,通過自己的部門特權向各地方官員直接索賄。
六部書吏在索賄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門道,從不含糊。在這六部當中,戶部索賄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是吏部和兵部。因為戶部是管各種費用報銷的部門,地方的各項開支要報銷,都必須經過戶部核準。
但凡有利益出沒的地方,就會產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諳規則的人,往往就沒有辦法辦成事。
進入清朝中期以后,送禮之風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在當時,一個省部級高官如總督、巡撫一年的“節禮”收入是不可估量的,其標準也是因時、因地而異。當時官員的灰色收入和地方經濟狀況是成正比的,富裕之地可以刮出的地皮油水肯定要比窮鄉僻壤更多。
晚清時期,一個省部級地方大員即使在甘肅、云貴這樣的窮地方為官,一年撈個兩萬兩銀子也難度不大(當時一兩銀子約折合人民幣200元,二萬兩銀子約合400萬元);如果在江西這樣不算窮也算不得富的地方為官,官員只要稍微動用“灰色技能”就能獲取六七萬兩銀子;如果運氣好的話,被分配到江浙地區這樣的富裕省份為官,那就等于是抱上了一棵搖錢樹,一年從樹上搖落個十萬雪花銀應該是很輕松的事。那個時代的十萬兩銀子,折合成現在的人民幣相當于兩千多萬元。
還有人推斷出,光緒年間官員的灰色收入是其薪俸的20倍。數字的精確程度暫且不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官員的灰色收入要遠遠大于其薪俸。古代官員的薪俸通常是朝廷付給的勞動報酬,屬于正俸。清代文官集團的正式收入在650萬兩銀子上下,但灰色收入卻達到了3000萬兩(這里也僅僅是放在明處的“節禮”一項)。兩相比較來看,差距又是何等驚人。
當古代官員拿著并不豐厚的俸祿在哭窮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了那薪俸背后的灰色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