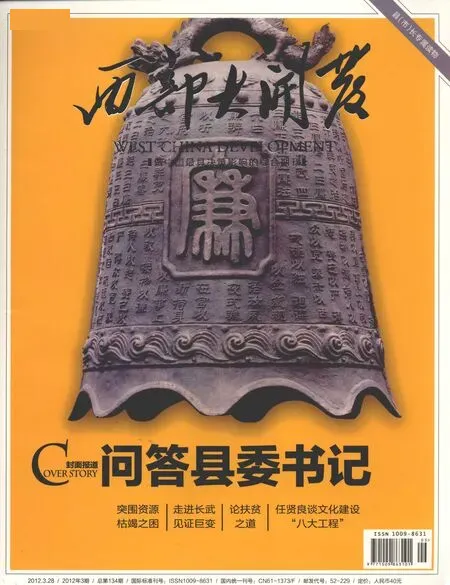危機乍現
◎ 文/本刊記者 周勵
危機乍現
◎ 文/本刊記者 周勵
數據顯示,我國目前有資源型城市118個,占全國城市總數的18%。近年來,隨著我國2/3的礦進入中老年期,1/4的資源型城市面臨資源枯竭的危機。資源型城市在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矛盾開始集中顯現,有的甚至十分尖銳——
資源枯竭表現在哪里
記者據資料所查,我們國家自然資源的匱乏主要表現在:能源方面。比如石油開采,僅供國內使用的46%,多數靠進口,更何況世界的石油儲量只能開采50年。煤炭資源也顯得十分緊張,價格近幾年曾一度飆升得令人難以置信,儲存量亦不足百年開采。
土地方面。由于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化進程,以及隨意的撂荒和破壞耕地,使得土地資源日漸稀缺。
森林方面。歷史上的幾次大砍伐,大煉鋼鐵,“文化大革命”,經濟過熱時的亂砍亂伐等等,已使得原始的樹木減少了2/3,大量的木質材料依賴進口。
物種方面。世界的物種每年正以上千種的數量在消失,我國物種的減少亦不容樂觀,每年已不下上百種,尤其是農林牧副漁的規模生產,那些經濟效益差的物種,日漸淘汰。以稻為例,百年前稻種具有上千種,如今只剩下區區幾百種了。
什么是資源型城市?就是以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采和初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城市,其一般發展規律是:建設-繁榮-衰退-轉型-振興或消亡 。
資源枯竭型城市,是指礦產資源開發進入后期、晚期的衰退或枯竭階段,其累計采出儲量已達到可采儲量70%以上的城市。
當資源型城市隨著礦業興起時,它們被冠以“煤都”、“汞都”、“石油之城”、“鐵都”、“銅都”、“瓷都”、“鎳都”、“錫都”等美譽。在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開采后,它們瀕臨困境,呈現落后態勢:一是隨著資源枯竭,產業效益下降;二是產業結構單一,資源產業萎縮,替代產業尚未形成,生態環境破壞嚴重;三是經濟總量不足,地方財力薄弱;四是大量職工收入低于全國城市居民人均水平,社會矛盾激化等。
資源型城市的生死劫
對于我們國家的資源型城市,因為沒有權威統一的評定標準,目前尚無最確切的數量。有專家學者統計,中國大約有400多座資源型城市。
在此基礎上,2002年,國家發改委《資源城市經濟結構轉型》課題組確定,全國共118座資源型城市。其中煤炭城市63座、有色金屬城市12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石油城市9座、森工城市21座,其他城市5座,占全國城市總數的18%,涉及人口1.54億。
無需諱言,無論是對一座城市,還是對于一個國家和地區而言,資源都掌控著它們的經濟命脈。
實際上,在中國龐大的資源版圖上,這118座城市都曾經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僅以遼寧阜新為例。這個有“煤都”之稱的城市,歷史上曾創造過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的輝煌:新中國成立以來,阜新累計生產原煤6.5億噸,“用60噸的火車車皮運輸,可以繞地球赤道4圈半”。甚至在1960年版的5元人民幣背面,是這樣一幅露天煤礦作業圖:高高揚起的電鎬,正奮力挖煤。這個沸騰的工作場面,背景就取自阜新海州煤礦。

甘肅玉門,老君廟油井仍在產油,只不過難現往日輝煌。
我國究竟有多少資源型城市,面臨著資源枯竭帶給它們的生死劫呢?2007年12月,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業界稱之為“38號文件”。
按照該文件指導宗旨,2008年3月、2009年3月、2011年12月,國家三批共確定了69座資源枯竭型城市。這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有著相似的成長軌跡:“礦業興則城市興,礦業竭則城市衰”。
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趙守國,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資源型城市在發展中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嚴重制約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資源枯竭型城市,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
“我國資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加重了高消耗。”趙守國說,“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8,德國的1/6,發達國家將生產轉移到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資源消耗自然低不下來。”
目前,這些資源型城市大多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部分礦區存在地質災害隱患。據不完全統計,每年85%的工業廢棄物來自礦山開采,金屬尾礦、煤矸石堆積已超過50億噸和40億噸,并且以每年4-5億噸劇增。因采礦活動誘發的地面坍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質災害時有發生,每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00億元。由于長期過量采伐林木,東北地區伊春的紅松林被砍伐98%,小興安嶺等地生態功能急劇下降,蓄水固土抗風沙能力明顯減弱。大慶由于開采石油造成森林覆蓋率大幅下降,草原退化、鹽堿化和沙化面積已占總面積的84%。
并且大多數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大批本地人才外流,外地人才又不愿前來工作。伴隨一些大型礦山破產,數以萬計的職工面臨失業。據國家人口計生委調研組2005年7月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當年遼寧省撫順、本溪和阜新的失業率分別為31.12%、21.30%和24.68%。礦工收入已從過去的各行業之首,倒退為各行業之末,年人均收入僅為最高收入行業的1/9。
職工養老、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問題也比較突出。隨著主業關閉破產和關聯產業陷于蕭條,下崗職工和提前退休人員激增,社會保險參保人數明顯下降,欠費增多,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嚴重入不敷出。較大規模的職工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社會治安也趨于惡化。
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成阻礙
資源型城市陷入發展困境,究其原因,除了資源枯竭還有哪些阻礙因素呢?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陜西省統計局原總統計師楊永善認為,“我國資源型城市出現這么多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除了有資源開采的客觀規律作用外,還存在諸多體制、機制成因。”
楊永善向記者分析解釋,資源枯竭城市在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和體制機制下,因資源開采留下很多欠賬,自身又尚未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內生能力,當地的經濟發展頻頻受阻;而資源開采仍處于穩產和增產期的城市由于缺乏有效制度機制保障,近年來,在政績攀比的作用下,地方政府拼資源、拼環境,加上不少民營企業在資源廉價條件下,盲目追逐超額利潤,加速了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計劃經濟下的直接調配與轉軌時期的價格失衡等問題,使資源型城市一直處于不利地位,在發展過程中,可以說走的是一條畸形軌道。”
計劃經濟時代,全國一盤棋,資源被國家無償調撥,經濟轉軌以來資源產品價格被壓低,從資源型城市低價輸出,而制成品高價輸入,造成資源型城市“雙重失血”。不少資源型城市是先有礦,后建城,企業級別高,規模大,政企不分,企業辦社會等問題突出。
大多數資源型企業拖欠銀行貸款數額巨大、時間較長,相當一部分已形成呆壞賬,企業信用低。比如,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資源型企業屬于“低增長高風險”企業,銀行不愿貸款。這使得資源型企業發展或退出所需資金嚴重匱乏。
資源型城市的發展長期缺乏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有水快流,竭澤而漁”的做法,導致不少資源型城市的建設缺乏科學論證,長期“先生產后生活”、“重開發輕建設”的思想,使當地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存在大量欠賬。
楊永善還指出,現有的價格、財稅政策難以保障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資源品價格扭曲,礦業企業成本不完全,未能涵蓋礦業權有償取得成本、環境治理成本和衰退期轉產成本等。許多礦上的開采嚴重破壞環境,污染大氣和水源,但企業并未付費或未完全付治理費,這部分成本沒有規定在開采成本中逐年攤消,而是推給政府、留給社會,是企業內部成本外化,私人成本社會化。
而現有的資源稅費制度存在的問題,導致中央財政支出中用于解決因資源開采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份額不足,而地方財政又捉襟見肘,對遺留問題有心無力。現有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缺乏補償資源型城市歷史欠賬的穩定渠道保證,造成資源型城市長期缺乏合理補償。
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命運,最終將走向哪里?長安大學地球科學與國土資源學院教授湯中立介紹,無論國內國外,依據各地現實情況一般是三條“方向”:一是就地消亡。比如美國底特律曾經是世界汽車工業中心,如今被稱為“美國鬼城”,持續40多年人口減少,規模不及巔峰時期的1/3。類似的還有美國的布法羅、德國的萊比錫、英國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以及俄羅斯的伊凡諾夫等城市,都經歷著自行淘汰的境遇。我們國家盛產石棉的青海芒崖鎮,在資源枯竭之后整體搬遷到了敦煌,是一種棄城式發展。
二是整體遷移。有著“中國石油工業搖籃”美譽的甘肅省玉門市,由于石油儲量減少等原因,上世紀末作出遷城決定,2003年4月得到國務院的正式批復。同年,玉門油田生活基地搬遷得到中國石油的批復。
三是轉型。成功的例子如河南省焦作市發展自然山水旅游,以云臺山為代表的“焦作山水”已經成為中國旅游的知名品牌;其鋁、化工、汽車及零部件等六大產業持續提升,代替了將要枯竭的煤炭資源開發,實現了社會經濟的全面轉型。
鏈接

目前我國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