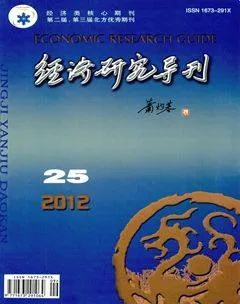地方行政立法審查的重點
范文舟
摘要:地方行政立法審查的重點應該是對行政立法的立法技術的審查,而對立法技術方面的審查重點又應該是其結構營造技術和法的語言表述技術。某些寧夏兩級地方行政立法的立法技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1)立法結構凌亂,層次不清,甚至望文生義;(2)立法規定過于原則、抽象,缺乏準確性;(3)立法中存在常識性語病以及立法語言口語化;(4)立法用語不規范,非法律術語、政策性色彩過濃。
關鍵詞:兩級地方立法;行政立法;立法監督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5-0238-02
一
如所周知,通常所說的立法監督是立法機關所為之立法監督,①然本文所探討的立法監督并非完全這種意義的立法監督,而是包括對地方(省級、省政府所在地的市、較大的市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涉及行政機關行政權力及其行使的地方性法規,以及省級人民政府、省政府所在地的市、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甚至包括對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之監督。所以本文所探討的地方行政立法監督,與通說有個共同點,即監督的主體仍然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包括地方人大對其常委會行政立法工作的監督,省級(在寧夏即自治區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省會市(在寧夏即銀川市)人大及其常委會行政立法工作的監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其同級別人民政府行政立法工作的監督,在寧夏即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對自治區政府行政立法工作的監督,銀川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銀川市人民政府行政立法工作的監督。
筆者認為,寧夏兩級地方行政立法監督的現狀中所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對立法技術的監督不夠嚴謹,所以監督的重點應該是對立法技術的監督。本文就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環境教育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為例,對行政立法技術的監督問題作一粗淺探討,期望能對包括自治區和銀川市在內的地方行政立法監督工作有所助益。
二
寧夏兩級地方行政立法的立法技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1)立法結構凌亂,層次不清,甚至望文生義;(2)立法規定過于原則、抽象,缺乏準確性;(3)立法中存在常識性語病,以及立法語言口語化;(4)立法用語不規范,非法律術語、政策性色彩過濃。
(一)立法結構凌亂,層次不清,甚至望文生義
《寧夏回族自治區環境教育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立法結構凌亂,層次不清。
整個《條例》包括第一章“總則”,第二章“組織機構與職責”,第三章“學校環境教育”,第四章“社會環境教育”,第五章“環境教育的保障”,第六章“獎勵與處罰”,第七章“附則”。按照立法的基本知識,“總則”部分應該規定本條例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其后各章應該是對“總則”所規定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的落實或體現。但《條例》常常把應該規定在第一章“總則”部分的內容規定在了后面的各章。如《條例》第33條規定,各級環境教育委員會應當定期對環境教育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并將相關情況報送同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環境教育委員會。第34條,自治區應當加強環境教育理論和重大實踐成果的研究,為開展環境教育提供科學指導和支持。這兩條都被寫在了第五章,但其內容都是原則性的規定,所以,都應該規定在第一章“總則”之中。
《條例》的一些規定還是望文生義的結果。第1條,“為了普及和加強環境教育,增強公民環境意識,提高生態文明水平,促進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結合自治區實際,制定本條例。”說本《條例》是根據環境保護法制定的,完全正確,但說是根據教育法制定的,就是望文生義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5條明確規定,“國家鼓勵環境保護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加強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提高環境保護科學技術水平,普及環境保護的科學知識。”這是一條原則性規定,就為各個地方立法機關提供了立法的依據,實際上也提出了地方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并未規定這樣的內容,它所規定的“教育”與《條例》所涉及的環境教育之“教育”不具有直接的相關性。說《寧夏回族自治區環境教育條例》是根據教育法制定的,乃望文生義也。
由于《條例》立法結構凌亂,層次不清,也就導致了其立法主旨不清,讓人搞不清其主要的規制對象是誰,是有關國家機關,還是普通公民。按照通常的理解,《條例》主要是規定環境教育的主體(機關或機構),即環境教育應該由誰來負責,他(們)應該如何開展工作,具有哪些權力,承擔什么責任等等都沒有規定清楚。
按照立法理論,地方行政立法的總則一般位于立法文件的首部,與分則、附則部分相對應,主要規定立法的立法目的、立法原則、適用范圍、執法主體等內容。總則是立法的主要精神和核心的載體。總則的文字表述應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內容應當簡明、準確,集中表述在法規結構的開端部分。
總則部分一般規定如下內容:立法目的、立法依據、立法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方針、基本制度、調整對象、效力范圍、法規適用、主管部門、獎勵主體、其他規定等,在具體的立法過程中,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以上內容進行選擇性規定。其排列順序通常為:立法目的(宗旨)和立法依據;調整范圍;基本原則、指導思想和方針;主管部門;基本制度;獎勵主體;定義條款;其他規定。
(二)立法規定過于原則、抽象,缺乏準確性
前文所列舉的《條例》的規定就是過于原則、抽象,缺乏準確性的規定,除此之外,這類規定還有很多。第9條(屬于第二章),“工會、共青團、婦聯以及其他社會團體,應當結合各自工作,開展多種形式的環境教育活動。”多種形式究竟是哪些形式?讓人無所適從。第21條(屬于第四章)第1款,“建立健全環保社會組織引導、管理和服務機制,為環保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創造條件。”誰“建立健全”?讓人摸不著頭腦。該條第3款(鼓勵環保社會組織開展國內外交流與合作,環保部門應當為環保社會組織開展交流與合作進行政策指導、提供信息、搭建平臺)第4款(鼓勵其他社會公益組織以及志愿者參與環境教育工作)也有同樣的“效果”。
有些規定極其抽象。如《條例》第34條,“自治區應當加強環境教育理論和重大實踐成果的研究,為開展環境教育提供科學指導和支持。”自治區哪個機關、哪個單位?還是所有機關、所有單位?都不清楚。
(三)立法中存在常識性語病和邏輯錯誤,以及立法語言口語化
《條例》第5條第1款:“環境教育分為環境普及教育和環境重點教育。”“普及”和“重點”并非相對詞。該條第2款:“環境普及教育的對象為全體公民;環境重點教育的對象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企事業單位負責人、教師以及學生。”“;”號把本款規定的內容分為前后兩部分,且這兩部分內容是并列關系,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企事業單位負責人、教師和學生都是公民,都屬于全體公民范圍內的,就是說他們和全體公民是包含關系,不是并列關系。這兩款是典型的常識性語病。
第6條:“環境教育實行經常教育與集中教育相結合、普及教育與重點教育相結合、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相結合的原則。”“經常教育”和“集中教育”也不是相對詞。再者,如前文所說,本條作為原則性規定,在《條例》以后各章中應該體現出來,但其后各章都沒有明確“經常教育”應該如何開展,“集中教育”應該如何開展等等,且都是典型的口語化表述。
(四)立法用語不規范,非法律術語、政策性色彩過濃
前文所列舉的《條例》的有關條文在存在上述毛病的同時,也體現出立法用語不規范,非法律術語、政策性色彩過濃的毛病。《條例》還有一些條款體現出這種毛病。《條例》第18條:“人民法院公開審理環境案件,應當公告相關信息,為公民旁聽環境案件提供便利。”這是一個典型的不規范的、政策性語言條款。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是否公開審判,是只服從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以及法院組織法等法律規定的,《條例》作為地方性法規是沒有權力為人民法院設置義務的。
《條例》第19條:“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村(居)民委員會,應當利用社區、集市、文化館等公共場所,向群眾開展經常性的環境教育活動。”這也是一條“政策性”規定,作為立法規定卻很不嚴謹。表面上看,《條例》是可以為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村(居)民委員會設置義務的。但是,村(居)民委員會在法律性質上和前兩者是不同的,前兩者是一級政府,而后者是人民群眾自治組織。立法在為他們設置義務時應該區別對待。當一級政府向人民群眾開展經常性的環境教育活動時,那是政府行為,在法律性質上可能是行政行為(當其為人民群眾設置義務時),也可能是行政指導。而人民群眾自治組織在開展經常性的環境教育活動時,就屬于人民群眾自我教育了,兩者在實際保障問題上將有極大的區別。
以上是筆者在對寧夏回族自治區以及銀川市兩級地方行政立法的相關行政立法文件進行審視時發現的立法語言方面的缺點,只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環境教育條例(草案)》比較集中地存在。這些也是地方行政立法監督的重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