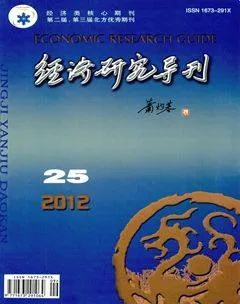西方文學潮流的精神內涵
徐翔
摘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關系與主體性的關系論視角出發,審視西方文學潮流中精神現象的表現及其問題,探討不同文學主潮的社會文化內在演變機理。
關鍵詞:主體性;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西方;文學潮流
中圖分類號:I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5-0253-02
正如馬克思的名言所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參照阿爾都塞的深入闡釋,特定的生產關系需要特定的意識形態來保證此生產關系的再生產,而正是意識形態把個體“傳喚”為主體。因此,人的主體性是特定的生產關系的具體的、歷史的產物,它不是永恒不變的,每個歷史階段有使得這個階段的社會關系得到現實地再生產的主體性。本文在此社會關系與主體性的關系論視角基礎上,對西方文學思潮中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五個時期的精神特征演變機理進行分析。
一、西方文學中的精神危機
古典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當然有悲劇,有痛苦,有物質的匱乏,有精神上的邪惡,但沒有我們現在所謂的“精神危機”。在古典作品中即使有太多的苦難,我們也看不到對于現實、對于他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的失望和批判。只是近現代以來,文學作品中的精神危機開始出現并越來越深重,從浪漫主義時期的“感傷”到現代主義時期的“荒原”和“生活在別處”。這種精神危機的實質根源,可以從前文所述的社會關系和主體性的關系中尋找答案。
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借用馬克思所說的,“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2]。在前一階段,也即前工業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直接的,不用通過他物而以人自身為媒介,人不是因為機器和制度而聯結,而是依賴于“人”;但到了后一階段,由于機器、工業的不斷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著深刻的轉變,很多關系都是以“機器”以及嚴格的、冰冷的制度為媒介,人是通過機器和制度而錯綜復雜地聯結在一起,也就是說,依賴于“物”。這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類型分別處于這一節所要說的兩個時期:前工業化的古典時期,工業化開始之后的近現代時期。它們對人的主體性的要求也是有著深刻差異的。前一階段,人的屬性是人自身的要求,主體被“人”自身要求和壓迫,但不會感到來自“物”的力量的壓制;而后一階段人的主體性在此是受到“物”的壓迫的。
古典時期的主體性并沒有感到被壓迫、被扭曲,沒有那種“異化”感,這個時期的人們就按照他們的主體性賦予他們的邏輯去生活。但是到了近現代時期,由于人們保持了古典時期“人化”的主體性的傳統,對這種被“物化”的主體性尚不能接受,因而當他們繼續按照傳統的方式、觀念去思考和作出價值判斷、行動時,就感到了一種沖突。通俗地說,當大地上的人們從古典時期走進近現代時期,就像一個農村的孩子闖進大都市,困惑、傷感、彷徨在所難免——除非他徹底地轉變成一個“城里人”,適應城市的人倫道德、生活方式。這個時候,他不僅不再是“大地上的異鄉者”,反而會覺得這里就是他的家園。
由此可見,西方近現代以來所出現的精神危機在于古典時期延續下來的主體性與近現代時期所要求的主體性之間的沖突。于是他們自先是在主體方面,幻想緬懷過去的人性,那“高貴的單純和寧靜的偉大”,這就是通常所稱的“浪漫主義”思潮;然后,他們又在客體方面,描繪這個現實世界并加以批判,這就是所謂的“現實主義”(更確切地說,是“批判現實主義”)思潮;后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新舊主體性的沖突更加深化,人們處于更加深重的精神痛苦和絕望之中,而現代主義文學則是這種痛苦的表現;到了后現代主義階段,人們開始嘗試忘記傳統的主體性在他們心靈深處的召喚——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放棄對于所處的物化世界的抗拒,開始肯定“機器文明”,開始認為“賽跑的汽車比沙摩特拉克的女神更美”[3],于是此階段開始和現代主義階段有了較明顯的區別。當人們沿著后現代主義的路繼續向前走,徹底放棄傳統以及對于現實世界和現實主體性的抗拒之后,適應了“速度”和“力”以及物化世界時,一種新的文學精神文化特征也會應運而生。
二、西方文學潮流的精神演變
在古典主義時期,社會關系和主體性是統一的,他們的生活就在“此處”,而沒有異化感和靈肉沖突。如席勒所說,“在自然的素樸狀態中,由于人以自己的一切能力作為一個和諧的統一體發生作用,他的全部天性因而表現在外在生活中,所以詩人的作用就必然是盡可能完美地模仿現實”[4]。經常有人把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相混淆,認為它們都是“摹仿”現實。其實這兩種“摹仿”在內涵上有著深刻差異:古典主義對現實的摹仿并不帶否定、批判的色彩。“現實主義描寫的不是人類應該有的理想生活,而是人類已經有的實際生活。但是,因為現實主義創作是在理想的照耀下反映現實生活的,所以也要表現作家的審美理想……”[5]。法國的新古典主義嚴格地說來,只是沿襲了古典主義形式的偽古典主義。兩者的根本差異在于,古典主義從模仿現實中得到和諧的主體性;而新古典主義卻不能通過模仿現實,只能通過摹仿古典主義作品才能表現這種主體性。
隨著古希臘、羅馬文化以及中世紀的結束,社會逐漸開始了一個深刻的變化,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人們漸漸步入了一個“以物的依賴型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社會形態中,這種程度加深后就是現代主義時期“物化”和“荒誕”的世界。人們開始緬懷前一階段“對人的依賴關系”的主體性。在文學上,在古典主義之外就出現了另一種思潮,文學從“模仿現實”到“表現理想”,從“素樸的詩”轉化為“感傷的詩”,而后者就是通常所稱的浪漫主義文學。在此思潮中,作家感到新時代賦予的主體性和從傳統沿襲下來的舊主體性之間的沖突,他們往往不由自主地用舊主體性去找尋那個失落的主體性。在這個找尋的途中,浪漫主義文學向三個方向尋找內心的和諧和尋找“自我”:從客體角度而言,是自然和社會;從主體角度而言,是心靈。轉向自然的最具典型性的是英國的湖畔派;轉向社會的有雨果、拜倫等,他們批判現實的社會,幻想著烏托邦式的理想國;轉向心靈的代表有德國“消極浪漫主義”。
到了第三個時期也即現實主義時期,心靈上的沖突仍然存在,而這種沖突說穿了只是現實中的主體性和理想的主體性的沖突。但此時的人們不再像前一階段那樣去幻想和緬懷,他們更多地把焦點放在對于現實世界的批判。這也就是為什么現實主義又是批判現實主義。正是在這種批判中,人們才可以找到理想。因此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既是相反的兩極——前者是在肯定中包含否定,后者是在否定中包含肯定——又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都拒不認同現實的主體性。
到現代主義時期,工業和資本主義比以往有了高度的發展,“物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們進入了“荒原”。人們依然試圖找尋溫暖的“人”及其“溫情脈脈”的關系,但所到之處只是冷冰冰的物和制度而已,于是在后現代主義看來,這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是沒有他們所預設的“人”和“人性”的“廢墟”而已,于是現代主義作家“用一只手擋開籠罩其上的命運的絕望,另一只手草草記下他在廢墟中所看到的一切”(卡夫卡)。就此而言,現代主義是很真切的現實主義。
現代主義文學既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以來失望的深化,也是對于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所擁有的烏托邦的放棄。從客體角度來說,他們否定現存世界,也即一個新到來的高度的工業化和科層制社會,認為這個世界是個荒誕的世界,因而他們不斷尋找家園。就主體角度而言,他們不認同現實的歷史階段和社會關系賦予他們的屬性,認為人性被扭曲;同時,也放棄了對于理想人性的向往,連烏托邦都無處可尋,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絕望和空虛之中。自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以來的文學中的精神上的問題,并不是世界本身的問題,而是在于作家們認為現實世界所賦予的主體性不是他們所應該有的主體性。
在后現代主義時期,作家放棄抵抗,開始返回“庸常”。但這并非取消意義,而是拒絕以前所強加的意義,使生活本身就是其意義。因此,“后現代給人一種愈趨淺薄微弱的歷史感”[6],其區別于前述各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對于主體性預設的消解。繼后現代主義之后,也會有其他的文學思潮。當現實本身成為寄托,那這很可能就是尚未來臨的第六個時期的特征,也即后現代主義之后的那個時期,是對于歷史中特定階段及其主體性的認同。此階段,人在“此處”找到“生活”,得到精神危機的拯救。就社會關系與主體性的關系而言,這個后—后現代主義與古典主義有著類似,但具有內涵的不同,這種差異主要在于它們的社會關系和主體性的內容都已發生了巨大變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3]曾慶元.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述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37.
[4]席勒.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G]//伍蠡甫,胡經之.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474.
[5]段楚英.漫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理論[J].孝感學院學報,1997,(3):51.
[6]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G]//張旭東.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橋,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1997:433.
[責任編輯 王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