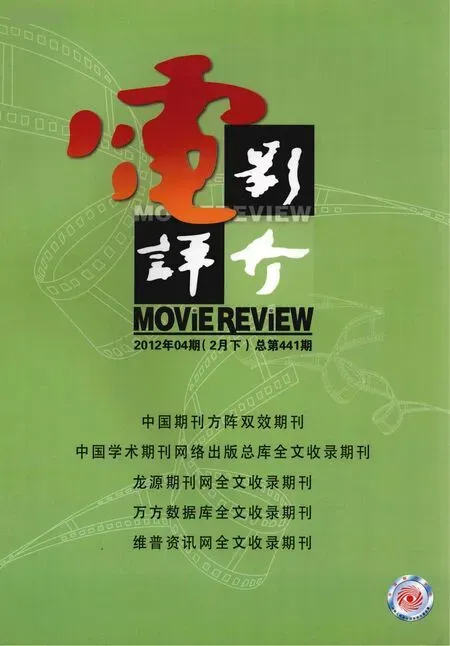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冷漠與溫情: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迷失之物》中的藝術真實
在歷屆奧斯卡獲獎動畫短片中,部分影片以刻畫人性之美丑見長,如《平衡》(1989)、《老人與海》(1999)、《回憶積木小屋》(2008),獲第83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獎的《迷失之物》(The Lost Thing,2011)也不例外。這部來源于作者少年時代生活體驗的動畫短片,其中所呈現出來的“真”實——與“善”和“美”共生的現實性主題,其實就是以虛擬性的“藝術真實”向觀眾講述一個存在于每個人心靈深處的情感歷程故事。

圖片來源:第83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迷失之物》視頻截圖
一、以動畫藝術來表現冷漠的現實主題
《迷失之物》根據陳志勇(Shaun Tan)的同名繪本改編而來,講述的是“在很多個夏天以前”發生的故事:還是個少年的主人公喜歡搜集瓶蓋,有一天在沙灘上發現了一個沒人愿意理睬的“東西”,一個表情悲傷而迷茫的奇怪生命體。雖然這個“無名物體”生性友善、好奇、膽小且又頑性十足,但是沒有人“留意”它,更少有人愿意幫助它,就連主人公的父母也不能接納它。在另外一個奇怪生物的指引下,主人公終于把“迷失之物”送到了屬于它們自己的烏有之鄉。
很明顯,這部動畫短片反映出人在成長過程中,由于世事的繁復與忙碌,導致原本友善、童真的自然本性日益消褪,對周圍的事物已不再有新奇感,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亦趨于冷漠,甚至是隔閡。應該說,采用動畫藝術來表現這樣令人壓抑的現實主題,的確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因為動畫向來以幽默與歡樂為自身的藝術特征,因此欲在動畫影片中添加真實的傷痛環節,實屬不易,更別說將影片的情感基調定位在憂郁、低沉和冷漠等這些“不太愉悅”的主題之上了。在這里,陳志勇等創作者們是想嘗試一種帶有悖論基調的風格:“虛擬”中的真情實感。他們要以批判的態度來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冷漠,同時對人性的復雜性給予反省,并期待短片能夠喚醒現代社會迷失已久的良知與溫情。
細軟的沙灘上,有人躺著享受日光浴,有人在翻看報紙,有些人則扎堆聊天,當然也有人在四處拾掇垃圾,而正在興致勃勃收集瓶蓋的“我”發現了坐在沙灘上“無所事事”的“那個東西”——一個磚紅色的大“玩具”。由短片中呈現的沙灘景象,我們便走進了一個現代工業社會的人性場域。與正“忙著別的事”的人們形成對比,處于一個隔膜的現實世界之中的迷失之物沒有“迷失”自我,“我”的一句“HELLO”,便立即喚醒了它昏睡已久的心靈,讓它重新恢復了往昔的活力,從龐大而怪異的身軀中迸發出的那個調皮勁兒,讓人在頃刻間就喜歡上了這個“被人遺忘”的“東西”。沒有比這個更讓人憐愛的東西了。“這個東西”表面看起來是想遠離人群,但實際上正觀望著人群,雖然處在喧囂而冷漠的社會里,但卻在等待著溫暖的陽光。“我”給了迷失之物無私而真誠的幫助。這種幫助,按照大機器工業社會的法則,其實是不應給予“流浪者”的,因為他們的迷失或許是競爭失敗,或許是因為懶惰、不安分守己、老弱病殘等因素造成的,但主人公還是伸出了援手。現在看來,迷失的不是這個“東西”自身,迷失的是人的友愛之情和憐憫之心,人與機械的結合成為現代工業社會的象征,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同情反倒成為一種可遇不可求的東西。這種互為本末的現實說明,人的孤獨與冷漠,即是現代人類文明釀就的苦果,也是人越來越憂郁的主因。
但是,在與這個東西玩耍的過程中,“我不知為何覺得有些不對勁”。乍看起來,“不對勁”的原因似乎是“不大可能會有人帶著這東西回家”,不過,從短片給出的情形看,真正的原因應該來自“我”周圍的環境。當大喇叭響起時,穿著印有編號制服的人們像聽到了“收工”的命令,收起遮陽傘,關掉機器,拔起插在沙子里的人造海鷗,然后紛紛離開了沙灘,原本熱鬧的景象只不過是一場有計劃的“偽裝”。顯然,這里的沙灘和人已經成為一種工業社會的象征,個體的人已不再需要很多屬于自己的色彩,他們只是資本社會大機器上的一個小零件。在面對一個關乎其他人的前途命運的時刻,他們無需做出努力或選擇——制度和規則已經安排妥了每一個生命體的歸宿。盡管這個社會還有善良與同情的成分,“我”和這個“迷失了”的東西之所以玩得“非常開心”,就是因為有“真心”的介入,很多時候,個人的能力和美好的愿望無法平衡這個世界,金錢才是命運的領導者和主宰者。在這個機器轟鳴的環境中,“迷失之物”擁有人的童心,但它同時擁有孤獨和悲傷,“我”也是一樣。并且“我”還生活在一個充滿成見和老于世故的家庭里,母親嫌棄迷失之物的臟,父親則擔心它會帶來“各種奇怪的疾病”,“他們倆只想讓我把它帶回當初發現它的地方”去。正在成長中的“我”不可能不受家庭環境的影響,潛意識里已經滋生出一點社會習氣與偏見,雖然這還不足以讓“我”喪失“真心”,但也成為“不對勁”的原因之一。
讓人倍感冷漠的另外一個原因則來自于聯邦什物部門。當“我”正在為如何處理這個東西而“進退兩難”的時候,電視上播放的聯邦什物部門服務廣告讓“我”決定把它送到那里去。按照大多數人的理解,這個社會公職部門應該是一個公益性的收容與養護場所。如果順利的話,迷失之物將得到庇護而不再“迷失”,它因此也可以獲得世界的合理性存在,與人們的正常溝通才成為可能。可是,一個讓人幾乎窒息的“沒有窗戶的灰色大樓”擺在我們面前,黑魆魆的大樓里面還充斥著“消毒劑的味道”,生性膽小的這個東西雖然亦步亦趨的跟著“我”,但仍然被一路泯滅的小燈所制造的黑暗嚇得夠嗆。在長長的過道盡頭,隨著最后一個小燈的熄滅,一盞刺眼的聚光燈在我們的頭頂上亮起。站在高高的柜臺下,“我”和這個仍然迷失的東西顯得是如此的渺小,以至于“我”仰起頭說話時,只能看到接待員的頭和手!高高在上的接待員面無表情的拖長語調說了句“填好表格”之后轉身就走了,等“我”雙手接過厚厚一摞表格時,頭頂上的聚光燈也被關閉了,只留下在黑暗中尋找桌子準備填表格的“我們”。陣陣冷風吹走幾張可有可無的表格,“迷失之物”的情緒也跌落到了冰點。社會服務廣告的欺騙性讓人心痛,這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處的真實情境!如果說“痛并快樂著”表明人還有希望的話,這里的“痛”已經讓人沒有了目標感,這是一種徹底透心涼的痛。正如法國劇場人阿爾托(Artaud)所說,神話故事“不是個人的,而是超越的,目的不是娛樂,而是表現一個民族心理、文化中最實在、最急切的真實。”[1]《迷失之物》也是如此,其中的無助和冷漠構成了今天人類社會真實的存在樣式,并存在于“一切向錢看”的意識之中,時時絞割著尚存良知的人,也正因為如此,社會才有了分裂感和不完整性。影片中的社會公職部門反而成了“遺忘與拋棄之地”,這正是《迷失之物》的現實性批判之所在。
二、冷漠的機器世界掩蓋不了真誠之心
《迷失之物》也為觀眾塑造了一個奇怪的機械世界:灰色的大街小巷和房子里到處都是銹跡斑斑的金屬管道、儀表、電線,以及各式各樣的煙囪、路標、紅綠燈、告示牌;行駛在鐵軌上的電車車頂上還裝有蒸汽機式的排氣管;甚至連大街上的人也是機械式的冰冷面孔與姿態,能拒人千里之外。“迷失之物”自然也是一個奇怪的合成物,它巨大的壺狀金屬外殼里除了柔軟而靈活的觸手與觸腳外,還包裹有金屬齒輪、風扇、儀表等一套蒸汽機裝置。不過,迷失之物純正的磚紅色外表讓它與影片中灰蒙蒙的城市“格格不入”——故事的伏筆正是通過這一抹亮色被巧妙地穿插進來——冷漠的機器世界掩蓋不了真誠之心。
在向一些人詢問無果后,“我帶著這迷失的東西去了皮特家”。他向“我們”伸出了熱情之手。皮特開門見到“我”時的微笑讓人頗感慰藉,他本人也是影片中最“真實”的人物,有自己的信念和想法,愛探究未知的事物,理性中帶有一點迂腐。皮特搬出參考書和各種實驗儀器,想“通過細心觀察,精準的測量,以及良好控制的實驗”來“辨認”這個東西是什么。很遺憾,皮特終究沒有搞清楚“這東西到底是什么”,他的實證方法失敗了。問題雖然沒有得到解決,但皮特一如既往的和“我”坐在他家的屋頂上喝咖啡聊天,而迷失之物則站在屋頂上興奮地觀望著這個城市。身在“高處”,“我”和皮特的友誼因此不會“迷失”。人要掌握這世界,也應該有相互間的真誠幫助與理解作為一種維度,這樣的人類世界才能真正成為我們真切的家園,才能以本來的面目無拘無束、毫無遮掩地交流,并快樂的生活。
回到家里,因為父母不能接受“這個東西”,“我”不得不“把它藏在后面的小屋里”。“不能就把它丟到大街上晃悠”是“我”對迷失之物最真誠的態度,這里面沒有摻雜任何人世間的虛偽,一方面,“我”只是出于一個青少年朦朧的責任感而堅持著這樣的態度,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東西”確實有著令人難忘的可愛勁兒,頑皮與懂事遠遠勝過了它怪異的外表,這種可愛勁兒來自于創作者細膩的刻畫。比如“我”和父母還有“這個東西”一起看電視,屋外火車經過時的震動讓墻上的鏡框歪斜了,這個東西輕輕地將它扶正;它又對臺燈很感興趣,觀察了一會兒后伸“手”去碰燈罩,結果讓燈罩歪斜著掉了下來,自己也嚇了一跳。在這里,創作者將細節安排得流暢而有起伏,自然之中的過渡是那樣的巧妙而不突兀,不落窠臼又有個性,而且在性格描寫中又有一種活潑與幽默,但幽默一定不是那種有意的逗笑,而是“這個東西”的本性。這種本性不是任何人都能具備的,它來自一種心無隔閡的真誠。與之相應,“我”的堅持就顯得順其自然,因為迷失之物是那么的單純與天真無邪,而“我”不懂得去遠離骯臟的東西,不懂嫌棄,不會勢利,在這個東西的眼里,“我”是一個可以信任和依賴的朋友,這個朋友不會拋棄它,他會義無反顧地幫助自己尋找那一片樂土。因此,還是少年的“我”和迷失之物的故事,就讓影片集“真、善、美”于一身,在不知不覺中讓人體會到了影片純真的魅力。
還是在聯邦什物部門,雖然“我們”受到了冷遇,但卻意外得到了一個奇怪生物的幫助。這是個帶著平頂帽、長著一條蛇形尾巴和兩條觸手的生物,是聯邦什物部門的清潔工。它給“我”一張印有“路標”的小卡片,在離開的時候,這個奇怪的清潔工重復著前面說過的話:“你不應該把它留在這。”語氣中帶著些許的責備,很顯然,清潔工在直白地告誡“我”,這里不是廣告所說的能夠解決“困擾”和“麻煩”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在乎那東西”,就應該按照這張路標去尋找真正屬于“它”的地方。看來清潔工常年在此工作,對那些被送到這里的迷失之物深感同情,因此在影片中扮演著向導的角色,并一次次揭露了人的冷漠與自私行徑。在輕聲細語中,清潔工展示出它的真誠與不惑,這使得它在短片中顯得分外醒目,成為平衡這個世界的重要角色。而且這個幾乎看不見頭的奇怪生物還充滿了絕妙的反諷意味:有頭有腦的人類對迷失之物一臉冷漠,更不愿知道它從哪里來;看似“無頭”的怪物卻心明眼亮,真誠的給“我們”指明了尋找的方向。
最終,在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后,“我”將這個迷失之物送回了屬于它的烏托邦,在這一時刻,“我們”相視而笑,心靈在瞬間都獲得了解放。短片最后體現出地這種真誠之心成為故事的靈魂,它建構起整個影片的情感,這就是故事“迷失”后“回歸”的主題。影片以超乎尋常的想象力為我們呈現出一個夢幻般的樂土:明媚的陽光,玩耍嬉戲并互相打招呼的大大小小的“玩具”,它們自由而歡暢,它們拋棄了人類的虛偽,純真與幫助成為一種默契。這片樂土也是一種象征,一個與人性并存的烏托邦世界,這個世界比人類世界可愛多了。生活在其中的“東西”是那樣地接近人性的真誠,善良與同情的心靈被開啟,然后自由地飛翔,任由飛翔的天空沒有邊界,即使迷失了,也要不停歇地尋找,堅持與真誠成為這個世界的情感主線。人們在這樣的情感中獲得了真實感,并由此可能成為那些“迷失”的東西獲得拯救的一種最好的方式。
三、回憶中的虛擬性真實
動畫藝術的真實還需要通過可知可見的視像表現出來。相對而言,這些視像的虛擬性真實,比超現實主義繪畫中的夢囈、電影文藝片中的假定性,顯得更真實可信,因為動畫藝術能夠把有機或無機的對象變成知覺意識中的人類世界,因此動畫中的虛擬,既是表現有個性特點的具體而個別的角色,在性格描寫和個性揭示中,又必須和必然地要反映出現實生活的真情實感。《迷失之物》以第一稱“我”的回憶為基礎,這就給予了影片強烈的真實感,并且其中的“真實”又遵循著動畫本身的藝術邏輯,以“虛擬性”的表現方式為人們呈現出人世間真實的冷與暖。
《迷失之物》中的虛擬性真實,首先是建立在“回憶”基礎上的,這就擺脫了時間與空間概念的桎梏,擴展了動畫藝術中可見情境的范圍,為人們展示了一個充滿幻想的無距離的世界。這樣的“虛擬”世界無形中延展了人們的精神空間,使我們能夠對真實的生活做更深層次的理解,虛擬性因而可以成為繼時間之后藝術中的“第五維坐標軸”,它也因此成就了動畫藝術中超乎想象的靈活性。《迷失之物》中就頻繁地運用了第五維坐標軸:無處不在的管道加深了觀眾對影片背景的印象;紅綠燈只是城市的標記物,并沒有實際功能;龐大的迷失之物能夠進出只有小門的房子,而且還能與“我們”一起“爬”上皮特家的尖屋頂;看不見頭的奇怪生物已經讓人詫異,它居然還能指引“我們”去尋找那片樂土。由于所表現的“迷失之物”具有知覺上夢幻般的想象性,由于影片具有觀眾所需要的生活原型,以及由于具有直接表現自然形態隨意變化的技術可能性,因此便有了處理并實現這種形態變化的第五維坐標軸,即虛擬性的存在。這就為最大限度地實現人們心中的夢想、接近現實生活中實在的矛盾與沖突提供了可能。這是虛擬性帶來的好處。因此可以說,具有第五維坐標軸性質的虛擬性是動畫藝術最好的同盟者。
其次,相框式的背景為“我”的回憶提供了“真實”的依據,也為虛擬性的表現帶來蒙太奇式的便利。短片極力還原了繪本的視覺效果,將其中印有電力學和機械學圖案的背景轉換為短片中的相框,新穎而別致。這些手工制作的相框不時出現,既奠定了短片的敘事風格與情感基調,也串聯起“我”記憶中的往事,同時還讓人們能夠從“第一人稱”的感官知覺到發生的一切,從而獲得直接而理想的真實性。相框所訴求的這種內在的獨特的視像感,是短片中所有要素和內在的超邏輯的敘事結構的綜合顯現。當“相框”這一虛擬的視像進入影片的蒙太奇結構之中,并成為具有特殊構成性的敘事要素時,它本身就已經成為既是表現的客體,又是表現的主體,還成為一種表現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這種虛擬的視像元素使觀眾與短片所營造的“虛擬實境”巧妙地聯動起來,讓觀眾產生了創造性的想象力。可以想象,如果是以生活本身為故事藍本出現在觀眾的知覺中的,那么,不管是創作者還是觀眾,都希望這種為了真實而虛擬的表現手段多多益善。
最后,有意做舊的材質與貼圖效果讓短片浸染著濃厚的歷史感,“回憶”的色彩很濃厚。墻體斑駁,管道等金屬物銹跡斑斑,書籍和電視也是陳舊的,就連生活在樂土中的形形色色的“玩具”都是如此。從時間維度看,這樣的處理是還原歷史真面貌的需要,是同環境、精神和審美心理緊密聯系的,烙印出時代痕跡;最關鍵的是,“由歷史性所帶來的確定性是實在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確定性,就沒有人類文化的根基,就沒有現實性的力量和普遍性的法則”[2]。當然,《迷失之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有歷史感的藝術載體,材質與貼圖還發揮出重要的情境揭示和隱喻功能。如短片中的標記貼圖,除了聯邦什物部門的清潔工給的那張“看起來無足輕重”的路標外,其實其它眾多的指示標記實際上沒有一個能夠指示方向,在“我們”走出聯邦什物部門的大樓后,影片甚至直接貼出“SIGN NOT IN USE”的字樣,這樣的貼圖設定顯然增強了“迷失”的主題性意味。如此來說,恰當的材質與貼圖設定應該具有積極意義上的創造性,如能通過這樣的設計激發人們對生活本質的思考,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就是藝術的真實。
結語
綜上所述,在敘事主題與藝術的現實性批判方面,《迷失之物》客觀而冷靜地講述了“迷失”的東西“回歸”家園的故事。從前文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影片中的“迷失之物”實際上象征著現代工業社會的人們在成長過程中那顆趨于迷失的心靈,孟子的“人性本善”論在這部短片中再一次得到了精彩的演繹。創作者不僅賦予世界不同的象征寓意,把人性中的善與惡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賦予短片以“心靈拯救”的人文內涵,使這一簡短的動畫影片充滿了“走出埃及”般的宗教意味。作為動畫藝術中的佼佼者,在視像表達與符號指向方面,《迷失之物》也滿足了當代人的審美期待,為人們營造出具有顯著時代性的“真實”的視覺藝術樣式,并為“迷失”與“回歸”的主題呈現塑造出充滿溫情的真實情境。這些成就讓我們知道,動畫也能從人性角度更好地表述藝術的真實,這就是短片的藝術魅力所在。
注釋
[1]劉俐.在焱焱柴堆中呼救——阿爾托和他的《殘酷劇場》[EB/OL].廣西話劇團.http://www.gxhjt.com/gxhjt/sys/html/2009/1/128.htm,2011年9月訪問.
[2]黃其洪.德里達論藝術[M].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07:55.
[1]《迷失之物》官方網站,www.thelostthing.com.2011-7訪問
[2](匈)貝拉?巴拉茲.電影美學[M](2版).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
[3](美)S.普林斯.真實的謊言:感覺上的真實性、數字成像與電影理論[J].世界電影.1997(1):20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