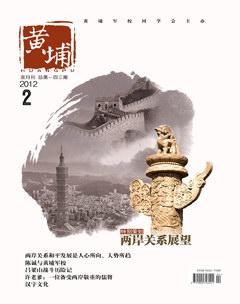特赦內戰罪犯,共產黨著眼統一 阻撓舊部回臺,國民黨拒絕接觸
邰言
“特赦戰犯”,曾經一度是出現頻率較高的名詞,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過巨大反響。到了1975年,所有戰犯,包括美蔣特務和特務船船員全部被特赦釋放,至此,中國再無戰犯。
“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在新中國成立后,解放戰爭時期被人民解放軍俘虜的國民黨戰犯,當時在全國各地監獄關押和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發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斗”的號召。當天,他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向臺灣展開相應的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協會后,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意見。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周恩來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并對各方面情況作了分析和研究,認為已經初步具備了釋放一批戰犯的條件。當時,國內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已提前完成,政治、經濟出現空前穩定。從戰犯本身的情況看,經過幾年的關押改造,他們之中的多數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釋放一批戰犯,將有助于孤立、動搖、瓦解境內外反動分子,同時有助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當時,根據周恩來闡明的對臺方針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國民黨去臺人員只要回到祖國,不管什么人,將一律既往不咎。在這種時候,釋放一批戰犯,將會有利于加強臺灣與大陸的聯系。
為了更好地處理戰犯問題,中共中央在向黨、政、軍、群等系統征求意見的同時也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征求意見,進行政治協商。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澤東提出: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如果不殺或許對臺灣還會產生影響。
對釋放戰犯的時間,毛澤東經過反復考慮后,在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沒這個必要。”
周恩來親切接見
特赦戰犯重獲新生
1959年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于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
9月17日,全國人大二屆九次會議討論并同意毛澤東主席的建議,作出了《關于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特赦令。
這個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功德林一號關押的戰犯,他們無比激動,感謝黨和政府的英明決定。10月2日,他們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以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在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有全體在押戰犯參加的特赦釋放大會,宣布了特赦釋放的戰犯名單,發放特赦通知書。在特赦大會上,被特赦的戰犯表示非常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使他們改邪歸正,從此獲得新生,并決心繼續改造思想,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戰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爭取早日獲得特赦。
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戰犯共3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在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
會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10個人和從撫順戰犯管理所釋放的末代皇帝溥儀專門組成一個小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門內旅館,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的同志負責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們意味著新生活的開始,下一步應該如何走,是每個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同樣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關注。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溥儀等11人乘專車駛進中南海西花廳。工作人員和藹地告訴他們,這里就是周恩來的家。
周恩來,這是他們非常熟悉的名字。這10名國民黨將軍中,除陳長捷、盧浚泉外,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今天,能夠見到30多年前的老師,心情格外驚喜,也感到十分的慚愧。周恩來在陳毅、習仲勛以及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滿面地走進了客廳。大家同時站了起來,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位當年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示意大家坐下,親切地同大家交談起來,逐一問起每個人的身體情況和家庭狀況。他對曾擴情說:“我在黃埔軍校時年齡還不到30歲,當時感到壓力特別大。”曾說:“我那時已30開外了,我這個學生比老師還大幾歲哩。”
周恩來又轉向杜聿明,詢問他的一些情況。杜聿明慚愧地低下頭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聽老師的話。”周恩來回答說:“這不怪你們,怪我這個當老師的沒有教好。”
張治中指著鄭庭笈向周恩來介紹說:“這是鄭介民的堂弟。”鄭介民在1946年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是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國民黨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來說:“我知道。”接著,他問到鄭庭笈的家庭情況。鄭庭笈告訴周恩來,他原來的妻子叫馮莉娟。1948年鄭被俘后,他的朋友為馮莉娟準備好了去臺灣的船票。但是,當她聽到鄭被俘后在哈爾濱發表的一篇講話后,就決定留下來,在海南島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戰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無法解決家庭生活問題,她決定和鄭庭笈離婚。周恩來聽后沉思片刻轉過頭去對張治中說:“那你們應該動員他們復婚嘛!”
在輕松風趣、和諧親切的氣氛中,周恩來把話轉入了正題。他勉勵大家通過加強思想改造,站穩民族立場和勞動人民的立場;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學習馬列主義,培養勞動觀點、集體觀點,加強群眾觀點;要認罪服法,重新做人。希望他們相信黨和國家,特赦后會信任他們,用上他們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屬的都可以。兩個月后再考慮安排工作。他還說,你們當中與臺灣有聯系的人,可做點工作,慢慢做,不著急,個人寫信靠得住些。
對于這次會見,楊伯濤后來感慨地回憶說:“這種對待俘虜的做法自古以來是沒有的。我為什么擁護共產黨,因為我是過來人,我看到過國民黨的興盛,也看到過他的衰敗。我為國民黨做過19年事,又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產黨才有這種胸懷。而周恩來使我形象化地認識了共產黨。”
特赦釋放后的戰犯,全部獲得了新生。這些人被釋放安置后,都由各級統戰部門負責管理。他們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陸的都與家人團聚了。有一些人還安排了重要職務,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漢杰、沈醉、廖耀湘、鄭庭笈、楊伯濤、周振強、李仙洲、羅歷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釋放的黃維、文強等先后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還有一批人被安排為地方政協委員、常委。他們參政議政,發揮了積極作用。絕大多數人擔任了各級政協文史專員、秘書專員、資料員和參事,也有極少數在農村和工廠,他們都過著幸福的晚年生活。許多人還以嚴肅的態度寫回憶錄,以求后代有所借鑒。不少人還參與對外交往活動,同臺灣的親朋故舊書信交流,為統一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
毛澤東說:都放了算了!
中國無在押戰犯
據中共中央調查部原部長羅青長回憶:“還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前,總理已經病得很重,連走路都已經很困難。但他仍然關心著臺灣問題的解決,關心著臺灣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為解決臺灣問題,再出一份心力。總理不顧個人安危,抱病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工作時,毛澤東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國民黨戰犯,包括清理在押的美蔣武裝特務。”
1974年12月28日中午,總理剛從長沙回京,就通知羅青長,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調查部與統戰部、公安部配合,組成一個小組,清理一下在押戰犯名單。羅接到總理的指示后就開始著手這項工作。羅青長知道,總理要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盡可能地為解決臺灣問題多做些事。
有關部門為討論戰犯名單及釋放后的安排、待遇等問題就搞了好幾個月,最后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形成了《關于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核心小組慎重清理、研究,將在押者中的25人單獨提出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給予落實政策。而最終列入在押戰犯名單的有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對該《報告》及準備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說明書做出批示。毛澤東說:“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一頓飯,要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當秘書讀到,報告中提出仍要繼續關押改造13人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注: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干什么!所以,一個不殺。”當讀到報告中提出,安置在農村的釋放人員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貼費15元至20元時,毛澤東明顯地表示出不滿意,說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澤東又說:“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毛澤東批示后,華國鋒立即主持召開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及公安部主管戰犯工作的負責人會議,關押戰犯最多的撫順戰犯管理所負責人員也被找來列席會議。幾乎所有與會人員都對毛澤東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長時間準備的分類處理在押戰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廢,所有在押戰犯不分有無“改惡從善表現”,一律特赦釋放,釋放后也不分他們原有的級別與表現,一律安排在城鎮。非常復雜的事情忽然變得如此簡單。
為了全面貫徹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來與華國鋒,以及后來出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要求有關部門對全部特赦釋放的所有在押戰犯做好組織、安置等各項準備工作。
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是一件很得民心的事。特赦釋放人員結束了在北京的參觀學習后,除王秉鉞等10人提出申請并被批準回臺灣外,其他人員按照自愿的原則,都被安置到祖國各地,與他們的親人團聚。
臺當局阻撓戰犯回臺
三人無奈重返大陸
王秉鉞等10人回臺灣的要求得到了批準。同時,還發給了臺灣往返通行證,如他們愿意,可隨時回來,并給予安置。
愿意回臺的10人是:原國民黨五十一軍中將軍長王秉鉞;原國民黨二十五軍中將軍長陳士章;原國民黨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王云沛;原國民黨軍統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周養浩;原國民黨國防部青年救國團贛東青年服務總隊少將總隊長蔡省三;原國民黨軍統局少將專員段克文;原國民黨青年軍二○四師上校團長張海商;原國民黨一五○師上校團長楊南屯;原國民黨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鐵石;原國民黨二八一師上校團長趙一雪。
王秉鉞等人對政府批準他們回臺灣,并給足路費、提供方便,表示感激。離京前,中央統戰部設宴為回臺灣的10人餞行。
王秉鉞等10人先赴香港,然后由香港辦理赴臺手續,才能到臺灣與親人團聚。但是,王秉鉞等10位回臺人員,在香港辦妥回臺登記后,過了一個月,仍沒有半點動靜,趙一雪等多次前去問詢,答復是“入臺證”不日即寄到。可回臺人員左等右等,仍遲遲未獲批準。時間進入5、6月,臺灣安全部門派出“特別小組”對回臺人員進行所謂“甄別”活動。臺北“救濟總會”致函九龍代理機構,轉知回臺人員寫信表明心跡。
由此種種,引得海內外同聲譴責,連香港的親臺報紙,也批評“臺灣的膿包決策者”。
為了達到阻撓10位人員返臺的目的,臺灣當局散布:回臺人員在港受到“左派包圍”。他們所指的是中國旅行社貫徹祖國大陸的政策,照顧回臺人員的食宿。而回臺人員一再表示:他們的行動并未受到任何限制。
6月4日,張鐵石化名王浩然,匿名“富都酒店”,自殺身亡。這一消息,讓港九為之震驚。6月9日,香港各報幾乎都在頭條報道了張鐵石的死訊。張鐵石死了,他是帶著與親人團聚的期待,帶著對臺灣國民黨當局的失望走向生命的盡頭的。
祖國大陸本著人道主義的立場,主動辦理張鐵石的后事,并主動和在臺灣的張鐵石的親屬聯系。6月6日上午,香港中國旅行社負責人及回臺人員段克文、蔡省三、趙一雪,在油麻地警署警官的陪同下,到九龍辦理認張鐵石尸體的手續。后來,張鐵石的兒子才在臺灣當局的許可下,帶著悲傷來香港辦理自己父親的后事,這種人間悲劇叫人情何以堪。
回臺10人,一個已化成灰,另9位客居陌生的香港,無所適從。時而傳來“入臺證就要到了”,時而臺灣當局駐港機構緘默無聲。9位老人都明白了,臺灣當局又以“拖”來對待他們。想到昨日還是10人,轉眼間離去一人,9位老人不禁潸然淚下。他們在問:何時才能赴臺與親人團聚呢?
原來由香港的臺北“救總”代理機構辦理回臺人員寫信表明心跡的手續,卻又被臺北“救總”公然否認了,這又給9人回臺設下了新的障礙。回臺人員萬般無奈,只得向臺灣當局提出,要求家屬來香港會面,臺灣當局也遲遲不予答復。
9位老人困在香港,有家不能回,有親人見不了,受盡煎熬,真是度日如年。萬般無奈之下,王秉鉞、陳士章、周養浩、段克文選擇赴美暫住。張海商、楊南屯、趙一雪三人揮淚告別香港,重返大陸。蔡省三、王云沛留在香港繼續等候回臺。
對特赦人員關心的海內外人士,都關心著張海商、趙一雪、楊南屯回到了祖國大陸后的情況。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機構則放出風,說什么三人“未完成統戰”任務,不可能受到中共的歡迎,免不了流落的結局。
可事實怎樣呢?
原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劉小萍回憶,9月2日,張海商、楊南屯、趙一雪抵達深圳時,受到中央統戰部和廣東省委統戰部代表的熱烈迎接。到達廣州時,又受到廣東省委統戰部和廣州市委統戰部領導的熱烈歡迎。廣東省委統戰部舉行了座談會,熱烈歡迎張海商三人歸來。三人在座談會上講了話,他們對踏入祖國大陸就受到熱烈的歡迎,表示十分激動。
9月3日下午,三人乘飛機到達北京,再次受到熱烈歡迎。中共中央統戰部原負責人李金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菊生,張海商等三人在大陸的親屬及愛國人士侯鏡如、鄭洞國、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文強等前往機場歡迎。
9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歡迎張海商等三人歸來。李金德說,你們去臺灣,我們歡送;現在回來,我們歡迎。你們的工作和生活將予以妥善安置。今后,如果能夠再回臺灣,我們再歡送。趙一雪先生代表三人發了言,這位頭發斑白的老人情緒激動,幾次流了淚。他說:“我們10人到港后,長期被阻,去不了臺灣。10人的情況不同,有的去了美國,有的還在香港等待回臺,張鐵石慘死。我們三人不愿在香港再等下去,申請暫時回來。我們一經申請,馬上就得到中旅社安排,自香港回到偉大的祖國首都北京。承蒙熱情接待,照顧備至,更使我們感到社會主義祖國的無比溫暖,我們表示衷心感激。”說到這里,趙一雪哭了,張海商、楊南屯也都流下了眼淚。
大陸歡送,臺灣阻撓,不同的待遇,讓人們看到了兩岸不同的政策,國共兩黨不同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