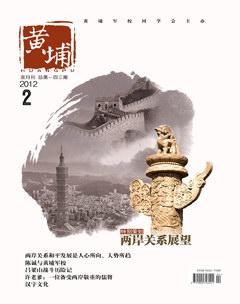許老爹:一位備受兩岸敬重的儒將
姚同發


初次聽到許老爹的稱呼,是在1998年赴臺訪問的一次聚會上。說實在的,對一位曾經叱咤風云的儒將,用一個近乎鄰家老伯的稱呼,感覺上總有點不甚習慣。后來又有幾次赴臺學術訪問的機會,與許老爹有了進一步接觸,才發現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稱呼,其實恰恰飽含了兩岸對儒將反“臺獨”、促統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敬重與欽佩,也是對儒將謙謙君子、諄諄長者高尚人品的仰慕與愛戴。
備受兩岸敬重的許老爹,就是島內德高望重的許歷農上將。值此許老爹93歲壽誕之際,謹以此小文,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長壽,更祈愿他能看到兩岸和平統一的那一天。
反“臺獨”,雖千萬人吾往矣
1919年3月4日出生于安徽貴池烏沙鎮的許老爹,高中畢業后即入行伍,1939年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六期畢業。在國難當頭、民族存亡之際,先后參加過皖南戰役、浙贛戰役等對日作戰,后來又加入了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之稱的青年軍,是一位被人尊為“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儒將。后隨軍去了臺灣,曾先后擔任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二任校長、總政戰部主任等要職。
其實,許老爹最為人稱道的并不是他在軍中的德高望重,而是他嫉惡如仇,數十年來不屈不撓反對“臺獨”的斗爭精神。1993 年,正當島內“臺獨”勢力甚囂塵上之時,他挺身而出,發起成立了以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為宗旨的新同盟會,并親自擔任會長。同年11月24日,恰逢中國國民黨建黨99周年紀念日,他含淚宣布脫離國民黨,加入新黨,在島內引起巨大震動。究其根源,是時任“總統”兼黨主席的李登輝,正一步步將國民黨引向“臺獨黨”的邪路,許老爹豈肯與之同流合污。
許老爹在“國民大會”上曾當面質詢李登輝:“你說了100多次你不是搞‘臺獨卻沒有人相信,我從來沒說過一次,人人都知道我不會搞‘臺獨。”這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責問,弄得李登輝啞口無言,狼狽不堪。
加入新黨后,許老爹毅然走在反“獨”促統最前線,聯合島內外各界有識之士,與“臺獨”逆流作不懈斗爭。在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50周年之際,他在臺北組織“我是中國人”大游行,參加者有8萬余人。他始終精神抖擻地走在游行隊伍前列,一走就是十幾里。
他還去過日本、俄羅斯、德國等國,參加世界華人反“獨”促統大會;到過香港、澳門,參加香港、澳門回歸慶典。而無論是在促統大會上,還是在慶典活動中,許老爹發出的振聾發聵之聲,都是疾呼要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
一向不出傳記及回憶錄的許老爹,在2009年終于有了第一本書問世——《雖千萬人吾往矣——許歷農文稿集》。文稿集收集整理了自1993年發表《大是大非——我的痛苦抉擇與嶄新希望》以來的演講稿及文章,真實記錄了許老爹公開與被李登輝掌控的國民黨決裂、創立新同盟會及民主團結聯盟、參與海內外和平統一運動的心路歷程。細讀文集,不難感受到作為受人敬重的“老爹”、眾人口中的“儒將”、新黨的“精神領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跟著道理走”的堅持,以及“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變,有所不變”的胸襟。
許老爹還將這些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手稿贈送民革中央,為我們留下一份反“臺獨”的歷史見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在接受手稿時指出,此次獲贈的手稿真實展現了許老堅持祖國統一、反對“臺獨”分裂的鮮明立場,是十幾年來兩岸關系發展變遷和島內愛國人士奮斗歷程的真實寫照。
促統一,相逢一笑泯恩仇
2005年國民黨、親民黨、新黨領導人先后訪問北京,相繼展開破冰之旅、搭橋之旅與和平之旅。其實,早在4年前許老爹就曾代表新黨到北京訪問,受到江澤民總書記、錢其琛副總理的接見,并就兩岸關系達成六點共識。與三位到訪的黨主席身份不同,許老爹是以一介平民邁出這可貴的一步,他追求兩岸和平、國家統一的精神無疑更加令人欽佩。
兩岸分隔60載,已屆鮐背之年的許老爹,和許多在臺老兵一樣,有著“但悲不見九州同”的感傷。他再三表示,“我唯一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國家統一”。他指出,早年蔣經國先生曾說過“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中國大陸自鄧小平先生領導改革開放,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后,經過30多年的努力,兩岸差異(包含思想理念)日益縮減,理應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懷,彼此接納。
對于許老爹追求國家統一的情懷,在島內是不被認同的。2011年3月25日,臺灣《自由時報》發表社論指名批評許老爹“以前‘反共,現在‘促統的諸多不是”。為此,許老爹撰文《我為什么以前反共現在促統》,旗幟鮮明地予以反擊,“誓以余年,為捍衛道理而戰!”
許老爹在文中坦言,“我以前之所以反共,是反對當時中國大陸實施的一些不當的作為和措施”。現在為什么不再反共而要促統呢?因為中國大陸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例舉了徹底消除階級斗爭思想、提升經濟成長、推行扶貧方案、推動科學教育、改善兩岸關系、發揚中華文化等六大進步。然后總結說,“冷靜思維,今天中國大陸的思想和作為,完全符合正常國家發展的原則,對兩岸亦屬有利。當年反共的理由,早已不復存在,當然不能為反對而反對,這就是我不再反共的理由。”
許老爹大聲疾呼,“我是中國人”,“臺灣與中國大陸一衣帶水,近在咫尺,搬不動,移不開,理性明智的抉擇,唯有選擇兩岸‘互利雙贏的統一方案,才是國家之福,全民之福!”
日前,許老爹深刻指出,馬當局主張兩岸“不統、不獨、不武”是政治語言、選舉語言,沒有真實的意義。臺灣的兩岸政策,早在1991年就已經完成并公布,那就是“國家統一綱領”。他表示,已經建言請國民黨和馬政府,恢復“國統會”和“國統綱領”。
建互信,化干戈為玉帛
為建立兩岸軍事互信,許老爹以其在島內軍隊中德高望重的地位,義無反顧地奔走于兩岸,繼續發揮著影響力。
2005年9月,許老爹和臺灣幾位參加過抗戰的老將受國臺辦邀請,出席在北京舉行的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會期將近,卻突然生病,高燒40度,住院打點滴。當他知道被邀請的人中有的因年老體弱、行動不便而不能參加會議,有的因害怕被臺灣當局扣“紅帽子”不敢去參加會議,心中非常不安。他毅然做出決定,說服主治醫生辦理出院手續,乘第二天的飛機趕往北京參加會議。在北京堅持開完會后,他又拖著病體,趕往福州以新同盟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中國同盟會成立100周年紀念活動。9月9日他再趕往南京,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向守志一起在當年接受日本投降的原址(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參加兩岸同歌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
面對近來島內一些“名嘴”在媒體侈談“漢賊不兩立”、“仇匪、恨匪”的聲浪,許老爹投書《海峽評論》提出《兩岸軍事互信,預防擦槍走火》。許老爹說,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是預防因誤會、誤解或誤判,“擦槍走火”發生意外的戰爭,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安定、穩定狀態。社會大眾,基本上應該不會有任何反對意見。許老爹認為,島內民間乃至退伍軍人、高級退役將領,懷著愛國情操,在不違背當局法令,符合當局政策,不“越俎代庖”的前提下,前往祖國大陸進行“交流”,讓雙方建立情感,減少敵意,消除“戰爭”隱憂,似乎不必過分苛責!他呼吁兩岸領導人和相關人士,能夠以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改革開放”時的勇氣、智慧和創意,完成這個理想,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真正享有“21世紀是中國人世紀”的榮耀。
老爹情,憐子如何不丈夫
當年,許老爹隨蔣軍離開祖國大陸,在紛飛戰火中告別新婚妻子時,說是很快就會回來的。然而,這一等竟是幾十年。當白發蒼蒼的許老爹再回到大陸的時候,他的妻子卻已不在人世。許老爹深深感嘆,那一刻,竟成了最后的訣別。雖然后來他在大陸找到了離散多年的女兒,但是與夫人的陰陽相隔,卻早已是永遠無法更改的凄涼與無奈。
上世紀80年代,經過一番周折,老爹終于和女兒許綺燕在臺北團聚。綺燕到達臺北的當晚,老爹用顫抖的雙手抱住痛哭失聲的女兒,一個勁地說:“能見面就好,能見面就好。”父女倆相擁,談到夜里12點多。老爹后來常跟人說,“每當談到這個女兒,總讓人感慨萬千。和她分開時,她只有三個月大,再見面已是四十載之后。”為了對女兒有所彌補,他后來每年總有一段時間在武漢,與女兒、孫輩、重孫輩組成的大家庭一起生活,舐犢之情處處洋溢。
在許綺燕眼中,父親柔情似水,總把自己當孩子看,恨不得把那幾十年的父愛一下子補償回來。后來綺燕每年一次赴臺省親,回家小住,每次都被父親珍愛得不得了,被一種深厚的親情感動得不得了。在女兒眼中,父親生活很簡樸,并不像自己以前想象的,做了高官就是錦衣玉食,父親的穿著干凈整齊莊重,被子破了、襯衣破了,補一補以后還在穿用。父親的菜肴也很簡單,有一點豆類,比如豆腐干就行。父親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沒有什么特別的嗜好。家里有好幾部電話,卻一再特別叮囑,只讓打自家出錢的那部電話,別的都不能打。雖然對女兒十分寵愛,但不是溺愛,每次許綺燕從臺北回大陸,老爹都要諄諄告誡:“小燕,你來時什么樣,回去還是什么樣。”
有硬骨頭精神的魯迅先生,當年因為愛孩子海嬰受人譏笑,乃作詩回敬:“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 出生入死的許老爹,有如此細膩的父愛,不亦魯迅先生“憐子如何不丈夫”乎。
老爹情,其實還體現在其禮士親賢上。在一些學者眼中,老爹是一位謙謙君子、諄諄長者。凡訪問過老爹的學者,對老爹仔細傾聽意見的儒將風度,記憶深刻;而臨別時老爹必親自將客人送至門口或電梯旁,更讓造訪者感動不已。筆者曾收到老爹一封親筆信函,墨跡之美如書法大家,賞讀之悅如沐春風。
老爹情,也體現在其對家鄉的關注上。因為女兒許綺燕在湖北長大,至今生活在武漢,老爹愛屋及烏,遂成了湖北、武漢的“常客”,還不時率臺商前往考察投資環境。他還將《雖千萬人吾往矣——許歷農文稿集》稿費,全部捐贈給家鄉安徽貴池的學校。凡此點點滴滴,無不透著老爹對家鄉的一份赤誠與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