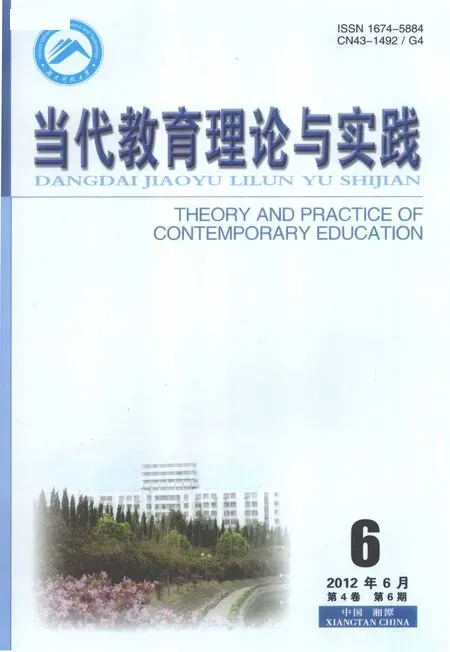語文教科書助學系統的研制規律
——基于教科書“教學”功能的思考①
韓芳芳
(湛江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廣東湛江524048)
語文教科書助學系統的研制規律
——基于教科書“教學”功能的思考①
韓芳芳
(湛江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廣東湛江524048)
本研究所指的助學系統是一個基于教科書結構功能“起點”和教學環境中學生這個教育“終點”上的研究性定義:學校教材建設中,助學系統屬于教科書編排形式結構的一部分,主要行使教科書的“教學”功能,它是針對課程目標和相應學習內容被設計的,引起學習發生、提示學習過程與策略、促使達成課程相關意義的學習結果、指導學生進行學習反思并助力促成學生學習行為改變的一系列條件性材料組合。它們往往共同為學生的“學”與教師的“教”助力,以此促成教科書“利教便學”功能的極大發揮。
語文教科書助學系統;教學功能;研制規律
語文教科書助學系統,簡單理解,就是對教材研究中較通行的教科書四大系統——“范文系統”、“知識系統”、“導學系統”、“作業系統”①顧黃初,顧振彪先生在"中學語文教科書的結構類型"的論述中指出教科書內部結構所隱含的知識和能力線索要借助于四個相互聯系的系統也即范文系統、知識系統、作業系統、導學系統組織起全部教學內容。它們可有不同的編排方式,從而形成教科書在結構上的不同類型。參見顧黃初,顧振彪.語文課程與語文教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75-76.的后兩項進行統整進而抽繹出來的概念。此種統整并非隨意而為之,而是建立在學科相關理論、教科書實際設計與以往研究的基礎之上。其中的導讀、練習等助學元素不僅發揮著各自獨特的功能,其間的聯系也甚為明顯,它們往往共同為學生的“學”與教師的“教”助力,以此促成教科書“利教便學”功能的極大發揮。在此基礎上思考助學系統的研制規律,不僅能為教科書的結構編排和內容設計提供科學借鑒,也為“教材教學化”的研究開辟了新的系統性探索路向。
一 教科書功能與助學系統的“教學”功能
研究教科書編排結構最終是為了教育過程中教科書功能的充分發揮,它無疑是指向教學中的“學”與“教”的。
立足于現代課程觀的教科書作用大致可從注重文化接受的觀點去理解。這種觀點強調不應該離開對如下問題的思考:首先是教學過程的基本目標,然后是如何整體的建構教學過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承擔的作用等。因此,這種教科書突出三大功能:信息功能、結構化功能和教育指導功能(也可稱學習指導功能)②信息功能指選擇、傳遞對學習者有價值的真實的信息、知識(真實性、思想性);結構化功能指有助于學習者建構自己的知識(系統化);教育指導功能指使學習者學會合理的學習方式(指導性)。參見鐘啟泉.現代課程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79-380.。也可從“一是實現教育目標最經濟有效的工具;二是輔助教師教學最好的工具;三是輔助學生學習的最經濟實效的材料”[1]這三方面理解。教科書助學系統作為教科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勢必也具有相同或相關的功用。希冀教材結構能促進語文基本內容學習的助學功能,促成學生種種學習結果的助學功能,又或是幫助教學工具、課程統整功能實現,基本上也屬于這三點的討論范圍。教科書不可避免盡力集結這些功能力量憑借目標導航下的教學思考形成對結構的反作用力,促使教科書結構不斷更新,使其在實際教學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學生的“學”生產更有益的價值。
曾天山在其《教材論》專著中從教學的角度思考了教科書的功能,并有如下表述:“教材的本質屬性與第一要素是教學性”[2],教材既能顯示“教學什么”,又具備“怎樣教學”的功能,同時顯示“怎樣教”為“怎樣學”服務的特性,就易顯示教材的教學功能,師生易于教學[2]。這就意味著教科書功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教學功能的充分呈現,且“教”是為“學”服務的。探討助學系統,雖然必要以“教學什么”為前提,然而概因其結構屬性,更多納入討論范圍的將是“怎樣教學”。這實際上突出了助學系統的策略性與方法論意義。
王榮生探討課程內容教材化和教材內容教學化,顯然也是從“教學”的角度拯失救弊如今略顯混亂的語文教學內容的:“課程內容教材化,實際上是要求語文教科書做好兩件事:一是要設計課程內容,對‘一般應該教什么’給出切實的回答;二是要對‘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做出有建設性的回答,使語文課程內容通過種種資源的運用得以具體顯現。教材內容教學化,實際上是要求語文教科書做好兩件事:一是局部的,要勾勒出教學一個點的主要步驟;二是完成一個大單位的設計,也就是將一堂課幾個點的教學連貫起來。”他還認為,“課程內容教材化、教材內容教學化應落實在語文教材的呈現方式上;在文選型語文教材中,主要是指選文之外的俗稱‘思考和練習’內容的呈現方式。語文教材呈現方式是語文教材編撰策略的具體體現……就絕大多數教師來說,其教學設計和所組織的教學活動應與該教科書的編撰策略具有較高的相關性。”[3]這里所說的呈現方式包括了助學系統的設計與組織,它建立在課程設計合理斟酌的基礎之上,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助學系統有助于教師形成教學設計從而加深學生對課程學習的理解。
二 教科書使用對象與助學系統的研制規律
上小節的論述使我們認識到教科書的功能和助學系統的“教學”功能將有助于我們形成連接課程與教學的功能性助學觀,促成教科書助學系統設計完善的動力。那么實際教科書是怎么體現助學設計的呢?如果從另一個視角——助學系統對教科書使用者的關照去解釋,助學設計將存在什么樣的規律呢?
(一)教科書實際助學設計的追問
被稱助學元素發達的香港啟思版教科書[4]中充斥著諸如此類的功能板塊設計或重復:在未進入單元課文編排前,編者設計并呈現了諸如“全書結構一覽表”的前置性概括說明;在某篇閱讀課文前編者設計了“作者剪影”,課文中又設置了“閱讀指引”,課文后則有“分析與探究”,并且有重復符號標示的學習重點、重復練習;閱讀、說話等部分都有“課堂活動”;寫作能力培養部分有“作法提示”;綜合能力訓練單元有“延展課業”;增潤單元有一系列“綜合能力訓練”;幾乎每個學習范疇都有“自我評估”。
人教2004年新課標版教材也設置有一些功能板塊,并有穩定的重復性板塊,舉例如下:分冊目錄前的“致同學們”,“閱讀鑒賞”課文后的“研討與練習”,“表達與交流”中的“寫作練習”、“課外延伸”,“名著導讀”中的“思考與探究”。
借助先前的理解,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些“指引”、“分析”、“練習”、“活動”、“延伸”、“評估”屬于助學系統的討論范圍,但是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同一質層不一致的板塊取名?“引”和“練”的區別在哪里?“析”與“評”的不同又在哪里?教科書中為什么要在相異的空間安置這些區別性個體?顯然,在結構探討中我們無法清晰而具體地回答這些問題。
(二)來自學習階段與教學事件的解釋
助學,顧名思義是為“學”而“助”,而“助”則是站在“教”的角度支持“學”。這里,我們需要把目光轉移到學習論對教學論的啟發上,以期從心理學的視角理解編者如此設計的理論用意和助學系統存在的“教學”價值。
為了拉近學習與教學的關系并方便描述,我將Margaret E.Gredler對加涅相關學習理論的研究稍作整合,改制③原表內不包括“教學事件”,參見(美)格萊德勒(Gredler,M.E.)著,張奇等譯.學習與教學——從理論到實踐[M].北京:輕工業出版社,2007:152-154.為表1。

表1 學習階段與教學事件關系表
加涅(Gagne)將認知加工概念應用于他的學習分析理論中,確定了須按照順序進行連續加工的9個學習階段。為了理解學習階段的功能,9個階段一般被劃分為3個時段:(1)學習的準備;(2)習得和操作;(3)學習的遷移。這種劃分的重要性在于它們在不同的學習中發揮不同的作用。據此,外在教學事件對學習的支持也相應存在自己的特點。簡要解釋如下:
學習準備:引起學生注意,告訴學習者目標和激發對先前學習的回憶是為新的學習設定的三個教學事件。于是教科書中,就有了“致同學們”、“全書結構一覽表”這樣的知識結構序列提示。三個教學事件都能在此找到相關聯系,學生有可能得到明確或有益的自主性激發,形成與新學習“對話”式信息交換的動力。
習得和操作:學習的核心階段,包括知覺的選擇,語義編碼,提取和反應、強化。教學首先呈現的是刺激特征或是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習者相互作用的情境。接著,向學習者呈現伴隨所需要的提示或線索的特殊情境。提供學習指導是教學的重要事件,它幫助“學習者將新能力轉換成稍后回憶的編碼”和“在簡單學習和復雜學習之間及有效學習和無效學習之間做出了區分”[5]。為了確定編碼的有效性,需要引發學習者新的技能動作。隨后,提供的反饋表示或者對動作進行必要的糾正,或者通過對已達到目標的肯定提供強化。反映到教科書中,我們需要在不同的學習和學習過程中加以考慮,從而能夠據此理解為什么單元內的某篇課文中設置了“閱讀指引”,課文后則有“分析與探究”、“課堂活動”、“自我評估”,并且伴隨著不斷的重復加固。如此基本的序,實際上就是為了保證一個伴隨著獲得、保持、回憶、作業和反饋內容在內的核心學習階段的順利進行。
提取和遷移:教學中得出結論的環節為提取和遷移提供了有線索相隨的新的學習的評估。在評估部分,應該給學生呈現新的情境或者例子,用以確定學習不僅限制在幾個例子的范圍之內。教學應該以為了促進保持和遷移而特別設計的刺激作為結束。教科書中,諸如“課外延伸”、“綜合能力訓練”和“自我評估”等項目可以由此解釋。
總體看來,加涅的理論在試圖尋找學習者和信息加工環境之間的此彼相生的關聯,比較恰當地闡釋了“教學”這種幫扶性外在學習條件對學習過程本身的意義。“教師和教學設計者選擇語言描述、問題、目標、圖表和其他刺激來誘導學習者的內部加工”[5],它們可以滿足九個教學事件的需要,也可以啟發我們對助學功能的理解和使用。
充分關注加涅的學習階段論和條件論,為我們奠基了一個學習過程中學習事件和教學設計應該如何的概念,提供了一張助學系統可以如何的愿景圖。設計中的功能及各種別具匠心的“刺激”、“指導”也被提示應充分注意。其背后的核心意義在于助學系統的設計要暗合某些學習與教學的基本規律,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心理需要,實現教學對學生的完整關注。
綜上所述,學校教材建設中,助學系統屬于教科書編排結構的一部分,主要行使教科書的“教學”功能,它是針對課程目標和相應學習內容被設計的,引起學習發生、提示學習過程與策略、促使達成課程相關意義的學習結果、指導學生進行學習反思并助力促成學生學習行為改變的一系列條件性材料組合。研究取義傾向于教材探討中的學習論與教學論,特別強調其附屬教科書結構所示辯證關系中有效輔助學習的意義。其根據學生認知與情感發展的規律和教育教學規律來設計,在語文教育領域區別于傳統意義上教科書的范文和知識系統,致力于形成教科書中的輔助習得性功能結構。
[1]高凌飚.基礎教育教材評價:理論與工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天山.教材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3]王榮生.對語文教科書評價的幾點建議——兼談語文教科書的功用[J].中國教育學刊,2007(11).
[4]布裕民.中國語文[M].香港:啟思出版社,2005.
[5](美)格萊德勒(Gredler,M.E.)著,張奇等譯.學習與教學——從理論到實踐[M].北京:輕工業出版社,2007.
(責任編校 王小飛)
G42
A
1674-5884(2012)06-0102-03
2012-04-09
韓芳芳(1984-),女,河北黃驊人,主要從事語文課程與教學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