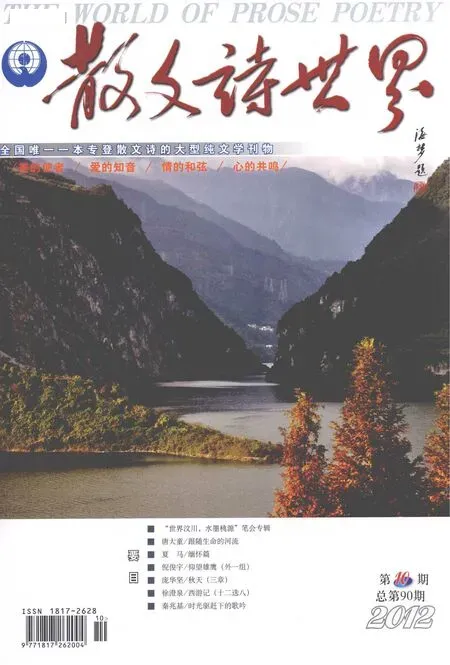以牛為命,散文詩為吟——讀許澤夫散文詩集《牧人吟》
黃永健
在外奔波20多年,始終不敢忘懷故土肥東的哺育之恩,人到中年卻因為研究散文詩走進了故鄉的文壇。最近從全國各地文友口中得知安徽肥東、肥西都活躍著一批散文詩作家,這其中先是認識了趙宏興(紅杏),接著認識了張道發,他們兩人的散文詩作享有“實力派”的美譽,應不過分。今年夏天認識了許澤夫先生,人高馬大,干練成熟的縣府公務員,與我一樣放牛娃出身,他如今已是縣城有點小權,可以喝點小酒,坐部小車的人物了。可是他自命為一介書生,視文學如紅塵知己,職場疲憊之余,回家以文字耕耘一方凈土,坐擁書城,物我兩忘,樂此不疲,寫作出書之余,在肥東縣城的醫院里辦報紙,在渡江戰役紀念館辦小報,在縣城辦《分水嶺文學》,策劃大型文學征文大賽。最近,許澤夫散文詩集《牧人吟》脫穎而出,作者說:“我決意要寫一部關于牛的書,并且用我熟悉的散文詩。散文詩就像四月隨地生長的不拘小節的綠草,喂養著勤勤懇懇的牛。”
我要寫它們,其實它們內心有陰云也有陽光,有喜怒也有哀樂。它們不會表述,更不會宣泄,我就做他們的代言人吧,寫一部很厚很沉的關于牛的散文詩集。
在這里,作者認為一首一首的散文詩猶如江淮丘陵上四月間的青青綠草,不擇地而生長,無拘無束而生命澎湃,用散文詩這種帶有“元詩”性質的文體來表現野性的牛善良的牛,則文與牛相得無間,詩與人相得無間。
散文詩自波德萊爾創始,流播演化于世界文壇,用學術語言來說,它產生了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文類變體”。五四時代的散文詩與當代中國散文詩已產生了巨大的差異,同時當代中國散文詩也因為中國版圖之大,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鄉文化、新舊文化、男女文化、階級文化等的參差錯落而產生了不同的語言風格、不同的審美訴求。我在《中外散文詩對比研究》一書中,提出了現代中國散文詩的“七種現代性訴求”,其中就有一種叫做“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訴求”,以懷鄉懷古的姿態審視、控訴現代物質文明,從而對氣焰囂張的現代物質文明發生有效的校正、平衡作用,這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訴求”,使得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因為情感的直覺警示而更加理性地邁步向前,許澤夫的含淚之吟為什么能夠得到都市里的讀者的情感認同,原因就在這里。
正如許澤夫所說的,我們都是農民的后代,我們不能忘本。第一是不能忘卻“農民”這兩個字所承載的民族文化包括鄉土文化之本;第二是不能忘記“牧牛”這兩個字所承載的人類情感(原真情感)之本。許澤夫以丘陵大地上一牧童的“根情”(白居易語)作為他散文詩集《牧人吟》的語言依據和形式依據,長出了“苗言、華聲、實義”,整本書分則各自獨立,合則成為丘陵大地上的一個特殊時代的備忘錄,一首長詩,一部長篇小說。即使從散文詩的藝術技巧上來看,這部散文詩集也具有可堪點評的特立獨卓之處,如剛柔并濟的抒情格調、詩語節奏的講究、意象語象的自然凝煉、地域方言的巧妙入用、比擬手法的逼真貼切等。當然,散文詩是一種緣情體物的文體,要言之有物,有具體的場景、故事和情節,一旦離開場景說話,以散文詩來解釋“關于牛的成語”,則很難奏效。
這篇小文,不成評論,感謝《牧人吟》給我帶來的不一樣的閱讀深度和寫作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