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欣:兩岸和平發展與統一運動的推手
■ 姚同發
她是最早到祖國大陸訪問的“海歸”人士,在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便“回到了家”;她亦步亦趨地踏著前輩的足跡,在島內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與統一運動,用生命書寫著燦爛人生;她曾在美國出版專著《一國兩制在臺灣》(英文版),并贈送給五百多位參眾議員,一時引起不小的轟動。她就是臺灣著名律師、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
“我終于回到家了”
1952年出生在高雄的紀欣,祖籍江蘇,是臺灣所謂的“外省人第二代”。從懂事開始,她就常常在夜間偷聽父親與朋友聊天,聽到他們感嘆國民黨不爭氣,一路逃到臺灣,與家鄉父母不能通信,注定要做個不孝子。初中時,年年雙十節都被迫集中到“總統府”前聽“明年將在南京慶祝國慶”的誓言,心中不免納悶:偏安于臺灣的國民政府能代表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地大人眾的泱泱中國嗎?兩岸都是中國人,為何不能往來?
入高中后,或因年輕人的反叛心理,或為賦新詞強說愁,她的書包里塞滿了存在主義的書,卻從未想通人生的意義。直至讀到陳映真的《將軍族》與《唐倩的喜劇》才稍微理解,臺灣人的壓抑多半出自對政局的不安、對孤島前途的茫然,與西方知識分子的苦悶并不一致。后因某種機緣讀到不少大陸上世紀30年代的文學作品(當時是禁書),其中魯迅的《阿Q 正傳》、老舍的《駱駝祥子》最令她震驚,由此聯想到中國人悲慘的宿命,若沒有新中國的成立,恐怕難以改變。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所著《羅亭》中“俄羅斯可以沒有我,我不能沒有俄羅斯”那句名言,更促使年輕的紀欣經常捫心自問:我的中國在何處?
1974年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后,紀欣赴美留學,專攻韓戰史。這一時期,她對中國近代史、對兩岸問題有了更透徹的了解,也結識了一批來自臺灣、同樣關心兩岸問題的志同道合者,并由此參與到海外的統一運動中。那時,她接待過不少臺灣的政治受難者及黨外人士。他們中有不少人后來成了民進黨的高官顯貴,事后想起來覺得對他們的那份熱情不值;而與多位臺灣上個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前輩的相處,則對她日后人生的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中美建交、祖國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后,紀欣隨著一批思想活躍的年輕人從美國飛往祖國大陸。可以說,這是祖國大陸最早接待的一批海外人士。當飛機徐徐降落在北京機場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終于回到家了。那時,祖國大陸改革開放才剛剛起步,所到之處遠不如今日之繁榮進步,甚至不如當年的臺灣,這使得同團不少海外臺胞露出不想認窮親戚的傲氣。而她則恰恰相反,暗暗立下了兩個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國家富強和兩岸統一。
1983年,紀欣在美國見到了自己少女時期的偶像——臺灣著名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她至今仍記得陳映真夫婦離開美國前的那個晚上,二十多人聚在一家餐館為他們餞行,陳映真情緒高亢地談著第三世界人民團結與兩岸和平統一,并與大家相約在臺灣相見。果然,幾年后臺灣解嚴,當晚在座的十多人相繼回到了臺灣。紀欣也于1988年回臺定居,開始其新的人生途程。此時,她已經在美國取得法學博士學位(J.D.),并已成為美國加州執業律師。
用生命書寫歷史
回臺初期,紀欣在工作之余將所有時間、精力投入自己有興趣、又比較不陌生的婦女運動。幾年后,陸續撰寫出版了將婦運經驗與法律知識結合的著作:《女人與政治——1990年代臺灣婦女參政運動史》、《美國家事法》等。這于她只是想略盡知識分子言責而已。
更大的挑戰還在于,面對臺灣社會甚囂塵上的“臺獨”和“去中國化”聲浪,她經常撰文駁斥,卻屢遭報社退稿。她一直認為,只要自己努力寫作、誠實勇敢地表達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觀點,即可問心無愧。但2000年以后島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卻使她猛然省悟,臺灣社會不缺進步的知識分子和隱性統派,缺的是勇敢站出來主張統一的愛國知識分子。在統派前輩一再曉以大義、勸說鼓勵下,她終于義無反顧地追隨前輩“用生命寫歷史”的足跡,踏上了統一運動的不歸路。
基于了解臺灣人多傾向維持現狀,以及對香港澳門回歸后的觀察,她始終相信,“一國兩制”是兩岸在“一國”之下,唯一能以和平方式統一,并確保臺灣在統一后能長治久安的正確途徑。因此當她看到2001年春夏的幾個民調顯示,有三到四成的民眾愿意接受“一國兩制”時,竟徹夜難眠,立即邀集有識之士對“一國兩制”與其在臺灣實踐的可能性展開研討。并于2003年底完成《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寫作和出版(轉年7月再版),系統完整地論述了“一國兩制”在臺灣實行的理論根據、客觀條件和實踐的可能性,在島內一片“臺獨”濁浪中,發出了難能可貴的聲響。
《一國兩制在臺灣》出版后不久,大約在2004年二三月間,嘉義大學歷史系吳昆財教授在看到這本書后,在網上發表文章,肯定紀著出版的重要意義。稍后美國舊金山華人電視節目主持人Stone在網上看到吳教授文章,打越洋電話專訪紀欣,美國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也打電話給她,請她去舊金山演講。當時在演講現場聆聽的王勝煒博士,會后表示想把該書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件被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未曾想王博士旋即著手翻譯,紀欣逐章審校,終于在2006年上半年得以在美國出版。11月初,除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舉行隆重首發會外,她和王博士還到了芝加哥、紐約及舊金山舉辦新書發表會。12月下旬,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將英文版《一國兩制在臺灣》贈送給五百多位參眾議員,一時引起不小的轟動。
有一段時間,一些人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統一聯盟1988年成立時,就公開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為何22年后要投入和平發展運動,難道要放棄統一的目標?為此,紀欣曾在不同場合,試著回答統派決不會也不可能放棄統一的目標。2010年8月,她又將自己對于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辯證思考,寫成《和平發展與統一運動》一書出版,受到各界的肯定。但是,在歷經兩岸關系諸多起伏曲折,即令看到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紀欣仍不免為統一的進程感到焦慮。她表示,仍將一如既往地為實現統一的目標,繼續書寫燦爛的華章。
接任統一聯盟主席
紀欣在2003年加入了陳映真出任創盟主席的中國統一聯盟,轉年當選統盟執委與第二副主席。2009年1月,她有感而發,寫下《臺灣需要一個統派的第三勢力》,呼吁分散在臺灣各地隱性的統派,勇敢站出來,攜手壯大統派的勢力。該文經多方轉載后,許多讀者輾轉來函或致電留言,鼓勵她不要只是坐而言,必須起而行。同年4月11日,她接下中國統一聯盟主席一職,成為統盟創盟以來首位女性主席。
由于財力不足,統盟主席都是“義工”。紀欣的職業是律師,因為精力大多放在統盟工作上,收入自然受到影響。這樣,維持簡樸生活、在臺北租房居住、出入搭捷運,便成為她無怨無悔的日常生活。她自謙,其實自己并不適合這個位置,因為從來沒有在公務體系中工作過,不善管理,不懂群策群力。但她堅信,只要“起而行”,朝著既定的目標走去,就一定能夠有所進步。
就在紀欣接任主席的2009年,統盟的各項工作依然有聲有色。這一年統盟組織了四個內地參訪團,一是北京訪問團16 人;二是百人代表團出席60 周年國慶閱兵及聯歡晚會;三是恢復“港澳一國兩制參訪團”活動;四是24人祭黃陵團,前往西安、延安。另外,統盟交流部、組織部、地區分部還組織“山西文化巡禮團”、湖北四川參訪團、黑龍江參訪團以及福建研習營等活動。這一年,統盟還接待全國臺聯、江西省臺聯、福建省臺灣研究會、中國社科院臺研所、河北省海外聯誼會等九個訪問團,以及美國費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訪問團、歐洲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德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澳門黃埔同學會訪問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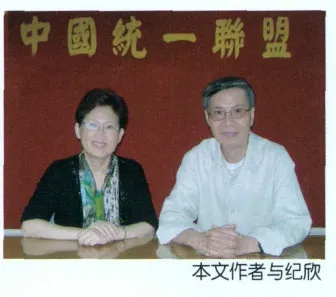
一段時間以來,當反“獨”和“和平發展”成為主旋律后,促統的話鮮有人提及,統派促統的文章投書臺灣媒體也沒人敢登。面對這種情況,紀欣奔走各方聯絡呼吁,終于在2010年3月27日,由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動黨、夏潮聯合會、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等19 個統派團體,正式成立了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紀欣成為兩位總召集人之一,島內的統一運動露出了些許曙色。
2010年4月29日,胡 錦 濤總書記在上海西郊賓館會見出席世博會開幕式的臺灣各界人士40余人,除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外,還有臺灣各界代表、民間統派團體負責人。紀欣有幸代表中國統一聯盟,受到熱情款待,還被安排與胡錦濤總書記單獨照相。這對紀欣推動統盟工作,無疑是巨大的激勵與鼓舞。
老爹文集的催生者
老爹者,備受兩岸尊敬的儒將許歷農先生也。多年來,紀欣一直企盼能看到老爹的傳記或回憶錄出版,認為老爹過去15年的超凡勇氣、愛國情操、獨到見解、堅強毅力,必須被記錄下來,讓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及全球的華僑華人知道,在臺灣,有像老爹這樣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不唯唯諾諾的正派人。
為催生老爹文集的出版,紀欣先上網搜尋相關的資料。可惜,除了近兩三年的幾篇文章、電視臺的專訪外,就是一些零星的新聞稿。萬般無奈之下,她只好硬著頭皮,帶著錄音機去見老爹。老爹一看到錄音機,立即停止講話,她只好將列印的資料留下,決定不再勉強他老人家。沒想到幾天后,老爹給她打來電話,說如果愿意的話,可以幫他整理一下家中及辦公室的資料、手稿,以便留給他的晚輩看看。抱著如獲至寶的心情,紀欣從老爹手中接過一個陳舊且沉重的箱子,心頭的感動及責任真是無以言表。
打開箱子,果然不出所料,里面盡是老爹珍貴的手稿。紀欣記得,在第三屆“國民大會”時,她被當時擔任新黨黨團召集人的老爹指定為黨團發言人,每日坐在老爹身邊,發現老爹每一次發言,不管是三分鐘的致詞或一個鐘頭的演講,一定親筆寫下所要講的內容,并且一改再改。看著老爹一頁頁手稿,往事歷歷在目,讓她油然而生幾多敬意。
盡管她對老爹作過承諾,在老爹百歲生日時再發表他的手稿,但她還是忍不住立即將其文稿分門別類,并且一篇篇親自打字、校對,唯恐遺失、破壞了真跡。在邊打印邊拜讀老爹文稿的過程中,她發現,老爹早已從早期捍衛“中華民國”,走向捍衛全中國的主權完整;從希望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走向認識祖國大陸當前所實踐的制度正好符合三民主義的理想;從反共不反中,走向支持兩岸和平統一;從支持中國國民黨的創黨理念,走向支持“能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那一邊”。
2007年,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了紀欣編的《許歷農文稿集》,稍后,祖國大陸出版部門也出版了該文稿集。盡管文稿集與傳記、回憶錄會有所不同,但讀者應能從老爹在過去15年之中的不同時空、面對不同政治環境、針對不同對象、就不同議題所寫的講稿、文章以及訪問稿中,清楚地看到老爹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在紀欣看來,本書所記錄的不只是老爹個人的文稿,它同時是一部臺灣政局與兩岸關系的現代史,未來有人為老爹立傳時,必將引用這本書中的第一手資料;而研究這一段臺灣與祖國大陸歷史者,也將參考老爹在本書中的諸多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