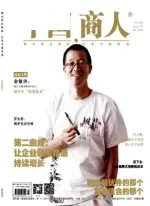“干干凈凈站著賺錢”要知道底線——對話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寇科研

民營企業應借助專業人士力量幫助企業發展
中國商人:1980—1990年代,由于對民營經濟前景的憂慮,胡雪巖式的“紅頂商人”發展模式成為眾多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安全選擇”,以致于“掛靠”某家國企,或者“戴紅帽子”的操作方法曾風行一時。當前,由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市場中的地位差距,千方百計靠近國有資源,依然是不少民營企業家的重要選擇。您認為民營企業應如何在企業經營戰略和法律底線之間安全建設?
寇科研:民營企業家當年選擇“掛靠”國企或“戴紅帽子”是基于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民營經濟逐漸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國家也通過企業體制改革對“紅帽子”企業進行規范。如果那時一些戴上“紅帽子”的企業,按照當時的相關規定履行了改制的程序,并且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批準,我個人覺得目前應該不會有問題。在《公司法》頒布之后,若現在還戴有“紅帽子”的企業,應該學會如何規范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跟相關政府部門協調,依據相關的政策法規解決。
在當前,有的民營企業家選擇與國有企業進行各種合作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企業需要生產發展。但現在國家法制比較健全了,在法制健全的環境下,若再去“掛靠”或借用國企的資質,就是違法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會給企業的經營發展埋下巨大的隱患。民營企業要利用國有企業的資源發展自己的業務,首先應對所在行業的相關政策動向有充分的了解。目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仍處于深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國家經濟的調控實際上是在加強,這時企業的發展戰略符合國家的調控政策就顯得至關重要。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可充分發揮自身對市場反應迅速、資源利用率高的特點,采取與國企設立合資公司或國有資產入股的方式等多種形式與國有企業合作,利用現代企業制度約束雙方之間的合作關系,以實現共贏。
中國商人:跟熱衷于尋求體制資源實現企業快速發展的企業家不同,孫大午式的企業家在長期經營過程中,刻意選擇了跟體制資源和公共權力資源保持距離,但最后卻在融資中出了問題。您認為應如何利用日趨完善的法制環境,實現一些民營企業希望“干干凈凈站著賺錢”的愿望?
寇科研:這一良好愿望的實現有待于法治狀況進一步改善。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日臻完善,但在法律的執行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民營企業自身規范發展,努力做大做強是根本,但若因為體制的種種弊端,選擇完全不和國有企業打交道、與公權力資源保持距離也是不現實的,企業的發展不可能脫離現實環境。
民營企業家要想干干凈凈地賺錢,不去觸犯法律是一個底線,因為在不對等的市場環境中,本身就處于比較弱勢的地位,一旦觸犯法律,危機來臨時企業馬上就會垮掉。在現行體制下,民營企業也可能與國有企業、政府公權力資源進行合作,國家對一些行業的扶持政策也可以借鑒。比如民營企業投資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項目,可以向國家有關部門申請減免企業所得稅,通過參與政府鼓勵的公共事業項目建設獲得相應的政府補貼等,通過申請高新技術企業、入住一些當地政府設立的產業園區,可以獲得當地政府的稅收優惠或補貼。在日趨成熟的市場環境下,民營企業發展應當從過去初期階段依賴老板個人能力和關系轉變為依賴多方的力量,尤其是要借助專業人士的力量幫助企業發展。國外就有專門為企業提供合理避稅服務的會計師或律師,國內目前的專業服務市場也在逐漸成長。比如,如果你的企業產品質量很好,并有一定行業前景,可以通過向VC/PE等機構進行股權融資的方式來解決資金問題。
民營企業要用好公權力這把“雙刃劍”
中國商人:一個民營企業的倒掉,會牽出一大批涉嫌貪腐的官員,而一個官員的倒掉又往往牽扯出大大小小的民營企業。“官員與企業”命運攸關的現象反映出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即:一個超速發展的民營企業背后,往往站著一位可以動用公權力和公共資源的官員(保護傘)。這種民營企業依靠官員獲得快速發展的模式,往往被社會指責為“官商勾結”。您認為一個民營企業家與官員之間應如何保持一種“距離上的美感”,從而實現企業的長期安全發展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允可的基礎上?
寇科研:這個問題出現的根源在于目前民營企業生存的環境。在目前國民經濟的很多領域中,還是國有經濟或政府權力為主導,民營企業想要在某個領域分一杯羹,不得不跟國有企業或相關的政府部門合作,如果不合作,就可能無法介入這個圈子。但與公權力的合作是一把雙刃劍,弄不好就會“走火入魔”,有的企業家為了最大限度的追逐利潤就鋌而走險了。
拋開制度層面的原因不談,一個企業要想長遠發展,成就百年基業,短期的行為是萬萬要不得的。一方面企業要發展不得不與官員打交道,但不能為了利潤鋌而走險,這樣可能一時獲得巨大利益,但這種行為是不可能長久的。作為真正的企業家,應該有自己的原則,當有些部門或有些人員提出無原則的要求時,要懂得適時拒絕。雙方擺正自己的位置,才能實現良性互動。與國有企業或官方打交道有獨特的方法,民營企業不能只想著背靠某種壟斷資源或官員權力去攫取超額利潤,應當看到你的超額利潤背后是對他人權利或者整個行業的侵害。
另外,民營企業自身守法,規范經營,提升自身業務,這樣民營企業才有底氣與國有企業保持距離。民營企業自己要強,只有自己做到不能讓國有企業忽視你的時候,才有一定資格去談保持距離,如果民營企業完全依附到國有企業身上,就很難去談所謂的“距離上的美感”。
中國商人:近年來,一些民營企業已經熟悉了利用媒體資源,建設和形成對企業戰略目標有利的輿論環境,但也有相當一批企業在媒體的監督性報道中崩盤。您認為,民營企業或民營企業家應如何實現與媒體和公共輿論的理性互動,從而確保企業發展既是合法的,也是受公眾歡迎的?
寇科研:企業發展的合法性是要靠企業守法經營,這是無法通過與媒體互動來保障的,媒體的包裝可能會起一時的作用,但不可能永遠掩蓋企業的違法行為。一些民營企業之所以在媒體的監督性報道中崩盤,更多是因為本身就有問題,不能將主要責任歸于媒體的監督性報道。
現在媒體信息傳播得非常快,尤其是手機互聯網等新媒體,一夜間就有可能讓消息傳遍每個手機客戶端,因此,企業必須要重視傳媒的力量。針對如何與媒體和公共輿論的理性互動,首先,企業必須有媒體意識。什么是媒體意識,就是知道自己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企業的所作所為是處在一個信息傳媒中,企業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有與外界溝通的人員與機制。其次,要有危機意識。俗話說“商場如戰場”,若出現輿論危機問題,企業應當認真及時予以應對,準確、依法處理問題,不要單依賴于自己傳統的做事方式和自身力量,要全方位整合策劃、公關等行業專業人士的力量來迅速降低不良影響。此外,還應該在平時至少應與行業相關的媒體保持一定的聯系和溝通,良好的媒體關系不但有利于企業獲取行業動向或進行自我推廣,在突發事件發生時也能快速找到應對渠道。
避免財產糾紛,民營企業須引入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中國商人:隨著中國富有企業家群體的日漸壯大,民營企業家夫婦之間,子女之間,有關企業繼承權、私人財產分割等問題引發的家族矛盾也越來越多。您認為民營企業家應如何建立個人財富、家族財富和企業財富可持續發展的安全機制?
寇科研: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家的個人財產和民營企業財產迅速膨脹,但是一些民營企業家的個人財產、家族財產和公司財產是沒有分開的,因而使得在財產分配方面問題比較復雜。
首先,企業家要把個人財產和企業財產分清,產屬清晰以后,再談建立個人財產管理機制。中國的民營企業好多都是家族企業,家庭成員往往擔任企業的要職,可能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各成員以自己的財產投入企業運營,但對于個人如何從企業中獲得回報卻沒有一個清晰的安排,有的企業家因出于稅收或其他考慮往往從企業中領取不高的薪水。要避免出現財產方面的糾紛,民營企業必須引入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將家庭成員所擁有的財產與企業財產有關的部分進行區分,同時將家族成員的財產權益分配納入公司的管理機制之中,并設立完善股權激勵、績效考核機制來使得企業發展的權益能在家族成員間合理分配。
在企業家個人財產問題上,涉及遺產管理的問題,為避免爭議,可以走法律程序立遺囑,在法律上定清晰,以及做相關的公證,在有生之年界定清楚。
中國商人:作為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有為數眾多的人都積累了“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因而也隨之出現了屬于這個群體的煩惱:如何在有生之年保住已然擁有的一切?如何讓子女把家族財富安全繼承下去?也有人還沒到這一天,就由于種種原因突然離開這個世界。您認為,在巨額財富之外,民營企業家應如何找到人生的終極安慰?或者換句話來說:什么樣的理念可以使企業家在世時能夠安全保有自己的財富?而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不會由于財富問題產生過多的擔憂和遺憾?
寇科研:談到民營企業家,好多人都會想到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在復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可能個別人的發家致富史中還存在灰色的一面,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就否定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經濟的重大貢獻。我們的社會目前還處于變革時期,可能制度層面還存在一些不確定的因素,但總體而言法制越來越健全,企業的發展越來越規范。民營企業家要想使得個人財富得到保障,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首先需要注意樹立風險意識,平時要謹言慎行,一定不要做違法的事情,不要自我膨脹,做企業和做人一樣踏實、樸實才能長遠。同時,還需要健全企業的管理制度,通過專業人士管理企業和財產,拿出相應財產進行適當投資活動以確保資產保值增值。
說到終極安慰,這有點像哲學命題了。首先要轉變觀念,中國人的觀念是以家為單位,我的是我的,也是我家的,并且要傳給子孫后代。但是現在企業家應該具備一個理念,企業家應該意識到自己的財富來源于社會,財富越多,責任越大,應該對社會有相應的責任感和回饋意識。在美國、歐洲等國家,企業家的子孫想不勞而獲很難,遺產稅立法的目的是希望促進社會財富的流動,而在中國這種思想是很少見的,現代社會這種觀念需要改變。其實駑架一定規模的財富是需要有一定的人生閱歷和綜合素質的,有時候給孩子過多的財富并不見得是好事。一個人要活得有價值感,其實是別人和社會對你的認同和贊許,自己的財富和能力幫助了更多人,這樣才能給自己更大的成就感;反過來,一個企業家、一個企業得到社會越多的認同和贊賞,所獲得回報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