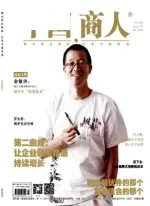一個模糊:上市遇阻官司來襲

福建歸真堂,原本好好的醫藥企業,一切合法的資質都齊全,為何偏偏上不了市?迄今為止A股市場沒有哪一家公司申請上市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
在證監會留下的相關上市信息中,歸真堂的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上市信息,一應俱全。目前這家公司的上市申請,還處于“落實反饋意見中”。
一條微博引發的慘案
“福建的歸真堂上市募資將用于年產4000公斤熊膽粉、年存欄黑熊1200頭等兩項目。已經省廳初查并且通過了!如果真上市,那今年就是月熊的末日。”2012年2月,云南衛視自然密碼制片人余繼春的此條微博被大量轉載,從而讓歸真堂活熊取膽事件迅速傳播。
從我掌握的材料來看,福建歸真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以稀有名貴中藥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的綜合性高科技生物制藥企業,主營業務為黑熊養殖及熊膽系列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擁有我國南方最大的黑熊養殖基地。2012年2月1日,證監會創業板發行監管部公布新一批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開募股,簡稱IPO)申報企業基本信息表,歸真堂榜上有名,備注為“落實反饋意見中”。
2月中旬,某非政府組織致信證監會反對歸真堂上市,72位社會知名人士聲援支持,迅速引起公眾關注。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德國《圖片報》、英國廣播公司等西方媒體紛紛轉載、報道,指責“活熊取膽”行為,呼吁中國將其取締,進而質疑中國傳統中醫藥的有效性。與此同時,國內部分媒體也紛紛報道此事,指責企業虐待動物,主張采用人工合成產品代替天然熊膽汁制品。
我想,活熊取膽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絕大多數網友對于歸真堂再度上市一事充滿憤怒,這是可以理解的。盡管歸真堂內部人員說取得熊膽是通過“無痛”、“無管引流”的方式,不會對熊的身體造成任何傷害。這種解釋在亞洲動物保護基金會的外事總監張小海看來,基本上是無稽之談。張小海對我說,“給熊取膽過程中的每個步驟,都無比疼痛。”
張小海談到,從1993年開始,就一直表示不可能有任何一種人道的方式可以從熊的身上活體取膽,痛苦不僅僅表現在抽膽的過程中,它還表現在熊的囚禁,指熊能夠遭受更多的、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痛苦,比如說它的骨骼、牙齒的問題,比如說身體上的其他傷痛,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它精神方面的傷痛,這都是熊在被活熊取膽這樣一個操作之下所遭受的痛苦。
據我所知,熊取膽汁后在骯臟的生存環境底下它的內臟會感染,所以有些熊的壽命會很短,三年、五年可能就死了;有一些活的時間比較長一點,但會慢慢因為膽囊病變,導致膽囊發炎;有的熊會被做第二次手術切掉一部分感染的膽囊,供膽的能力會越來越低;有一些養熊廠會把不能夠出膽的熊用來繁育小熊,小熊繁育出來了,老熊就慢慢老死、病死了。
慈善人士欲1.2億收購歸真堂股權阻止上市
福建歸真堂事件升級,公益慈善組織“中國SOS求助”創始人白一鵬向我透露,其已經聯合幾位自然人籌措了1.2億元資金,計劃對歸真堂的股權進行收購,2月8日已經正式發函給歸真堂公司及其部分股東——幾家創投公司。在歸真堂排隊IPO前發出收購邀請,意欲阻止歸真堂的上市計劃。
2011年歸真堂上市風波第一次引起媒體關注時,白一鵬曾經計劃對歸真堂進行股權收購,以阻止其上市融資。而當年白一鵬籌措的收購資金為5000萬元,如今他已經聯合幾位自然人一起籌措了1.2億元的資金,計劃再一次發起對歸真堂股權的收購。
按照白一鵬的話說,在此次計劃出資收購歸真堂股權的合作伙伴中,有的擁有海外市場的營銷渠道,有的擁有醫藥領域的市場經驗,與他們合作,將有利于歸真堂的發展。一旦入股成功,也將以股東的身份讓歸真堂的發展逐步脫離“養熊取膽”行業。
歸真堂副總吳亞告訴我,歸真堂從2009年開始籌劃上市事宜,并于2010年初開始接受萬聯證券的上市輔導,直至此番申請上市環保核查。
在我看來,歸真堂未必會被取消上市資格,因為證監會只是對上市文件做調查,不會涉及倫理方面的審核,只要歸真堂是一個遵守中國現行法律的企業,它就具有申請IPO的資格。如果它的行為不符合現行法律,它不僅沒有資格申請IPO,其經營牌照也應該被工商管理部門收回。由于目前的IPO仍然實行審核制,因此它提出申請不等于一定能通過。但是,名人們所從事的聯名上書行動,期望運用權力來阻擋一個企業的上市申請,這對于資本市場來說卻是個不值得肯定的行為。只要是合法存在的公司,都有可能獲批上市。歸真堂沒有污染環境,沒有損害公眾利益,卻因涉嫌虐待動物而遭到民眾的強烈抵制。
這是歸真堂第二次提出要啟動上市程序,此前2011年的上市計劃在剛剛通過福建省證監局的核查程序后就迅速被輿論狙擊而一度停擺。歸真堂上市募資將主要用于擴大熊膽粉項目,增加黑熊繁殖數目。動物保護組織認為,歸真堂如果上市,其規模就會變得更大,就會傷害到更多的黑熊。雖然他們都有林業等部門的相關證件,但是這其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這種活熊取膽的殘忍方式,已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精神相抵觸。
很明顯,在我從眾多反對活熊取膽的人那里得知,活熊取膽在公眾眼中是一個殘忍而不道德的行為。為了抽取膽汁,人們要在取膽黑熊的腹部通過手術制造一個長期不能愈合、深入腹腔直達膽囊的傷口。這樣的傷口以及每日反復抽取膽汁的操作,給取膽黑熊的身體以及心理造成長期的巨大折磨。歸真堂上市擴大規模,將有更多的黑熊受此折磨,這樣一家以活熊取膽為主業的企業,不應獲得上市批準。
歸真堂究竟該不該上市?
據我了解,歸真堂事件發生后,危機公關公司迅速做出反應,建議歸真堂2月22日首次對外開放養熊基地,但兩小時的參觀未能徹底消除媒體和外界質疑。媒體記者既然可以參觀,那亞洲動物基金會要求參觀為何卻被拒絕? 參觀后,歸真堂要求記者填寫調查表,表明對“活熊取膽”的態度,這似乎也是公關手段。
歸真堂事件將關于企業商業道德方面的爭論推向高潮。歸真堂創始人邱淑花很后悔當初要上市。實際上,對歸真堂而言,這一場全民圍觀未免就不是好事。如果歸真堂已上市,問題才被全民注目圍觀,那才是真正的危機,不僅投資者難以買賬,而且要面臨“欺詐上市”的追責。
我認為,歸真堂事件反應出最關鍵的問題一是熊膽的替代性;二是動物利用與動物福利問題。公眾極力反對歸真堂上市還為歸真堂指點了未來的發展方向,那就是尋找熊膽替代品。資料顯示,早在1983年8月,“人工熊膽”的科研項目就已正式立題,國家衛生部在1990年曾作出審批結論表示,合成的熊去氧膽酸符合藥審要求,完全可替代熊膽,而且更具優勢,不只是便宜,更重要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膽酸有效成分含量確定,雜質少。為什么熊膽替代品長期以來得不到應用和推廣呢?那就是在利益的驅使下,一直未將熊去氧膽酸這種有效成分推廣開來。據歸真堂內部人士透漏,歸真堂營業額在1—2億元。1克熊膽粉需要7—9毫升熊膽汁,就是說,1000毫升膽汁可以做約125克熊膽粉。熊膽粉分為幾個等級,最高等級的金膽,每克售價118元。而僅僅3g熊膽粉被包裝在50厘米見方的盒子里,包裝得很豪華,售價也高達400多元,利潤之大可想而之。“大部分的熊膽消費都是禮品消費,而不是藥品消費。而這些禮品消費都是建立在黑熊的痛苦之上的。”這是令公眾所不能容忍的。要知道公眾的健康是建立在熊痛苦之上的,從動物保護權利上講,難免讓人覺得不仁。活熊取膽已形成龐大的利益鏈:從養熊場到制藥企業到營銷體系,甚至涉及相關利益部門及其官員。毫無疑問,歸真堂是利益鏈上的重要環節。如果把熊膽粉無限制擴大,形成保健品、禮品,那中醫藥管理部門也會堅決反對的。目前人造熊膽確實也沒有審批出來。但有關研究有進步也是事實。
據我了解,2001年,為保護野生動物資源和保證保健食品的食用安全,衛生部已不再審批以熊膽粉和肌酸為原料生產的保健食品(衛法監發[2001]267號)。相關部門也表明了“鼓勵熊膽替代品的研發工作”的基本立場。
我從國家食藥監局資料里查到,在歸真堂目前生產的熊膽產品中,除了“熊膽粉”和“熊膽膠囊”獲得國家藥監局批號外,其他三十多種產品均未獲得熊膽藥品或含熊膽藥品批號,主要為熊膽茶、清甘茶等保健產品。不過,歸真堂還沒有一種產品獲得任何保健品批準字號。
除被指責取膽手段殘忍外,歸真堂還被質疑產品中有半數以上為保健品而非藥品,違反了相關部門關于熊膽粉不能用于保健品生產的要求。對此問題,歸真堂副總吳亞稱,歸真堂的熊膽產品分為熊膽粉、熊膽膠囊、清肝茶三大類,其中“食字”批號的清肝茶是公司的早期產品,從去年開始就沒有再生產,目前歸真堂獲取的熊膽粉全部用于藥類。當記者發問“可否舉證到底哪種疾病非熊膽粉不能治療?”這個問題時,歸真堂及所有專家也啞口無言。
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簡稱“它基金”)聯合馮驥才、韓紅、崔永元、李東生等72名社會知名人士,向中國證監會信訪辦遞交吁請信,懇請對福建歸真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申請不予支持及批準,將歸真堂上市引發的“活熊取膽”爭議,推向了又一個的高潮。
我想,有良知的大眾以“捍衛生命”的名義抵制“活熊取膽”,這已不單是一個動物保護或醫藥問題,而演化為一個社會事件。“養熊取膽”引發的爭議從抵制“歸真堂上市到要求“取締養熊業”逐步升級,看似黑熊“痛不痛”、熊膽是否可用替代的爭論,歸根到底是一個動物的保護與利用問題,從人類的道德、從生態倫理道德的角度來說,保護是為了合理科學的利用。絕對的濫用、沒有度的養熊再取膽汁是不可取的。
此次事件的發起者以愛護動物為由,以攻擊合法養殖黑熊、取用熊膽汁的國內養殖企業為切入點,聲稱最終目的是取締該行業,對國內外與藥物有關的動物利用問題實際上采取的是雙重標準。對于熊膽的使用,有專家提出,熊為人類做出了貢獻,還應盡量考慮動物的權益。盡管熊膽是用于治病救人,但治療病種應有限定,而不是無限制地用。
亞洲動物基金會中國區外部事務總監張小海曾對我說,西方國家都持“非常強烈的反對態度”,“首先,西方國家就從來沒有過養熊場,他們不相信中醫。像我們亞洲動物基金會,由英國人創辦的基金會,也是代表了來自西方的聲音,希望淘汰養熊業。”
德國和意大利是目前世界上可以人工合成熊膽的國家。國家藥監局網站披露,目前我國進口的人工合成熊膽藥只有熊去氧膽酸膠囊和牛磺熊去氧膽酸膠囊。兩者分別為德國福克藥廠和意大利貝斯迪大藥廠生產的專利藥,中文商品名分別為優思弗和滔羅特。適應癥為:膽固醇性膽結石;原發性膽汁淤積性肝硬變,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膽汁返流性胃炎等。
專家承認熊膽粉的藥用價值不可否認,科學利用人工繁育的黑熊作為中藥產業的可再生資源,通過發展養殖業獲取熊膽粉原料,有利于保障中醫藥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也是對黑熊等野生動物資源的真正保護。
歸真堂哪些方面出紕漏乃至眾人觸怒呢?我分析一是主營業務技術含量不高。創業板IPO主要是支持科技型企業成長,技術含量高低是重要指標。但無論是黑熊養殖環節,還是活熊取膽環節,抑或膽汁加工制藥環節,都很難講歸真堂主營業務具有高科技,具有別人難以復制的技術獨創性。雖然中醫藥是重要的中華傳統瑰寶,國家也大力提倡、鼓勵和支持中醫藥的發展甚至“走出去”,但方向應該說更在于草本入藥,包括藥材生產和制藥工藝,而非動物制品入藥,如果是動物制品入藥,本身就很難稱得上高科技。
其次歸真堂主營業務有違生物倫理和環保潮流。IPO管理辦法第12條明確規定,發行人應當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及環境保護政策,但活熊取膽確實有違生物倫理和環保潮流,盡管歸真堂在取膽環節進行了諸多人性化的技術改造,從有管引流升級到無管引流,甚至讓黑熊在取膽過程中幾乎沒有感覺,但不管怎樣,乃至像中國中藥協會會長房書亭所說的“感覺很舒服”也好,活熊取膽改變不了人類粗暴切開熊腹并擊穿膽囊的基本事實。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目前沒有禁止活熊取膽,更沒有像一些國家那樣推行嚴格的反虐待動物法,但動物保護無疑是不可阻遏的國際潮流。國家林業部規定,除上海市外,18個省級轄區內不再有活熊取膽的養殖場,野生動物保護部門不再批準建立活熊取膽養殖場的申請,并承諾嚴肅查處轄區內可能存在的非法養殖場。顯而易見,養熊業屬于國家正在限制乃至要逐步淘汰的產業。2001年9月,國家衛生部即發文明確規定,不再審批以熊膽粉為原料生產的保健食品。活熊取膽不符合IPO管理辦法第14條所提到的:“發行人的行業地位或發行人所處行業的經營環境已經或者將發生重大變化,并對發行人的持續盈利能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另外我不得不說,歸真堂有違規甚至違法之嫌。IPO管理辦法第26條規定:“發行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最近3年內不存在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違法行為”。包括國家衛生部和林業局在內的多個部委,曾明文限制熊膽產品生產。從歸真堂官網看到,其產品線涵蓋熊膽粉和熊膽膠囊、清甘茶等30多種,其中前兩個藥品批準文號分別為國藥準字Z10980024、國藥準字Z20054679,在藥監局網站明確可查。有關產品廣告也表述了歸真堂對熊膽的超限利用,而歸真堂熊膽粉的宣傳廣告也正暴露了熊膽粉當保健品送禮的事實。
因此,以上幾點可以說明歸真堂難以認定為高科技企業,不屬于成長型企業,乃是被限制發展的,而且經營上有違規甚至違法之嫌,基本可以判定,歸真堂在創業板IPO基本沒有希望。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公開允許“活熊取膽”的國家。事實上,歸真堂違反《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管理辦法》的三條理由中,最為集中的質疑在于涉及熊膽的國家產業政策、外部監管環境可能發生變化,或者對黑熊有立法保護,導致歸真堂不能“活熊取膽”,這會對企業的經營產生阻礙,從而降低盈利預期。但只要這些潛在風險在上市前對投資人有告知,歸真堂就可以上市,基于產業帶來的風險自己負責。
因此我的觀點是,上市是一個嚴肅的話題,需要綜合各方面的考量。目前在市場存在各種爭論,我們也希望監管層在做出決定時,既要充分考慮市場方面的因素,同時也要考慮社會影響,做出一個公正、公開、公平的決定。
歸真堂涉嫌欺詐被起訴公司稱不違規
遭遇上市風波以來,歸真堂又卷入消費者糾紛。 3月26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一位北京市民對福建歸真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訴狀。起訴狀稱,2012年3月10日,原告花費220元購得一盒歸真堂熊膽粉。但隨后發現,所購產品說明書的功能為“清熱、平肝、明目”6個字,主治“用于驚風抽搐,外治目赤腫痛、咽喉腫痛”。
原告認為,這與歸真堂網站描述“可防治肝炎、酒精肝、脂肪肝;清肝明目;清熱解毒;利膽溶石;可降壓、降脂、降火等”差異巨大。
原告已向法院提出6項訴訟請求,包括雙倍賠償購藥貨款共計440元;停止銷售所涉產品并全部刪除產品外包裝及其網站虛假違規宣傳內容;歸真堂就其產品外包裝及其網站虛假宣傳、夸大藥效的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向原告公開道歉等。
“熊膽粉”和“含熊膽成分的產品”是兩個概念,含熊膽成分的產品是可以零售的,而熊膽粉是不允許的。歸真堂的做法是違反規定?還是虛假宣傳?將是法庭審理的重點。
該案另一位代理律師對我說,這起案件顯示了政府管理在某些方面的缺失。如A部門嚴禁熊膽粉零售,B部門卻給企業頒發銷售許可證;又如,相關部門對藥品廣告的管理,在傳統公共媒體平臺,如電視、報刊等的監管較為嚴格;但是在企業“自媒體”,即企業網站、微博等宣傳平臺的監管存在疏漏。
我認為,“自媒體”也是公共宣傳平臺,就是宣傳展示給公眾看,歸真堂的所有虛假及夸大宣傳,都是出于商業推廣需求。這種在“自媒體”上的虛假宣傳,其性質跟街頭違法小廣告并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