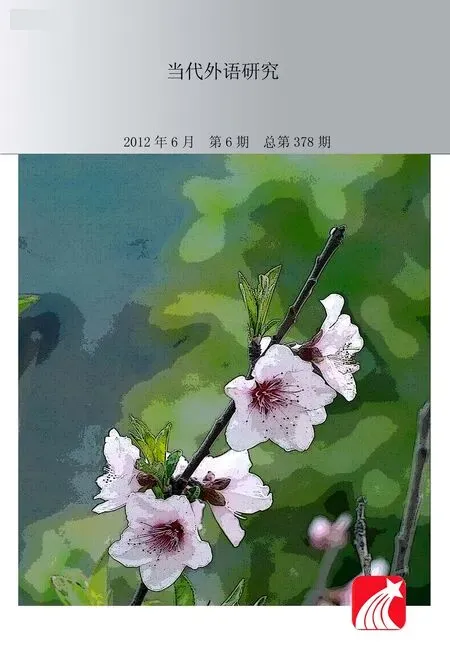構式語法視角下的離合詞
馬玉蕾 陶明忠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200240)
1.引言
離合詞匯集了漢語諸多的語法現(xiàn)象,最能體現(xiàn)漢語語法的特點和本質。然而,由兩個可合可離的音節(jié)構成的語法結構體是詞還是詞組,人們的認識并不統(tǒng)一。趙元任(1979/1968)把含有非自由語素的詞的分開使用形式稱為詞的離子化形式,并將其劃為復合詞。趙金銘(1984:20)持有同樣的觀點,認為應該把“生……氣”看作一個詞。呂叔湘(1979:503)認為,“走路、打仗、睡覺”等離合詞在詞匯上可以被認為是一個詞,而語法上則是一個短語,最好還是歸入短語。這與王力(1985/1954:10)的觀點相近。他認為,“‘說話’不是雙音詞,因為咱們可以插進一個字,如‘說大話’、‘說好話’,等等”。朱德熙(1982:13)則認為,“我們把‘理發(fā)’看成詞,把擴展以后的形式(理了個發(fā)、理不理發(fā))看成詞組”,這與陸志韋(1957:79)的觀點一致。其他的早期著述對離合詞的看法基本上是在以上三種觀點之間徘徊,爭論的焦點是,詞跟詞組的分野是以形式為標準還是以意義為標準。周上之(2006:314)從字本位出發(fā)認為離合詞就是離合雙字組,希望以此避開語素、詞、詞組之間的糾纏。本文將從構式語法的角度論述漢語離合詞的判別標準、離合詞的性質及擴展法的局限。
2.離合詞的構式觀
離合詞究竟是詞還是詞組?用什么標準來判別呢?讓我們先分析下面的幾組語法結構體:
A組:喝水、讀書、捕魚、殺雞、打人、修橋、補路
B組:理發(fā)、請客、結盟、結晶、游泳、造反、觀光
C組:拔河、砸鍋、吹牛、談天、接火、裝蒜、嘴硬
D組:壓驚、吃虧、將軍、革命、落伍、栽贓、宰客
上面的四組語法結構體都是可以擴展的。如果僅以形式(即擴展法)為標準,它們在擴展后都應該是詞組。然而它們之間卻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把它們一律看作詞組似乎有困難。A組和B組當中的語法結構體可以按照字面意義來理解。兩者的不同點是:A組中的每個語法結構體的每個語素都可以獨立成詞,組合是開放的,整個語法結構體是詞組;B組中的每個語法結構體都含有黏著語素,黏著語素不能獨立成詞,因此整個語法結構體不是詞與詞的組合。C組和D組當中的語法結構體不能按照字面意義來理解,整個語法結構體的意義并不是兩個語素獨立意義的簡單疊加,而是具有引申義,其組合是封閉的。然而C組和D組也存在著差別:C組中的每個語法結構體的每個語素單獨地看都可以成詞,D組中的每個語法結構體當中都含有不能獨自成詞的黏著語素。
詞組是詞與詞的自由組合,其整體意義可由其組成部分推知。然而,上面的分析顯示,能擴展的語法結構體并非完全是可直接按字面意義理解的“詞+詞”的自由組合。因此我們認為,在詞與詞組的劃界上,把B組、C組和D組當中的語法結構體歸入詞組會失去邏輯上的嚴謹性(即違反矛盾律:不成詞的黏著語素=詞;詞組意義≠組成部分意義之和)。因此嚴格地說,無論是合還是離,B組、C組和D組當中的語法結構體都不是詞組。本文將嘗試運用構式語法理論來解決離合詞與詞組的劃界問題。
構式語法的基本理論觀點是:
C是一個獨立的構式,當且僅當C是一個形式(Fi)和意義(Si)的對應體,而無論是形式或意義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從C這個構式的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構式推知。(Goldberg 1995:4;陸儉明2004:15)
這里所說的構式不僅包括句式,也包括語素、復合詞、固定語等。構式在認知上具有完形性,其組成部分互相依賴且不可替代(若發(fā)生替代,則意義發(fā)生改變,或者構式不成立),對構式的組成部分的解釋必須以整個構式為依據(jù)。這些認識對我們解決離合詞與詞組的劃界問題將起到關鍵作用。
本文以“復合詞由語素構成”為語法前提,以構式語法為理論視角,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如下的判別離合詞之所以為詞的標準:
(1) 如果兩個可合可離的單音節(jié)語素①組合起來形成的整體意義不能從這兩個語素的字面意義中推論得出,那么這兩個語素形成的語法結構體在詞這一級構式層次上形成完形結構,是離合詞。比如“拔河”、“吃虧”等。
(2) 雖然兩個可合可離的單音節(jié)語素組合起來形成的整體意義能夠從這兩個語素的字面意義中推論得出,但如果其中的一個語素是黏著的,或兩個語素都是黏著的,那么這兩個語素形成的語法結構體在詞這一級構式層次上形成完形結構,是離合詞。比如,“理發(fā)”、“結盟”、“請客”當中的“發(fā)”、“盟”、“客”是黏著語素,“鼓掌”當中的“鼓”和“掌”是黏著語素,它們都具有依賴性,因此“理發(fā)”、“結盟”、“請客”、“鼓掌”都是離合詞。相對于詞這一級的完形結構而言,黏著語素是非完形的。
(3) 如果兩個可合可離的單音節(jié)語素組合起來形成的整體意義能夠從這兩個語素的字面意義中推論得出,并且這兩個語素都是自由的,那么這兩個語素形成的語法結構體不在詞這一級構式層次上形成完形結構,不是離合詞,而是詞組。比如“喝水”、“讀書”、“捕魚”等。相對于詞這一級的完形結構而言,詞組是雙完形結構的。
標準(1)和標準(2)是基本標準,足以判斷一個語法結構體是不是離合詞,標準(3)補充說明標準(2),明確地把詞組排除在離合詞之外。
3.離合詞的完形性質
“理發(fā)”中的“發(fā)”是黏著語素。根據(jù)判斷離合詞的第2條標準,無論是合是離,“理發(fā)”是詞,不是詞組。我們把“理發(fā)”看作離合詞的合并式,把“理了個發(fā)”中的“理……發(fā)”看作“理發(fā)”的分離式,把“發(fā)已經理了”中的“發(fā)……理”看作“理發(fā)”的特殊分離式,即換序式。“理……發(fā)”和“發(fā)……理”當中的兩個語素在形式上是分開的,而我們仍然稱它為詞,這樣是不是不顧形式標準呢?非也。趙金銘(1984:20)曾指出,“在現(xiàn)代漢語中,若從語法分析上看,也并不是所有的直接成分都是相鄰接的。”這種觀察符合漢語的實際情況。為了準確說明“理……發(fā)”和“發(fā)……理”在形式上也是詞,本文在此特別提出“鄰接黏著”和“非鄰接黏著”的概念。當離合詞的兩個語素中間沒有其他成分阻隔時,黏著語素與另一個語素是鄰接黏著的(該語素也可能是黏著的);當離合詞的兩個語素之間隔著其他成分時,黏著語素與另一個語素是非鄰接黏著的。
在漢語中,非鄰接黏著的現(xiàn)象并不局限于離合詞,也表現(xiàn)在其他方面。比如,介詞一般是不能單獨使用的,是黏著的。然而介詞并不是永遠都與后面的成分毗鄰。請看下例:
(1) 他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孩子們身上。
例(1)顯示,緊跟在介詞“在”后面的并不是它的賓語,而是體助詞“了”。“了”把介詞及其賓語隔離開了,但這并不妨礙介詞與其賓語的句法關系。由于“了”的存在,介詞“在”與其賓語是非鄰接黏著的。同時,“了”也是黏著語素,與前面的動詞“放”形成非鄰接黏著。與離合詞中的黏著語素不同的是,這里的“在”和“了”不是某一個詞的組成成分,因此它們是具有黏著性的虛詞②。
建立非鄰接黏著的概念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使我們放棄下面的引起頗多爭議的假設,即黏著語素必須上升為詞才能充當句子的核心成分。問題的關鍵在于,誰也說不清楚黏著語素是怎么單憑自身的力量上升為詞的。
明確離合詞中的黏著語素在分離后仍是黏著之后,接下來的問題是,黏著語素可以直接充當句子的核心成分嗎?就這個問題,程雨民(2001a,2001b)持十分肯定的觀點,其文章的題目就是《漢語以語素為基礎造句》,并據(jù)此建立了字基語法(與字本位語法不同)。我們也認為,漢語的許多事實都表明,雖然說黏著語素獨立活動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但黏著語素如果獨立運用,就可以直接充當句子的核心成分,我們不必說它們是詞。例如:
(2) 新學生對王老師鞠了一個躬。
(3) 因為缺少淡水,有的戰(zhàn)士曾經11個月沒有洗過一次澡。
例(2)和例(3)中的“鞠”、“躬”、“澡”都是黏著語素,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jù)說它們是詞,然而我們卻有把握說“鞠”是述語的核心成分,“躬”和“澡”是賓語的核心成分。在離合詞處于分離狀態(tài)的時候,黏著語素不能獨立成詞,也不必成詞,它是離合詞的一個組成成分,同時也是所在句子的一個句法成分。
離合詞的分離形式不是出現(xiàn)在靜態(tài)的詞法層面上,而是出現(xiàn)在動態(tài)的句子中,因此應結合它們的句法表現(xiàn)來討論。如果只在構詞的層面上討論,我們對離合詞的本質不會看得很清楚。趙淑華、張寶林(1996:44)認為,離合詞是“一種特殊的、可以具有兩種不同形態(tài)的詞”。顏紅菊(2004:96)認為,“語言中的詞匯單位是抽象的、概括的,以各種具體形式存在于言語中,包括凝固形式和分離形式。表面形式被分離的詞匯單位是語言中的詞匯單位在言語中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之一,是一種變異形式。”本文則認為,離合詞在句子中表現(xiàn)出來的合并形式和分離形式都是離合詞詞位(lexeme)在句子中的語法變體(variants)③。如“理發(fā)”在句子中的語法變體為:

趙淑華、張寶林(1996:44)和顏紅菊(2004:96)都認為,合并形式是詞的原式,分離形式是詞的變式。我們則不區(qū)分離合詞的“原式”與“變式”,認為離合詞的合并形式和分離形式都是詞位在句子中的語法變體。“原式”與“變式”的區(qū)別似乎有概率統(tǒng)計的意味,然而概率統(tǒng)計并不總能表現(xiàn)實際情況。比如,我們在實際生活中聽到的“理發(fā)”的分離形式不一定比合并形式少,說不定還多些;而“將軍”一詞在棋局之外大多用其分離形式,我們沒法斷言哪種情況是“原式”,哪種情況是“變式”。
詞在句子中不同的存在狀態(tài)(即變體)表現(xiàn)了詞在運用中的動態(tài)性。處于分離狀態(tài)的離合詞的兩個語素并不是彼此獨存的,它們是前后呼應的,是非鄰接黏著的,是跨越隔離成分相互結合起來成詞的。這對兩個語素都是所謂自由語素的離合詞來說同樣適用。比如,我們說“拔”和“河”在“拔河”這個離合詞中都是所謂自由語素,意思不過是說,“拔”和“河”這兩個語素在有些句子中都可以單字成詞。但是,它們一旦結合起來就有了專門化的意義,表達的是一個不能從字面意義推知的完整的概念,是認知上的完形結構,其整體的意義不是部分意義的簡單相加,而是形成了封閉的構式,性質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同樣,在離合詞“將軍”當中,“將”和“軍”也不再是自由的了,它的分離形式“將……軍”在“他將了我一軍”這句話當中是相互結合起來成詞的,不能各自獨立成詞。這里的“將”不再是尋常意義的“將”,這里的“軍”也不再是尋常意義的“軍”,我們甚至說不出這里的“將”和“軍”分別是什么意思。在這里,“將……軍”的意義只能整體理解,無法拆開來分析。我們認為,如果一個離合詞的整體意義是引申的、隱喻的或轉喻的,那么這個離合詞中的語素(嚴格地說,是音節(jié))就都是黏著的,完全失去了本義,失去了自由,不能獨立成詞。
有的離合詞當中的語素在擴展后似乎轉化成了動量詞,然而這不是全部事實,不能構成“黏著語素不成詞”這一觀點的反例。比如“見過一面”是“見面”的擴展式,其中的“一面”是表動量的,語素“面”似乎轉化成了臨時動量詞。然而,由離合詞中的一個語素來臨時擔任動量詞,這純屬巧合。“見過一面”中的“面”實際上是一身兼兩職的,它既是“一面”中的動量詞,又是“見……面”中的一個語素。其“兼職”的過程是:
(4) 見面→見過一回面→見過一(回)面→見過一面
在“見面”的擴展式“見過一回面”當中,“回”是常用的動量詞,“面”是潛在的臨時動量詞,在經濟原則的作用下,動量詞“回”可省略④。“回”省略之后,“面”就接收了“回”的句法功能,臨時擔當了表動量的句法角色,但它本來的作為“見……面”中的一個語素的身份還在。這個例子再一次證明了漢語句法構造的經濟性和精巧性。下面是兩個類似的例子:
(5) a.插嘴→插了一句嘴→插了一嘴
b.打仗→打過一回仗→打過一仗
這種擴展方式雖精巧,但不可類推。下列離合詞中的后一個語素都不能用作臨時動量詞,所以動量詞“回”和“次”不可省略:
(6) a.跳傘→跳過一回傘→*跳過一傘
b.請客→請過一回客→*請過一客
c.游泳→游了一次泳→*游了一泳
在本質上,5a、5b中的“嘴”、“仗”在“插了一嘴”、“打過一仗”當中還仍然是相應的離合詞的語素,它們可以臨時表達動量,但這并不能改變它們是離合詞的一個語素的事實。例6中的“傘”、“客”、“泳”只是相應的離合詞的語素,不能做臨時動量詞。
吳道勤、李忠初(2001:49)指出,“離合詞的擴展,只不過是語素與語素之間的擴展,是詞內部的一種特殊的‘句法現(xiàn)象’。”明確地講,離合詞的擴展是在句子層面上對詞進行的句法拆分,在擴展之后,構成離合詞的語素仍然保持原來的身份不變。
離合詞的擴展呈現(xiàn)兩個互有關聯(lián)的特點,一個是句法形式操作的自治性,一個是擴展成分語義指向的不確定性。句法形式操作的自治性指的是,離合詞的擴展在形式上的操作可以不顧及局部意義是否能搭配得起來。比如,“你得請我的客”中的“我的”在形式上是“客”的擴展定語,但在語義上并不是“客”的所有者。因此,說“我的”是“客”的擴展成分,這在形式上是成立的,但在語義上并不成立,所以有些學者(如徐杰2001:6)稱這類關系中的定語為偽定語。
其實,離合詞不為漢語所獨有,德語中的可分動詞與漢語的離合詞在句子中的表現(xiàn)是類似的。德語的可分動詞是由“可分前綴+動素”構成的,可分前綴重讀,具有區(qū)別意義的作用。舉例來說,aufstehen是一個可分動詞,其中的auf是可分前綴,stehen是動素。如果句子是完成時態(tài)的,或者句子中有情態(tài)動詞,可分前綴與動素合并在一起。而在現(xiàn)在時、過去時和命令式的句子里,可分前綴放在句末,與動素一起形成框形結構。下面的句子是現(xiàn)在時的:
(7) Sie stehen um 6 Uhr auf.
他們 站 在六點鐘 起來。
他們六點鐘起床。
“stehen...auf”合到一起是“起床”的意思,不能分開來理解,這里的“stehen”和“auf”都失去了單獨成詞的資格,是彼此黏著的。
陸志韋(1957:92)說,“從動賓結構的一般語法作用來看,這樣的詞(指漢語的離合詞)也不宜于看作像德語的分離動詞。”我們不能完全同意陸先生的說法。陸先生的意思是,漢語的離合詞是動賓結構的,而德語的可分動詞不是動賓結構的。但這無法否認兩者都具有可合可分的句法表現(xiàn),它們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我們可統(tǒng)一稱之為框式動詞。框式動詞在分離使用時形成框形結構,框內可裝進需要表達的語義成分或語法成分。值得一提的是,在語音上,漢語的離合詞和德語的可分動詞的兩個語素在分開時都是重讀的,以強調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Wells(1963/1947)曾對非連續(xù)成分提出過以下的限制性條件,即如果在某些環(huán)境里,跟非連續(xù)序列相應的連續(xù)序列作為一個成分出現(xiàn)在結構里,而這個結構在語義上跟出現(xiàn)某個非連續(xù)序列的結構是一致的,那么這個非連續(xù)序列是一個成分。該限制性條件強調的是,語義上的一致性可以作為判斷直接成分的標準,不必顧及非連續(xù)序列當中插入的成分。
4.擴展法的局限
在談到離合詞時,馮勝利(2001:163,167)討論了“詞匯的完整性原則”,即短語(句法)規(guī)則不能影響(或適用)到詞匯內部的任何部分,認為這個原則是詞匯研究的必要條件,并據(jù)此把“關心”看作詞,把“關……心”看作詞組。“詞匯的完整性原則”正是擴展法的來源。在結構主義的視角下,“詞匯的完整性原則”指的是構成一個詞的語素在形式上應該是鄰接黏著的,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在句子中拆卸組裝。但是以印歐語為語料總結出的這個原則實際上并未完全反映出印歐語的全貌。正如我們在上面第2節(jié)中所討論的,德語的可分動詞在形式上并不遵循這個原則。
在構式語法的視角下,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詞匯的完整性原則”。“詞匯的完整性原則”指的是:(1)作為詞,其構成語素在形式上可以是鄰接黏著的,也可以是非鄰接黏著的;(2)有些合成詞的整體意義不可由組成部分來解說。一個語法結構體只要能滿足上面的任何一條原則,就應該是詞。因此,“詞匯的完整性原則”應該重新解讀為詞在認知上具有完形性。很明顯,“關……心”中的“關”和“心”只在整體中呈現(xiàn)意義,而沒有各自獨立的意義。說“關”和“心”分別是詞,有點類似于盲人摸象。
擴展法一直被用作判斷詞與詞組的方法,因此關于離合詞是詞還是詞組的爭論焦點,就在于擴展法是否為確定詞與詞組的有效方法。我們認為,擴展法的應用有一定的范圍,超出這個范圍就失去效用。其最明顯的缺陷是把離合詞分離后的黏著語素作為詞來看待。現(xiàn)代漢語中構成離合詞的黏著語素在古代漢語中曾經具有詞的身份,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現(xiàn)代漢語的黏著語素在離合詞的分離形式中具有單獨成詞的能力。把離合詞分離后的黏著語素看作詞,是自相矛盾的。不會把構成離合詞的黏著語素當作詞收入詞典就是最好的證明。另一方面,從具有引申義的離合詞中分離出來的成分在句子中并沒有獲得詞所應該有的獨立的意義,其自身也并不具有在整體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引申義。比如,“他將了我一軍”是“他給我出了一道難題”之義,但我們無法把“將……軍”分開來理解,說“將”是“出”的意思,“軍”是“難題”的意思。
因此,在區(qū)分詞與詞組時,擴展法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任何原理、規(guī)律、規(guī)則、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擴展法也不例外。擴展法可以用來對付除了離合詞和固定語(包括成語和慣用語)以外的語法結構體,用來對付離合詞和固定語,就會造成誤判。離合詞和固定語在句子中都是以其整體作為詞一級的單位來使用的(兩者的主要區(qū)別是音節(jié)數(shù)不同)。
5.結語
本文運用構式語法理論討論了離合詞的判別標準、離合詞的完形性質和擴展法的局限,從詞這一級構式的完形性出發(fā)提出了“鄰接黏著”和“非鄰接黏著”的概念。離合詞的合并形式和分離形式都是靜態(tài)的詞位在動態(tài)的句子中的語法變體。被拆開的兩個語素前后呼應,形成了一個可容納更多信息的句法框,因此我們可以稱離合詞為漢語中的框式動詞。
把離合詞和詞組分清楚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更有信息處理和對外漢語教學上的應用價值。在漢-外機器翻譯中,機器可以根據(jù)離合詞處理規(guī)則,把分離開來的單音節(jié)語素合并起來作為一個詞來翻譯。舍此,譯文必出錯。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對離合詞的分合情況做統(tǒng)一處理,可以消除理論上的困惑,使留學生們正確理解句子的結構與意義。
附注:
① 馮勝利(2001:161-74)已證明,離合詞首先必得是雙音節(jié)的韻律詞。在句子中可合可離的3個或3個以上音節(jié)的構式算作習語。
② 呂叔湘(1984/1962:377)說,“虛詞的取得詞的資格是因為它不是另一個詞的一部分”。
③ 在現(xiàn)代漢語中,詞位的語法變體還體現(xiàn)為詞的重疊式和不重疊式(劉叔新2005/1990:54-5)。比如,干凈:干凈/干干凈凈,嘗:嘗/嘗嘗,家:家/家家。
④ 當然也可以保留“回”而省略“面”,成為“見過一回”。“面”可以省略,是因為“面”在“見面”當中只是個襯字,沒有給“見”增加任何內容。
Goldberg, Adele E.1995.Constructions:AConstructionGrammarApproachtoArgumentStructure[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lls, Rulon S.1963/1947.直接成分(趙世開譯)[J].語言學資料(6):29-53.
程雨民.2001a.漢語以語素為基礎造句(上)[J].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1):35-48.
程雨民.2001b.漢語以語素為基礎造句(下)[J].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29-36.
馮勝利.2001.論漢語“詞”的多維性[J].當代語言學(3):161-74.
劉叔新.2005/1990.漢語描寫詞匯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
陸儉明.2004.詞語句法、語義的多功能性:對“構式語法”理論的解釋[J].外國語(2):15-20.
陸志韋.1957.漢語構詞法[M].北京:科學出版社.
呂叔湘.1984/1962.說“自由”和“黏著”[A].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C].北京:商務印書館.370-84.
呂叔湘.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A].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C].北京:商務印書館.481-571.
王力.1985/1954.中國現(xiàn)代語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
吳道勤、李忠初.2001.“離合詞”的語法性質及其界定原則[J].湘潭工學院學報3(3):47-50.
徐杰.2001.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xiàn)象[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顏紅菊.2004.詞匯單位的動態(tài)性——漢語詞匯單位的離合現(xiàn)象分析[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26(5):96-98.
趙金銘.1984.能擴展的“V+N”格式的討論[J].語法教學與研究(2):4-23.
趙淑華、張寶林.1996.離合詞的確定與離合詞的性質[J].語言教學與研究(1):40-51.
趙元任.1979/1968.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
周上之.2006.漢語離合詞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