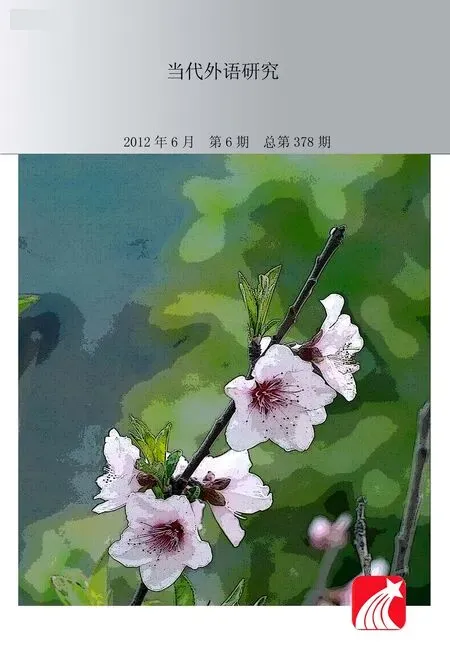基于普遍認知能力的網絡模型及其解釋力
——兼比較圖式網絡和概念網絡模型
呂晶晶 唐樹華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對外貿易學院)
1.引言
認知語法將語言看作復雜的圖式網絡(schematic network),強調在普遍認知能力參與下的具體與抽象、語言知識與百科知識、語義與語用之間的連續體關系,為形式語言學難以解釋的語言現象提供了新視角(束定芳、唐樹華2008)。但近兩年網絡節點隱射的語言離散性頻惹爭議,Allwood(2003)、Zlatev(2003)等分別提出了“連續意義潛式”或“用法潛式”來代替圖式節點網絡。Langacker(2006)一方面認可這些提法對語言連續性的凸顯;另一方面也指出“場”隱喻的均一性不能體現語言范疇典型性和邊緣性的差異。因此提出用“山脈”(mountain range)代替“網絡”隱喻。
山脈隱喻雖能在凸顯語言事實連續性的同時,體現各范疇典型與邊緣的不同地位,但圖式網絡是否就此被輕易取代?答案是否定的。在圖式網絡遭質疑時,作為認知語言學發展之一的詞項語法①以概念網絡(Conceptual Network)作為自己新動向的根本,將共時語言學的各個方面,從語音、詞態、語義到句法的整個語言系統都歸于概念網絡之中。這兩種主要的認知網絡模型要旨何在?它們有何異同?能否為語言現象提供充分的解釋?通過比較認知語法圖式網絡與詞項語法概念網絡的異同,分析其對多義、不規則動詞變化、隱喻和轉喻等語言現象的解釋性,可以得到問題的答案。
2.圖式網絡
網絡模型是認知語法的三個理論基礎之一,其中提出的圖式網絡概念新意不在于概念本身,而在于它的應用帶來的理論統一性(劉宇紅2004)。意向圖式、隱喻、理想認知模型等都可以納入圖式的框架之中,圖式網絡也是其中之一(Tuggy 2007)。Langacker(1990:35)是這樣定義圖式網絡的,“頻繁使用的詞素和詞項具有大量相互聯系的意義,這些意義形成一個網絡,即圖式網絡”。該定義的主要貢獻在于:詞素等不同語言單位的頻繁使用會帶來不同語言模式的圖式化和語言規則的抽象化,它們的意義是通過網絡節點范疇以類推、歸納等方式進行激活、繼承和擴散的。圖式網絡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它從具體到抽象,基于使用的語言觀和它對人類一般認知能力在語言使用和形成過程中作用的凸顯,包括:凝固化能力或自動化能力、抽象能力、范疇化能力、組合能力和符號化能力。
圖1中,實線箭頭表示上層圖式與下層實例之間的完全制約關系,虛線表示以原型為基礎的推斷,方框邊線的粗細表示該意義的固化和凸顯程度。具體解讀為:對于ring的名詞用法而言,其最典型的意義是“圓狀、環狀物體”,包含常見的“戒指、耳環、鑰匙環等”,由此通過隱喻機制拓展出“圓圈”和“馬戲團的圓形競技場”等“無形環狀物”的用法。所有用法共同抽象出上層范疇“圓狀、環狀”(含抽象與非抽象實體)。可見,其中詞的規約價值不能縮減為一個單一結構,而是激活一個相關的認知域,域中的聯系有系統的規律可循,并受到該詞在使用者心中的固化度和認知凸顯度的影響。

圖1 名詞ring的部分網絡
3.概念網絡處理過程及其心理現實性
概念網絡是2007年詞項語法的最新進展《語言網絡——新詞項語法》一書中提出的核心概念,該著作完全圍繞概念網絡這一根本對各級語言現象進行了分析和解釋。在概念網絡中,默認承接和擴散激活是兩個關鍵的過程。以詞為單位的節點通過“是”關系(范疇化關系)鏈接,節點之間概念距離的遠近導致相應節點被目標詞激活的程度相異;下層節點從上層節點繼承特征,當遇沖突時,則跨越上層特征被直接激活,例如不規則動詞就是跨越動詞變化規則被直接激活的。圖2以動詞過去式的形成為例說明概念網絡的建構:

圖2 詞項語法概念網絡例示
圖2中三角形及豎線表示從屬范疇化關系,箭頭表示的是三者之間的名稱關系,或稱為論元(argument)論值(value)關系,簡言之,就是“a的e是c,b的f是d;d的g仍然是d”。具體來說,動詞的過去式是“詞根+后綴”,pass是個動詞,繼承動詞的特征,它的過去式是passed。這種規則形式是作為“類型”來默認承接的,無需在記憶中儲存。后文將通過概念網絡對不規則動詞的提取作進一步的解釋。
概念網絡模型強調接觸頻率和新近程度導致的心理距離的差異,并進而帶來對目標成分可及性的影響。在話語錯誤中,目標詞總是被網絡中另一個在語音、語義或形式上鄰近的詞替代,如例(1)中的口誤就是因為waste與term被形式和語音相近的taste和worm替代而產生的:
(1) a.Youhavetastedthewholeworm.
b.You have wasted the whole term.
語義啟動試驗也證明了語言使用過程中概念距離對激活程度的影響。結果顯示,要讓被試判斷ink是否是一個合法詞,給出pen會比king更能加快判斷的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有時新概念激活的相關節點不止一個,會出現多層默認繼承現象,從而產生沖突并導致學習者的錯誤。如I amn’t就是從aren’t,isn’t等縮略詞的構成規則以及am的特征多層繼承的結果,最終的結果是沖突一方的讓步。
4.作為普遍認知能力的語言能力——兩種認知網絡的相通之處及各自特點
圖式網絡和概念網絡將人類普遍認知能力融入語言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典型的認知模型。二者均強調語言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普遍認知能力的參與,語言事實是具有不同抽象程度的連續體,尤其強調低層圖式和人類認知能力的作用。Hudson(2007:ⅹ)指出“語言能力與其他的認知能力是相似的”。在Hudson與筆者的郵件中,他指出“詞項語法與認知語法的主要共同點在于‘將語言能力作為普遍認知能力’,這一點構成了認知語言學的基礎”。
舉例來說,詞項語法將默認承接作為其范疇化關系中的基本邏輯,是日常推理的基礎。默認承接關系預設了人的范疇化能力和根據常規圖式演繹推斷的能力。Langacker相應地將語言現象看作復雜范疇,范疇化能力就是人的普遍認知能力在語言處理過程中的使用。二者都支持認知原型觀。原型和拓展是Langacker圖式網絡中與抽象化和例示共存的兩大基本關系,原型模型被看作是包含于圖式網絡的特例。Hudson同樣承認原型在范疇關系中的作用,認為好的范疇成員承接所有特征;中間成員繼承部分特征;邊緣成員跨越太多特征以至于其成員身份倍受爭議(Hudson 1990:45;Jakendoff 2002:185,轉引自Hudson 2007)。
另外,基于使用的語言觀也是網絡模型的基礎,即不把語言看作自上而下由規則推導的自主生成模塊,而是受到人類社會、文化、心理經驗活動理據支持的事實——規則連續體。強調我們的語言常規來源于自下而上對語言事實的歸納,語言知識是無數次與具體語言個例“遭遇”的結果。Hudson提出的默認承接和Langacker提出的完全制約,均最終依賴于語言事實和語言細節的確認。某語言結構的使用頻率和新近程度直接影響了其可及性和固化程度,隨著固化程度的增加,會形成新的圖式和常規,從而改變網絡的結構。
概念網絡和圖式網絡有很多共通之處,但是對于激活過程的處理,兩種模型卻有各自的特點。圖式網絡認為激活點的選擇是認知凸顯度和與目標范疇重疊度這兩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使用事件會激活內容、結構上相似的概念化單位,在其他條件等同的情況下,具體的結構或者低層次的圖式更易激活,因為與高層圖式相比,具體細節能提供更多可能的重疊。但另一方面,高層圖式如認知凸顯度足夠高則可能作為規律強加執行,從而贏得競爭。概念網絡用概念距離來解釋激活點的選擇,即離激活點概念距離近的鏈接更易被激活。并強調關于目標結構的細節事實和它的距離要近于該目標結構與上層圖式的距離,因此我們判斷“金絲雀會飛”所花的時間要長于判斷“金絲雀會唱歌”花的時間,因為“會唱歌”是關于金絲雀的事實,而“會飛”是從上層概念“鳥”繼承而來的特征。
圖式網絡用認知凸顯度和重疊度(很大程度上是相似度)來解釋決定激活點選擇的因素,比概念網絡用概念距離和關于目標結構的“事實”的提法更具有說服力。因為后者會帶來進一步的問題,即如何區分上級圖式和目標事實,并可能導致把不可預測的特征都歸于事實,從而使“事實”成為不規則現象的避難所。概念網絡關于默認承接和概念距離的提法能夠直觀地呈現網絡節點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比圖式網絡的重疊度更易接受和理解。如果說Langacker的“完全制約”和“部分制約”直觀呈現了節點之間的關系,Hudson的觀點則補充了節點之間關系的距離。
5.網絡模型的應用價值和解釋力
概念網絡和圖式網絡能應用于語言習得、語義分析、隱喻、轉喻研究等各個領域,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二者雖同為認知模型,但因對人類認知能力凸顯的層面和細節不同,在具體應用中各有所長。前者對于不規則動詞的習得、語言的多義性等語言現象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對于隱喻、轉喻網絡的構成和區分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5.1 對于不規則動詞變化的解釋
概念網絡模型中被激活的特征往往是所需概念路徑最短的對象,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不規則動詞的記憶提取要快于規則動詞。我們以動詞go的過去式變化來說明,見圖3。
動詞的形態變化以“詞根”(stem)和“整體”(whole)為基礎,詞匯的“詞根”從詞項中繼承,而“整體”是該詞曲折變化完成后的詞形。規則動詞的提取首先要承接其上級節點“動詞”的特征,通過詞根加上詞綴然后形成整體,這種形成過程帶來的整體詞形作為一種類型標記不會被儲存于記憶中;而在具體使用中遇到的不規則動詞則被作為個例標記的整體直接在記憶中儲存。可見后者與詞根建立了更加直接的聯系和更短的概念距離,從而較之于規則動詞的曲折變化形式需要較短的提取時間。

圖3 動詞曲折變化的概念距離
5.2 對多義現象的解釋力
多義與同形異義的區分一直是詞匯語義學的研究話題,也是詞典編撰者需要面對的實際問題。多義詞如break既可以指“打破玻璃”,也可以指“打破記錄”;同形異義詞如“bank”(河流)和“bank”(銀行)之間被認為幾乎沒有聯系。這兩個例子清晰地展示了意義之間距離遠近、關系疏密的兩個極端。但是,其實很多情況下意義之間的聯系是介于兩個極點之間的,比如dry用于修飾“wine”(酒)和“soil”(土壤)的時候,或者cycle指“bicycle”(自行車)和“abstract repetition”(循環)時的情況。
對于這些問題,傳統理論強調多義和同形異義的嚴格區分,并提出了一些測試標準,但這些標準卻總是屢遭困境。如根據其中一條標準,即如果兩個論元不能同時并列連接某個謂語,那么該謂語動詞就是多義的,因此例(2)中run就有兩個含義:(1)動物、人等的奔跑;(2)河水的流淌。
(2) a.Tom and his dog are both running.
b.Tom and the water are both running.
但事實上,如果在b句中加入背景信息,也可以成為可接受的句子,見下句:
c.It is a quiet afternoon; everything is silent in the woods; only the water and I are running.
圖式網絡模型則可以為此類現象提供更充分的解釋。在該網絡自下而上的描述中,多義被看作是一種正常的語言現象。無論語言使用的背景是結構的、搭配的、還是語用的,都毫無例外要影響語音語義符號結構的識解,從而導致語義變體的出現;當多個變體被逐漸固化成為相互聯系的語言規約單位時,多義就形成了。同形異義是相關度漸變過程的終點,只依靠共同的語音實現互相聯系,因此是極度受限和退化的多義形式。
概念網絡模型觀持有相似的立場,認為意義之間的聯系沒有是或非的標準,只有程度的差異,概念距離的遠近構成一個連續體。假設在break的兩種意義之間存在一個單位的距離,而在bank(河流)和bank(銀行)之間存在十個單位的距離,那么dry的兩種意義之間的距離則居中。
可見,圖式網絡和概念網絡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同樣的立場,即多義與同形異義是一軸的兩個極點,意義聯系的緊密只是程度的差異,并非絕對二分。正如Langacker(2006:139)所提倡的那樣,“多義詞的不同意義形成一個連續體,如astounded到底是作為一個靜態過去分詞還是作為一個形容詞來對待取決于它與動詞astound的關系緊密程度”。要對意義進行描述,實際的問題不在于要區分多義和同形異義而在于充分準確地描繪語義網絡的特征(Langacker 1987)。Smith(2002)就基于圖式網絡的基本思想以及意義延伸的輻射范疇模式(Lakoff 1987),建立了德語虛詞es基于原型拓展的多義網絡。國內目前借鑒意向圖式、隱喻、轉喻等認知機制對多義的研究很多。這些研究多數提到了語義網絡、知識網絡等,并將其作為多義建構的基礎(如黃月華、白解紅2006;廖光榮2005),但均未對語義網絡的延伸和運作、細節等進行詳述。陳偉(2006)從理論層面探討了基于語義網絡的多維釋義新范式,而涉及具體語言現象的操作層面的研究尚有可為。
5.3 隱喻、轉喻網絡
網絡模型還可用于隱喻、轉喻的識別、區分。隱喻涉及從書面意義到隱喻義的拓展,比如“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貓出了袋子)被拓展到“information out of concealment”(秘密出了隱藏之處)。在隱喻網絡中,可以在字面意義和隱喻意義上抽象出上層圖式,如圖4中“subject out of concealment”(抽象或具體實物暴露)。

圖4 “cat out of bag”隱喻網絡示例
不同的是,在轉喻網絡中,本體和喻體卻沒有共同的上層圖式,如圖5所示,dish可與plate近義,指盛食物的器具,也能夠轉指所盛的食物。但二者卻不能抽象出一個共同的上層圖式如“碟子或食物”。
隱喻和轉喻既有不同,也有交叉、過渡和重疊,如圖5中dish又拓展出“迷人的女孩、女人”之意。認知語言學發展的這30年,也是隱喻轉喻研究迅速發展的30年。“沒有隱喻研究,很難想象當今認知語言學的發展。沒有對隱喻的探索,這個語言學分支的發展歷程也許要緩慢很多。”(Hamilton 2004:104),這一點在我國的認知語言學研究領域尤為明顯。我們統計了我國幾種主要的語言類核心刊物20年來發表的認知語言學論文,其中隱喻、轉喻研究的數量遙遙領先——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圖5 “dish”的轉喻網絡示例
隱喻、轉喻網絡一方面為隱喻、轉喻作為重要的認知機制對意義進行的衍生和引申過程提供了有效的呈現工具,另一方面,也為隱喻、轉喻的識別、區分和交叉、重疊等聯系提供了可視化的呈現工具和有效的解釋。
6.結語
Hudson(2001:50-51)指出,只有網絡能夠作為擴散激活的數據庫,由此我們認為網絡模型決非一個符號問題。另外語義啟動等實驗也為網絡的心理真實性提供了證據。同時,詞項語法和認知語法之間的共同點卻完全是出自各自獨立的發展,這一點本身是最令人鼓舞的,因為這說明這些理論是事實驅動而非個人歷史背景所致。不僅如此,構式語法理論也認為,“構式是形式與意義的結合體,有關語言的所有的知識可用構式的網絡來建構,并以原型構式為基礎形成‘家族相似性’構式”(嚴辰松2006)。林杏光(1999)也認為要真正解決漢語詞類的處理問題,需要依靠概念層次網絡理論,網絡模型能抓住漢語以詞義組合方式來實現形態變化的特點,繞過詞性等表層現象,直接進入語義層面,通過概念關聯來探求它的句法功能,從而通過概念激活方式徹底解決了漢語“詞無定義、類無定職”的困擾。
認知網絡觀能夠彌補傳統范疇觀只注重范疇成員和上級圖式之間完全吻合或毫不吻合情況的缺點,增加對范疇成員漸進性拓展的關注。同時,范疇成員也受到激活點的新近程度、使用頻率、聯系緊密程度等影響而呈現出動態性。目前,網絡模型在詞匯、詞類研究方面貢獻最為突出,如張紹全(2010)利用可視化的詞匯多義網絡模型對學生的多義詞習得進行了實證研究,張曉東(2003)分析了網絡模型對英語詞匯習得的啟示,林杏光(1999)指出了網絡模型對漢語詞類處理問題的解釋力等。
網絡模型有它本身的局限性,不能指望連接主義的神經網絡會給語言學帶來一副萬能的靈丹妙藥(袁毓林1998:57)。具體語言使用帶來的不同網絡激活點的選擇,概念激活的規律及限制條件,隱喻、轉喻網絡的建立及其認知機制,網絡形成的任意性與客觀性等都是后續研究值得探索的課題。
附注:
① Hudson(2001:50)指出“雖然認知語言學還只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但是其中三種理論能夠對語言結構作出較好的解釋,那就是認知語法、構式語法和詞項語法”。
Allwood, J.2003.Meaning potentials and context: Some consequences for the analysis of variation in meaning [A].In C.Hubert, R.Dirven & J.R.Taylor (eds.).CognitiveApproachestoLexicalSemantics[C].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29-65.
Hamilton, C.A.2004.The review onMetaphorinCognitiveLinguistics[J].CognitiveLinguistics15(1): 104-12.
Hudson, R.2001.Language as a cognitive network [A].In Hanne Gram Simonsen & Rolf Theil Endresen (eds.).ACognitiveApproachtotheVerb:MorphologicalandConstructionalPerspectives[C].Berlin: Mouton de Gruyter.49-72.
Hudson, R.2007.WordGrammar[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1987.Women,Fire,andDangerousThings:WhatCategoriesRevealabouttheMind[M].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acker, R.W.1987.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vol.1,TheoreticalPrerequisite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W.1990.Concept,ImageandSymbol:TheCognitiveBasisofGrammar[M].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mith, M.B.2002.The polysemy of Germanes, iconicity and the notion of conceptual distance [J].CognitiveLinguistics13(1): 107-51.
Tuggy, David.2007.Schematicity [A].In Geeraerts Dirk & Hubert Cuyckens (eds.).TheOxfordHandbookofCognitiveLinguistics[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82-116.
Zlatev, J.2003.Polysemy or generality? [A].In C.Hubert, R.Dirven & J.R.Taylor (eds.).CognitiveApproachestoLexicalSemantics[C].Berlin/NewYork: Mouton de Gruyter.447-94.
陳偉.2006.多維釋義理論學理探析[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1):69-73.
黃月華、白解紅.2006.英語介詞多義研究之我見——over例析[J].外語與外語教學(11):4-7.
廖光榮.2005.多義詞范疇原型裂變、次范疇化及相關問題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10):12-13.
林杏光.1999.詞匯語義學和計算語言學[M].北京:語文出版社.
劉宇紅.2004.R.W.Langacker認知語法述評[J].外語研究(4):6-11.
束定芳、唐樹華.2008.認知詞匯語義學回眸[A].束定芳.語言研究的語用和認知視角——賀徐盛桓先生70華誕[C].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15-45.
嚴辰松.2006.構式語法論要[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4):6-11.
袁毓林.1998.語言的認知加工和計算分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紹全.2010.英語專業學生多義詞習得的認知語言學研究[J].外國語文(8):101-7.
張曉東.2003.分層網絡模型與激活擴散模型對英語詞匯教學的啟示[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6):3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