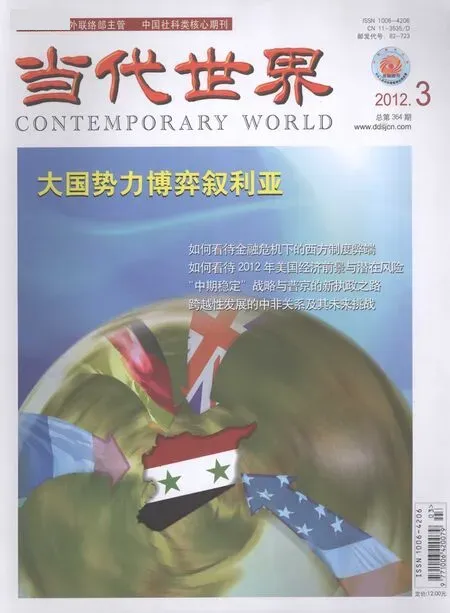跨越性發展的中非關系及其未來挑戰
跨越性發展的中非關系及其未來挑戰
■賀文萍/文
中國龍年新春伊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出席非洲聯盟(簡稱非盟)第18屆首腦會議并對埃塞俄比亞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此次訪問不僅是有史以來出席非盟峰會的最高級別中國代表團,而且賈慶林主席還出席了中國援建的造價8億元人民幣的20層非盟會議中心的落成典禮,并宣布了中國未來三年將向非盟提供6億元人民幣援助的新倡議。
和以前歷次中國領導人出訪非洲一樣,一些持“零和”思想和冷戰思維的西方媒體不僅想當然地把中國領導人出訪非洲又慣性解讀成“能源之旅”或“石油之旅”,甚至帶著醋意地渲染中國援建非盟會議中心是為了“展示在非洲的影響力”,批評中國在非洲“涉入太深”,以及所謂“中國殖民非洲”等等。
的確,隨著近十年來中非政治和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國際媒體、西方智庫及學術界有關中非關系的報道和討論急劇升溫,有關中國在非洲搞所謂“新殖民主義”的鼓噪也在泛濫。客觀地說,在這些鋪天蓋地的“報道”和“研討”中,既有大量負面的“中國新殖民主義論”、“中國掠奪非洲資源論”,也有正面的“中國促進非洲發展論”和“中國機遇論”。那么,為什么中非關系忽然間似乎成為了一門各方關注的“顯學”,西方為何對中非關系的發展如此“熱衷”和“關注”?中非關系如今究竟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未來發展又面臨什么樣的挑戰?
中非關系的跨越性發展被認為是“動了西方的奶酪”
在過去的十余年里,中非關系依托“中非合作論壇”這一強勁的機制化平臺,在貿易、投資、承包合作、發展援助等各個領域均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如今,中國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雙邊貿易額從2000年的100億美元躍增到2011年的1600多億美元,2009年超越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另外,非洲還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場和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相比西方從15世紀開始就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在非洲進行了數百年的殖民統治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長期“投入”和“耕耘”,中國與非洲之間雖說最早的接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中國的漢代,但真正意義上經常性的中非交往則始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時間跨度也就短短的60年。特別是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建立以來的最近十年來,中非經貿關系更是每三年就跨越一個新臺階,這自然讓一些把非洲視為自身“后院”的西方國家,特別是其中一些持“零和”思想和冷戰思維的媒體和政界人士感到不舒服,仿佛是中國“動了西方的奶酪”。
一、中非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
自1949年 新 中 國 成 立 以來,中非關系大致走過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中國和非洲國家關系建立和發展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非關系主要體現在反帝反殖、爭取民族解放和鞏固國家獨立斗爭中的相互支持。突出的兩件大事是周恩來總理的訪非(1963 年12 月至1965 年 6月間先后三次訪問非洲11國并在訪問期間提出了“中國對非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和坦贊鐵路的修建(1970—1976年修建完成,耗資4.55億美元,成為中國對非外交史中的一座豐碑)。非洲國家和人民對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的正義事業也給予深切同情和積極支援,并為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做出了重要貢獻。在1971年第26屆聯大會議上,恢復中國合法權利的提案終以78票贊成(其中非洲國家為26票)、35票反對、17票棄權、2票缺席的壓倒多數獲得通過。毛主席因而形象地稱之為,“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聯合國)的。”
20世紀80年代的十年可以說是中非關系發展的第二階段。在繼續加強中非友好政治關系的同時,合作重點開始轉向經貿領域,強調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多種經濟技術合作。1983年初中國提出了同非洲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的四項原則,即平等互利、講究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這四項原則是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深化和發展,它有力地推動了新時期中非經貿關系的發展。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及非洲形勢的變化,中國再次適時調整了對非政策,中非關系進入了全面合作的第三階段。除繼續加強中非經貿合作的力度外,中國還重視從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多渠道、多層面地全方位發展中非關系。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的成立為加強雙邊交流、溝通和合作建立了機制化的戰略平臺。
二、“中非合作論壇”對中非關系的有力推動
從2000年10月在北京舉辦的第一次會議到2003年的亞的斯亞貝巴會議,2006年舉世矚目的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及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的第四次部長級會議。每隔三年就舉辦一屆的論壇會議已成為中非合作與發展的一個重要舞臺和強有力的推手,使得中非關系在這十年里取得了快速和全方位的發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非關系發展最快的時期。
十年來,中非之間在推進建立和發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安全上加強交流和磋商,以及國際事務上加強合作”的“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在政治層面,頻繁進行的中非雙邊高層互訪(胡錦濤主席已六次訪問非洲,習近平副主席也于2010年11月中旬出訪南非、博茨瓦納及安哥拉等非洲三國)及在國際重大問題和雙邊事務上的相互支持使中非政治互信不斷深化;在經濟層面,中非貿易額在近十年里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長,從2000年的100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068 億美元、2010年的1269億美元及2011年的1600多億美元。中國對非投資也從2001年的5000萬美元提高到近年來的年均10億美元,投資存量則已超過100億美元,涉及礦業、制造業、農業等多個領域。目前,中國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非洲躍居中國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和第二大海外勞務工程承包市場。在非洲的中國人已近百萬,在非洲開展經貿活動的中國公司已達2000多家;在文化和教育層面,以弘揚中華文化和推動文化交流為宗旨的“孔子學院”在非洲如雨后春筍般地建立,非洲來華留學生和各類人力資源培訓班的數目也呈直線上升趨勢;另外,在安全領域,中國近年來積極參加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行動,共派出3000多名維和人員參加了12項維和行動,現仍有1100多名官兵活躍在非洲八個維和區。而且中非間近年來還在防治重大傳染性疾病、禽流感、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了磋商和合作。
中非關系十年的快速發展是與“中非合作論壇”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理念分不開的。論壇自建立之日起,就本著為非洲國家和人民辦實事、減貧和促發展的精神,不搞空泛的政策宣示,而是在減債、大幅增加對非援助、促進對非投資以及大規模擴大非洲零關稅進口商品的種類等方面推出實實在在、具體的實施計劃和推進措施。為幫助非洲解決糧食安全等民生問題,每屆論壇還特別針對農業合作、人力資源培訓、醫療衛生和教育合作等提出了每三年需要完成的具體量化目標。
應當說,這些具體措施和量化目標的提出,一方面彰顯了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及負責任大國對非洲發展問題的關切,另一方面從技術和操作層面上看,目標越具體,指標越量化,監督落實就越容易,從而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實上,從歷屆中非合作論壇行動綱領的落實情況看,每屆論壇提出的目標都能按計劃如期甚至提前完成。中非論壇用十年的實踐和行動表明,它不是奢談非洲發展的空談俱樂部,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中國同非洲國家之間開展集體對話、交流治國理政經驗、增進相互信任、進行務實合作的重要平臺和有效機制,是中國對非關系及中國多邊外交的一個響亮的品牌。
中非合作論壇十年鑄就的品牌效應還體現在其與時俱進的精神及在國際社會對非關系中所發揮的示范和帶動作用。中非合作論壇從不墨守成規、固步自封,而是隨著中國、非洲的國際形勢的發展及中非合作關系的深化而不斷充實論壇的框架和內容,從而實現論壇自身的不斷發展。第一屆論壇北京會議為中非發展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關系確定了方向;第二屆會議增加了“中非企業家大會”;第三屆會議建立了“中非外長政治磋商機制”;第四屆會議召開前夕則舉辦了“中非婦女論壇”、“新聞研討會”等新的對話機制。這使得中非合作論壇的合作領域不斷從政治層面擴大到經濟、文化層面,從政府間對話延伸到企業、傳媒界、民間友好團體之間的合作對話。另外,從論壇推出的行動綱領看,每屆論壇提出的促進中非關系發展的舉措均很好地體現出中國對非政策的延續性和創新性。如第一屆論壇重點是對非減免債務,為非洲關注的巨額債務減免問題發揮中國的作用。第二屆會議強化對非人力資源培訓。2006年北京峰會則大幅度、全方位在減債、投資、援助、民生等方面提出了對非合作的“八項舉措”,使中非關系邁上了一個新臺階。2009年第四屆論壇提出的“新八項舉措”則回應國際社會和非洲提出的新關切,在延續和提高以往各項領域的支持力度之外,又在環境保護、清潔能源、科技合作及支持非洲中小企業融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政策措施。
事實上,如果西方一些戴有色眼鏡的人士能夠從“零和”思維中走出來,把目光放得更遠,應當不難發現中非關系發展對非洲及對世界的積極意義。中非合作論壇十年來所走過的成功之路,其意義已經不僅局限于推動中非雙邊關系前進本身,而是對推動其他國家及整個國際社會關注非洲、幫助非洲發展都產生了輻射效應和推動作用。2006年北京峰會結束后,陸續能看到韓國—非洲峰會、日本—非洲峰會、印度—非洲峰會、第二屆歐洲—非洲峰會及土耳其—非洲峰會,甚至不久前的越南—非洲峰會等等。應當說,由中非關系快速發展所客觀帶動的國際社會對非洲發展的新一輪關注對非洲發展是一個利好消息,這有利于改善非洲發展的外部環境及為非洲發展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另外,從更廣闊的人類發展大勢和社會進步的視野看,在當今南北差距持續擴大、恐怖主義威脅陰霾不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繁榮及深度參與并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果實對于推動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和諧發展也具有深遠的意義。
未來中非關系可持續發展中面臨的挑戰
后發而勃興的中非關系在引發了非洲的興奮和西方的關注的同時更應該讓中國自己心存挑戰意識和危機意識,在總結經驗的同時更應當反思不足和教訓,以便能夠在國際風云激蕩、非洲形勢也不斷出現新變化的環境下繼續挖掘潛力,深化全方位合作的中非關系,把中非友好之船沿著和諧發展的方向駛向未來。
首先,從經濟層面看,現階段中國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貿易量的快速提升并不意味著經濟競爭力的同步提升,貿易結構、經貿合作中的技術和科技含量、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甚至有關法律和專家人才隊伍的鍛煉和培養等其他經濟競爭力的指標要素都缺一不可。在提升中國在非洲的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道義感召力和外交親和力這四個方面,都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有很長的路要走。在許多方面,西方的一些經驗和做法也需要中國放下身段來學習和借鑒,來自非洲的有益提醒和建議更需要中國認真傾聽。
事實上,中非關系的可持續發展和中國在非洲到底還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對一些非洲關注的敏感問題(比如加強中國公司的屬地化管理,當地勞工的雇傭不足問題、紡織品工業的競爭和保護非洲幼稚工業問題、中國商品的質量問題、提高中國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等)如何回應,如何在走入非洲的過程中真正從非洲的利益著想,切實做到、做好互利雙贏。
其次,在細細掂量中國通過艱辛努力所取得的上述中非經貿合作的“物質”成就時,中國也需要對中非交往在“思想”領域中的不足甚至是缺失心存憂患意識。長期以來,著力投資和援助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看得見”和“摸得著”的“硬件項目”一直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和中非交往中的突出特點之一,并且在實踐中也深受非洲人民的歡迎。相比較而言,西方國家則把資源更多地投入到培育非洲的市民社會、非洲領導層的“能力建設”、非洲知識精英的學術研究等“軟件項目”上。這種—“硬”—“軟”、—“外”—“里”的區別在素來就憂患意識有些過頭的美國國會山議員和智庫專家們看來似乎成了美國對非外交的“不足”,因為他們希望美國“兩手都要硬”,“里外都要抓”。
回過來看中非交往,雖然近年來中國開始重視對非洲的人力資源培訓和中非間的人文交流,也啟動了中非聯合研究交流計劃,但對這方面的重視與投入若與在“硬件項目”中的投入相比,仍難以望其項背。長期以來,中國在海外利益(當然也包括在非洲)的拓展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因秉承“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中方雖經過多年打拼和努力,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逐漸積累了經濟方面的權重和影響,但在政治、安全、外交及話語權等方面的影響則并未同步發展,與西方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如今,非洲的一流學生首選的海外留學目的地仍然是歐美國家。雖然中國人在非洲已有近百萬之眾,在非洲投資興業的中國公司已逾2000家,但在非洲的大學里仍難覓執教的中國教授,在非洲的傳媒和刊物上也難聽到中國聲音。非洲的精英層(包括領導人及知識精英)也大多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民主”、“自由”等思想理念上與西方的契合度也往往大大高于中國的想象。
因此,未來中非關系的發展除繼續在經貿合作方面做好做實以外,還特別需要在話語權的提升方面多下工夫。需要明確的是,話語權的擴大、提升和掌握并不簡單是爭奪“麥克風”的問題,而是擴大和深化中非之間溝通和交流的范圍和領域,特別是要就“人權”、“主權”和“民主”等思想領域方面的關鍵和核心問題展開充分討論并達成共識。長期以來,西方國家高舉“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大旗,堂而皇之地長久占領著輿論的道德高地。中國則一直秉承謙虛與低調的傳統,在“不干涉內政”和“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原則下,埋頭實干抓生產,促經濟。正因如此,雖然如今滿世界都是“中國制造”的產品,但西方卻能一邊享受著“中國制造”的物美價廉的商品,一邊輕易地把“環境污染”、“資源掠奪”和“新殖民主義”等一頂頂帽子扣到中國的頭上。而這些如“狼來了”般的囈語經過不間斷的重復也逐漸滲透到了非洲的語境和觀念之中。
事實上,中國在非洲的思想領域發揮并提升中國的影響力應當是大有可為。由于中、非之間在歷史遭遇、發展階段上的相似性,中、非間在“人權”、“主權”方面有許多共識。如與西方片面強調人權的普遍性、個人性、至上性和政治性相比,中國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更強調民族權利等集體人權和發展權等人權的經濟屬性。即便在大多接受西式教育的非洲精英層(包括領導人以及知識精英)與西方認知契合度較高的“民主”、“自由”等思想理念上,中國也可以解放思想、大膽與其展開發展經驗交流和多渠道的民主對話。如同股票和市場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屬品一樣,民主、自由與人權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獨享物。如今,始自華爾街的金融危機、西方的經濟衰退、中國等新興國家成功應對危機的沖擊并保持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等等,這些因素的疊加已經在非洲催生了一種“向東看”的政治思潮。中國應緊緊抓住這一歷史契機,從思想上爭取非洲精英層,為掌握話語權打下思想基礎。
第三,隨著在非中資企業和務工人員的日益增多,在非中國人及中資財產的安全保護問題也需引起中國的高度關注。2012年年初,就在中國歡慶雄偉的非盟會議中心建成投入使用之時,從蘇丹和埃及先后傳來中國工人遭當地反政府武裝和勢力綁架的消息已經讓國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國企業和中國工人“走出去”的風險及中非關系中仍存在的隱憂。
提升中國企業和中國工人的海外安全系數可以說是一個綜合工程。不僅政府層面需要加大外交部和各駐非使領館的領事保護工作力度,不僅要協調與所在國政府的關系,也要跟各部落、武裝勢力的領導人建立暢通的溝通渠道,擴大接觸面,增加情報來源。企業則需增加對安全成本的重視程度,提高在安全和風險防范方面的投入和主觀能動性。個人也需多了解所在國的社會及文化,包括一些當地“方言”及習俗,提高對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另外,未來在探討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如何加強中非之間的安全合作時,也要引入保護中國企業和中國人安全的內容,從機制上探討安全問題的解決方案。
總之,隨著中非關系的發展不斷走向深入,其所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嚴峻。對這些挑戰,中國必須未雨綢繆,事先做好分析、預判和預案,否則容易陷于被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責任編輯:魏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