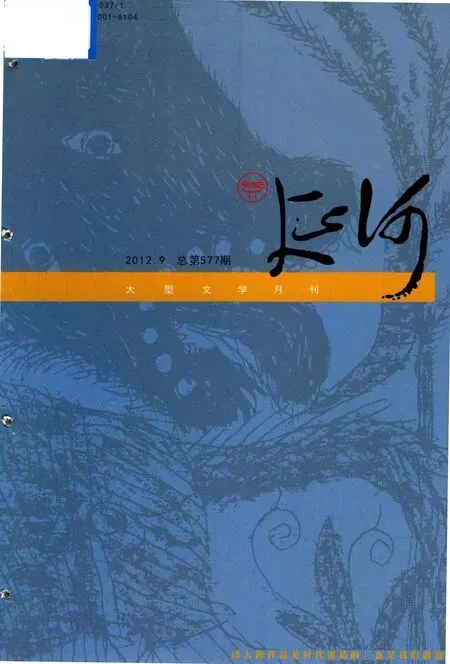拉哥們一把
和軍校
魏明新拿到組織任免的紅頭文件以后,躲進洗手間里,褲子也沒有脫,就那么干蹲著,咬著自己的袖子,任淚水飛揚。魏明新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不是板上釘釘的事兒,他不會露一絲聲氣。最先,是郭頭兒給他吹的風。郭頭兒說,三十年的媳婦熬成婆,你熬成了,祝賀!魏明新知道郭頭兒跟組織部長是牌友,他的話向來不是空穴來風。辦公室的同事們陸續逮著了風聲,嚷著叫魏明新請客,魏明新硬是撐得穩如泰山。后來,組織部長找魏明新談話了,魏明新知道他的這個副處級八九不離十了,但他還是不動聲色地該干啥干啥,不張不揚。公示之后,紅頭文件下來了,直到這會兒,魏明新懸在半空的心才算落到了肚子里,他知道,這個副處級已經是他袖筒里的鳥兒了,再也飛不了了。魏明新的眼淚越淌越歡,心里五味雜陳,只有他清楚,為了這個副處級,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悄悄地哭了一氣,魏明新用袖子把眼睛沾干凈,用涼水洗了臉,抿著嘴唇,然后一點一點地把兩個臉蛋吹大,再一點一點把氣放出去!往事如煙。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一去不復還。他魏明新副處長的幸福生活從此翻開新的一頁了。
魏明新走馬上任后,郭頭兒原本想給魏明新安排幾個出頭露臉的活兒,但魏明新提出他先去基層走一走,跟基層的同志見見面,熟悉一下。魏明新的理由很充分,容不得郭頭兒不同意。魏明新知道,郭頭兒是他命中的貴人,他現在的一切都是郭頭兒給他的,沒有郭頭兒,就沒有他魏明新的今天。他不想跟郭頭兒擰著來,但他也有自己一點隱私。
魏明新決定先去烏爾禾。這一決定,連魏明新自己也嚇了一跳,天大地大的克拉瑪依,他為什么偏偏選擇了烏爾禾?平日里,太多的瑣事總是讓魏明新焦頭爛額疲于奔命,烏爾禾進入思維和夢想的時間越來越少,亦無牽掛,直至忘卻。此時此刻,烏爾禾第一時間躍入他的腦海,且越來越清晰,隨之清晰的還有師傅、小初、阿福。烏爾禾,是魏明新踏上工作崗位的第一站。那會兒,魏明新剛從大學畢業,他的師傅在烏爾禾,他的初戀在烏爾禾(如果那還算做初戀的話)。魏明新恍然明白,不是他忘了烏爾禾,而是他一直回避著烏爾禾。二十年彈指一揮,物是人非了,他可以坐著屬于自己的專車風光無限地回烏爾禾了,他要大聲地告訴烏爾禾:我魏明新又回來了!他還要告訴整個世界,沒有靠山的人照樣可以功成名就飛黃騰達光完耀祖。他要去見見師傅,見見小初,見見阿福。
烏爾禾的天還是這么高,還是這么藍,烏爾禾的空氣里還是飄蕩著濃濃的牛羊肉的馨香。魏明新視線模糊了。魏明新和阿福同一天來到烏爾禾采油廠報到,同一天給小初的父親當了徒弟。師傅是個銼墩墩,四方大臉,愛下棋。收下魏明新和阿福為徒的當天下午,師傅就把兩個人請到家里吃飯了。師傅端著酒杯說,在我這兒,有個老規矩,收徒弟的第一天,在家里擺個收徒宴。往后呢,我肚子里有多少貨,給你們倒多少貨,看你們不順眼了,也打,也罵,打了你,你擔著,罵了你,你也擔著。如果你們愿意擔著,就端起酒杯,這一杯酒下去,咱們就是情同父子的師傅和徒弟了,如果不愿意,擰身子走人,我不攔。魏明新和阿福不約而同地端起了酒杯,叮當一聲響,三個人一飲而盡。就在那次飯桌上,魏明新見到了小初。小初漂亮得像仙女一樣,聲音像銀鈴一樣,魏明新一個勁兒地咽著口水,他實在想不明白,師傅這樣丑陋的男人怎么能有小初這樣如花似玉的女兒?他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小初追到手。魏明新沒有把阿福列為情敵。阿福畢業于另一所高校,是個農村娃,性子溫和,貌不驚人,衣著不講究,走路低著頭,開會坐角落,人多不開腔,一副與世無爭安于現狀的模樣。魏明新和阿福住同一間宿舍,魏明新巧舌如簧,阿福笨嘴拙舌,魏明新喜歡夸夸其談,阿福是大事小事都擱在心里,性格的差異,使兩個人成了形影不離無話不談情同手足的好朋友。魏明新說,逛去?阿福說,走。魏明新說,喝酒?阿福說,成。魏明新說,去師傅家玩?阿福說,走。魏明新問,你說小初長得漂亮不?阿福說,嗯。魏明新問,你說我跟小初般配不?阿福說,嗯。眾所周知,師傅沒有多少文化,卻是一名天才棋手,每次廠里舉行棋類比賽,師傅都是第一名。每次比賽前,師傅往棋盤前一坐,咬一根煙,不管對面坐的是誰,他都用食指敲一敲棋盤右下方的車馬炮,說你隨便拿掉一個吧。有人拿掉了車,有人拿掉了馬,有人拿掉了炮,不管拿掉了啥,結果還是師傅勝。當阿福坐在師傅的對面時,師傅還是老話老動作,阿福說,師傅,不用。師傅抬頭見是阿福,呵呵一笑說,還是拿一個吧。阿福固執地說,師傅,不用。比賽就這么開始了。第一局,阿福勝;第二局,師傅勝;第三局,阿福勝。阿福笑著說,師傅讓我呢。師傅連聲說,后生可畏后生可畏。說畢,師傅用拳頭拄在了桌子上站起來了,那一拄,似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氣。師傅丟了冠軍,丟了威風,也丟了“棋圣”的名號。魏明新直看得牙根發癢,心下說,瓷乎乎的,你就不能讓讓師傅?但阿福不讓。阿福就是這么一個人,實誠,也犟,犟得像牛!
可是,后來和小初手牽手走進婚姻殿堂的不是魏明新,而是阿福。魏明新捶胸頓足后悔不已痛不欲生,徹底明白了什么叫大意失荊州。
魏明新奇怪的是,在阿福面前受挫的師傅不但不生氣,反而越發地喜歡魏明新和阿福了,得空就叫他們去家里吃飯,吃罷飯,師傅就和阿福擺上了棋攤子,魏明新看不懂棋譜,對下棋也沒有興趣,他就陪著小初干家務,洗鍋呀,涮碗呀,掃地呀,一塊去沙漠里看月亮呀,一塊去看露天電影呀……魏明新是幸福的,從小初的笑聲中,魏明新判斷得出來,小初是喜歡自己的,也是幸福的。魏明新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他開始憧憬以后的幸福生活了。
師傅突然給阿福和小初訂婚了。之前,一點征兆也沒有,師傅沒提過,小初沒提過,阿福也沒提過,怎么就訂婚了呢?魏明新很失落,很傷感。酒席上,師傅笑得很開心,小初笑得很開心,阿福也笑得很開心,魏明新悄悄地把眼淚往肚子里咽。那一刻,魏明新恨師傅,從里到外,阿福沒有一點比得上他的,師傅怎么就相中了阿福呢?由此,魏明新又聯想到師傅的一系列所作所為:技術培訓,師傅讓阿福去了,阿福在大城市逛了半個月;技術比武,師傅讓阿福參加了,阿福得了冠軍;生產中有了疑難雜癥,師傅也讓阿福去了,阿福總是手到病除……魏明新不服氣,如果讓他參加培訓,讓他參加技術比武,他照樣拿冠軍,如果讓他解決生產中的疑難雜癥,他也能做到手到病除。可是,師傅把機會都給了阿福。魏明新明白了,師傅是偏心的,他愛的是阿福。或許,師傅、小初,還有阿福,他們共同都在嫉妒他的聰明能干。魏明新思謀著跳槽了。技術干部雖然吃香,但技術干部越來越多,想出人頭地,比登天還難,思來想去,魏明新打算逆流而上。魏明新探聽到郭頭兒要來烏爾禾檢查工作時,他對郭頭兒的基本情況了解了一番,找郭頭兒毛遂自薦了。
魏明新雙手把自己的簡歷呈上去,一臉誠懇地說,郭處長,我想干宣傳。
郭頭兒看罷魏明新的簡歷,說,你給我一個理由。
魏明新說,念大學的時候,家里窮,我就靠當家教補貼學費,也一直想當老師,但受專業的限制,只能到采油廠來,但我還是想當老師,想搞宣傳,我的興趣和特長就是愛寫愛畫。魏明新之所以這樣說,是他了解到,郭頭兒的兒子正在念初中,學習一般。
郭頭兒把魏明新端詳幾分鐘,意味深長地“噢”了一聲。
一月后,魏明新的調令來了。
離開烏爾禾時,魏明新一直沒有回頭,這是一處傷心地。
干上宣傳以后,魏明新像許多的宣傳干事一樣,寫廣播稿,寫通訊報道,辦櫥窗,貼標語,掛橫幅……和許多宣傳干事不一樣的是,魏明新還是郭頭兒孩子的家庭老師,還是郭頭兒的服務員。鞭炮紛亂年氣濃濃家家團圓的時候,魏明新陪著郭頭兒和郭頭兒的朋友走進沙漠腹地“放松”——靠近農家樂搭起自己的帳篷,吃抓飯,吃烤肉,喝燒酒,然后就是打牌。郭頭兒愛打牌,愛得通宵達旦廢寢忘食,魏明新并不參戰,他只是做服務工作:搭帳篷、泡茶、找零錢,點菜。郭頭兒說,所謂放松,就是遠離老婆娃娃,專心致志地打牌。節假日了,魏明新要陪著郭頭兒“一條龍”:泡澡、捏腳、按摩、喝酒、卡拉OK……郭頭兒說,人嘛,不僅要會工作,還要會生活,生活嘛,就要豐富多彩。郭頭兒嘴上的活兒很講究,雞蛋要吃土雞蛋,面粉要吃新麥磨成的面粉,土雞蛋哪兒來?新麥磨成的面粉哪兒來?都是魏明新從300公里外的老家源源不斷地運來……幸運的是,郭頭兒沒忘魏明新的這一番苦心,把他扶上了副科長的位置,又扶上了科長的位置。年齡漸漸大了,專業忘得一干二凈,魏明新怎么甘心在科長的位置退休呢,他做夢都想“進步”。如果不進步,怎么對得起自己的一輩子?魏明新心里明白,要想進步,他就得有讓郭頭兒張得開嘴的資本,所以,他在陪郭頭兒之余,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博覽群書上,再一篇接一篇地寫著“大塊”文章,發表在油田的報紙上。辦公大樓下有一塊公示牌,機關有什么活動呀,通知呀,人事變動呀,都會在公示牌上公示。魏明新最關心的就是那一塊公示牌了,暗想,他魏明新的名字總有一天會出現在那塊公示牌上。有一天,魏明新的媳婦出差了,他中午泡了一碗方便面,就沒有下樓,下午上班以后,魏明新見辦公室的幾個人鬼鬼祟祟地咬耳朵,他問老寧,啥事呀,神神秘秘的?魏明新跟老寧年齡相仿,也是“進步”路上的競爭對手。老寧說,祝賀你,上公示牌了。魏明新的心呼地一下就懸了起來。但他故作鎮定地說,又拿我開涮呢。老寧說,真的,不信,下樓看看不就明白了?魏明新沒有下樓,他在網上溜了一會兒,然后裝作去洗手間,從洗手間出來后,直接下樓了,公示牌上確實有新內容,確實有魏明新的名字,公示的卻不是干部任免通知,而是遲到早退名單。魏明新像是被人抽了耳光,低著頭,匆匆從公示牌前消失了。他知道老寧等著看他的笑話,他發誓要打敗老寧,不能讓老寧看他的笑話,不能讓師傅、小初、阿福他們看他的笑話!
住進賓館以后,魏明新想先去拜訪老黑。老黑不姓黑,生得黑,就掙得了老黑的綽號。魏明新跟老黑是校友,老黑比魏明新高兩屆,屬師兄,實干家,升得也快,現在是副廠長。魏明新在烏爾禾時,就跟老黑走得近,兩個人喜歡端著老碗喝燒酒,還喜歡吃烤羊腿。魏明新撥通了老黑的手機,問,師兄,在哪兒瀟灑呢?老黑說,打兔子呢。魏明新說,師兄真夠腐敗呀,上班時候打兔子?老黑嘿嘿笑著說,你是不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了?魏明新抬腕一看,竊笑自己真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原來今天是星期六。魏明新說,師兄你多打幾只,晚上就吃你打的兔子。老黑說,怎么,衣錦還鄉了?感謝師傅來了?魏明新打著呵呵說,什么呀,搞調研嘛。老黑說,好,晚上見。收線以后,想起剛才的一番對話,魏明新覺得老黑一句話說對了,一句話說錯了,說對的一句是:衣錦還鄉。說錯的一句是:感謝師傅。自己的升遷跟師傅井水不犯河水呀!
賓館很整潔,很寂靜,獨自呆著的魏明新百無聊賴,就出去在街道上溜達,街面上的商店、餐館、理發館、招待所,都似曾相識,里里外外都透著一股親切勁兒。走著走著,魏明新陡然發現眼前的一切竟然是這般熟悉,這幾株槐樹,這一片草叢,這兩條石凳,這……不是師傅家屬區的那棟樓嗎?自己怎么不知不覺地走到這兒來了?樓已經很陳舊了,師傅還住在這兒嗎?一個老太太正坐在樹下的石條凳上搖扇子,魏明新向老太太打聽師傅是不是還住在這兒,老太太揚手朝上一指說,四樓,靠東那一家。聽到這一聲,魏明新的腿就軟了,心里泛起一股酸楚。二十多年了,師傅還住在這棟55平方米的小樓房,他們的生活可想而知了。想當初,師傅要是把小初嫁給他,一切都是另一番景象了。魏明新打算回賓館去,等買一些禮物,再正式地前來看望師傅。魏明新一擰身,怔住了,他的身后站著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女人,手里拎著菜,愕然地張著嘴巴。
明新,真的是你嗎?女人情不自禁地問。
果真是小初。二十多年過去了,小初的輪廓沒有變,聲音沒有變,膚色沒有變,只是頭發沒有了往日的濕潤和光澤。
魏明新叫了一聲小初。
小初興奮地說,我爸和阿福都說你這幾天要來呢,果真就來了。
魏明新笑著沒吱聲,也沒有把小初的話往心上擱,這次烏爾禾之行,除過郭頭兒,沒有人知道的。難道師傅和阿福會算卦?小初之所以這么說,或許是出于客套。
小初揚著手里的菜說,我爸和阿福釣魚去了,走,家里去,我給咱做飯。
魏明新遲疑著。
小初說,怎么,剛當了官,就擺官架子呀?
魏明新一頭霧水,她么知道自己當官了?他急忙擺手說,不不不,我想……
小初說,別想這想那的,快家里去。
師母走得早,師傅一直沒有續弦,師傅又守了小初這么一個女兒,所以一直跟小初過活。師傅家的布局還和過去一個樣,簡單,整潔,過去的木頭沙發換成了布衣沙發,18英寸的背頭電視換成了32英寸的液晶電視,木頭小圓桌換成了玻璃茶幾,墻上還掛著兩張地圖,一張世界地圖,一張中國地圖。小初給魏明新泡了一杯茶,系上圍裙,坐在茶幾前,一邊摘菜一邊和魏明新拉家常。
魏明新問,師傅還好吧?
小初說,好著呢。
一杯茶裝進肚子里,魏明新徹底放松了,他想從小初的臉上中捕捉一點后悔的神情,他卻失望了。魏明新說,小初,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不知當問不當問?
小初說,看你,當了官就變得這么生分了,說吧,啥事?
魏明新問,當年,你怎么突然就和阿福訂婚了?
小初說,這事呀,我給你說。有一天,我下班后,我爸突然對我說,你也不小了。我明白我爸的心思,說爸你想趕我出門呀,休想。我爸說,就算我不趕你出門,你也該考慮個人問題了。我說,這是你考慮的問題,不是我考慮的問題,你看上誰就是誰。我的脾氣你知道,打小就被我爸慣壞了,大事小情都靠著我爸。我爸點燃了一支煙,半天沒言語,直到把那支煙抽完了,我爸才說,阿福的母親病了,按關中的風俗,想討一門親事,定個婚,沖個喜,爸知道,這是說不出口的事,也是迷信的事,但是俗話說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所以,我想給你和阿福訂婚,你想一想,你要是同意,就點個頭,要是不同意,權當爸沒說。我說,爸,我聽你的。我爸喜出望外,問我,你同意?我表態說,你同意我就同意。你知道,我打小就是一個乖乖娃,遇事沒主意,大事小情都聽我爸的。
魏明新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是這個結果,他問,就這些?
小初說,就這些。
小初并沒有征求魏明新的意見,和面、切菜、拌餡兒、搟皮兒、包餃子,韭菜雞蛋餡兒。魏明新心里暖烘烘的,小初還記著他的最愛。
魏明新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復雜的情愫。小初是善良的,是純凈的,是無辜的,只要從師傅的臉上看到愧意,只要從阿福的臉上看到自愧弗如,這一頁就算翻過去了,就算看在小初的情面上,他也應該拉阿福一把的,他給老黑說句話,把阿福調進機關還是有可能的,當個科長副科長也是有可能的。魏明新比自己的想法嚇著了,原來,“給師傅、小初、阿福他們一點顏色瞧瞧”的想法盤踞在他的心頭。
小初保持著往日的麻利,包完餃子,又拌了三個涼菜,一碟熗蓮菜,一碟老虎菜,一碟尖椒變蛋。小初把涼菜擺上桌,說明新,你先吃。
魏明新連連擺手說,要不得要不得,等師傅和阿福回來了一塊吃。
小初笑道,他們呀,天不黑是不進家門的。
小初告訴魏明新,父親是退休后愛上釣魚的。每天天一放亮,左手漁具,右手小凳子,晃晃蕩蕩出發了,風雨無阻。小初還告訴魏明新,阿福就是一個跟屁蟲,父親愛上釣魚,他也愛上了釣魚,每逢周末,他就跟父親一塊釣魚去了,起早貪黑的。
魏明新問,那吃飯怎么辦呢?
小初說,上班的時間,我就給父親帶點吃的,周末了,我就做點好吃的,給他們送過去,和他們一塊吃,孩子在念大學,周末也不回來,我一個人呆在家里也無聊,就出去跟他們吃個熱鬧。
魏明新喜出望外,說,走,我跟你一塊給師傅送飯去,我也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小初推辭不過,就收拾了行禮,跟魏明新一塊給父親和阿福送飯去了。
大自然很神奇,人類很偉大。竟然能在浩浩蕩蕩的沙漠中竟然能建起一個魚塘!有了水,便有了靈氣。一方碧水,幾株綠樹,一群水鴨,鳥兒的啁啾聲在枝頭跳躍著。
樹蔭下鋪了一塊碩大的塑料布,師傅和阿福兩個人赤著腳盤腿而坐,每人跟前放著一個大塑料杯子,里面是顏色不正的劣質茶葉。中間是棋盤,兩個人正殺得全神貫注。
小初說,哪是釣魚,完全是掛羊肉賣狗肉。
小初又說,他們每天每人只釣一條魚,然后就下棋了,我不送飯,他們不吃飯,我不叫他們回,他們就死坐在這兒。
魏明新心里泛起一股悲涼的情緒,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兩句“俗話說”,頭一句是:破罐子破摔;第二句是:棒槌敲肚皮——自己給自己寬心。
魏明新恭敬著叫了一聲師傅,師傅瞅了一眼魏明新,說明新回來了。阿福也跟著附和了一聲,明新回來了。師傅和阿福都沒有表示出他所期盼和想象的欣喜,他們的表情和口吻都淡淡的,仿佛他們早就知道他要來或者說他壓根就不曾離開過這里,更像過去他給師傅當徒弟時出門打了瓶醬油又轉身回來了一樣。隨后,師傅和阿福又急不可待地把目光和注意力轉移到了棋盤上。
魏明新心里有幾分失落。
小初說,別下了,吃飯吃飯。
師傅伸出一只手掌阻攔道,別著忙,別著忙,這一局,我倒是要看看鹿死誰手!
阿福不動聲色地說,是啊,鹿死誰手還真說不準呢。
師傅哼了一聲說,不服輸,咱們就騎驢看畫本——走著瞧!
阿福嘿嘿笑道,走著瞧走著瞧。
小初著了急,蹲下身,三把兩把把棋盤上的棋子兒撥拉了亂七八糟,邊撥拉邊說,瞧個啥呀,瞧個啥呀,再瞧黃瓜菜都涼了!
師傅和阿福不約而同地伸手保護棋盤上的現狀,無奈不及小初的手快。
小初命令道,快洗手吃飯。
兩個人不滿地咕噥著在魚塘里洗了手,小初從塑料袋里拿出一條干凈毛巾遞給師傅,師傅拭完了手,遞給阿福,阿福拭完了手,遞給小初,小初又疊得四方四正地裝進塑料袋里。師傅和阿福又一次赤腳坐在塑料布上,小初也學著兩個人的樣子,把鞋丟在一邊,盤腿坐在塑料布上,她擰頭招呼魏明新,明新,快來坐呀。
魏明新猶豫著,他很想像師傅和阿福一樣,赤腳坐上去,但他又很想表現一下“領導”的矜持和大城市人的文明。
明新,快來坐呀!小初又叫了一聲。
魏明新只好脫了鞋,在塑料布上坐下了。小初把三個涼菜和餃子擺上“餐桌”,開始分發餐具,一人一個小木盤、一個小碟子、一雙筷子、兩張餐巾紙,分發完畢,兩手一拍,喊,開飯嘍!
師傅抄了一筷子涼子,邊嚼邊說,有點酒就好了。
小初瞪父親一眼,冷腔道,都‘三高’了,還酒酒酒,往后少跟我提酒!
阿福說,沒那么嚴重,少喝一點不礙事。
小初又瞪了阿福一道,揚了聲說,你個馬屁精,少在這兒裝好人,都‘三高’了,還不嚴重?啥算嚴重?住醫院里就算嚴重了?往后,你也少跟我提酒的事兒。
阿福舉手投降,說,好好好,我也不提酒的事。
小初并沒有動筷子,她在剝蒜,剝一瓣兒,扔師傅碟子里,又剝一瓣兒,扔魏明新碟子里,又剝一瓣兒,扔阿福碟子里,再剝,再扔。這一家人都愛吃蒜,餐桌上一年四季都有剝好的蒜瓣兒,師傅說過,大蒜是天底下最好的消炎藥。魏明新跟這一家人學會了吃蒜,那會兒也覺得大蒜香,解饞。自從調到克拉瑪依,魏明新就不吃大蒜了,那沖鼻子的味兒,漱口漱不凈,刷牙刷不凈,嚼口香糖也于事無濟,他要給郭頭兒匯報工作,他要跟著郭頭兒檢查工作,他要開會,他要在電梯里上上下下,薰了郭頭兒和別人可怎么辦呢?最近流行的一句話叫做細節決定成敗,這話說得有分量,在大機關工作,不講究細節怎么行呢?
魚塘邊,樹蔭下,塑料布上,一片香噴噴的咀嚼聲,這般和諧,這般溫馨,這般幸福。魏明新突然想起了他的妻子,那個性格怪異的小出納,魏明新幾乎每天晚上都有應酬,應酬完了都是搖搖晃晃回家的,回家就跌在沙發上喊水——水——水——,可惡的小出納不但不給他倒水,還惡聲惡氣地罵,有本事就喝死到外面去,有本事就不要回家!往往,魏明新都是在小出納的罵聲中走進夢鄉的。
飯畢,師傅和阿福還要下棋,小初說,下什么下,今天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呢。
師傅“噢”一聲,說,釣魚。
阿福朝魏明新揚了揚漁具,魏明新擺了擺手。
師傅和阿福坐魚塘邊了,兩個人一人咬一根煙,一切都寂靜下來,知了的叫聲格外嘹亮。
魏明新和小初相視而笑。
魏明新在心里感慨,淳樸的小地方人,他們是多么容易滿足啊!
返回的路上,魏明新心事沉沉,一句話也沒有說。
晚上,老黑給魏明新接風洗塵。這是魏明新“愛得要命恨得要死”的場所,這是魏明新熟悉又迷戀的氣氛,在這里,魏明新如魚得水。老黑請來的都是校友,還有魏明新往日的幾個好朋友。老黑原本也是請了師傅和阿福的,師傅說他不能碰酒,拒絕了,阿福說他有事兒,也拒絕了。
魏明新坐在“上席”。坐在“上席”的感覺真爽,魏明新的眼神和抬手動足的做派都有了居高臨下的意思。老黑站起身,舉著酒杯,干咳一聲,正要講開場白,隨著“吱呀”一聲小心翼翼的門響,探進來半拉腦袋,是阿福。老黑急忙招呼阿福快來坐,又吩咐服務員加一套餐具。
阿福把一個剪貼本遞給阿福,說,你們喝你們喝,我還有事呢,走了走了。
阿福說走了,真的就走了。
魏明新翻開剪貼本一看,驚呆了,這是他發表在油田報紙上的“作品集”,有“豆腐塊兒”,也有“大塊頭”,一篇一篇貼得整整齊齊,每篇文章下都標注著發表的日期,從字體上看,有的是師傅寫的,有的是小初寫的,有的是阿福寫的,無一例外地都是一筆一劃寫上去的,公公正正。魏明新曾經讓小出納把的“作品”收集整理一下,說不準那一天要出一本書的,小出納不以為然地說,溜須拍馬的玩意兒,誰看呀,還出書呢,不夠丟人現眼的!沒想到,師傅一家人默默地替他做好了這一切,魏明新鼻腔發酸。
沉默了片刻,再仰起頭來,魏明新又是一臉燦爛的笑容了,他舉著剪貼本說,人嘛,就要自強不息,就要靠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出人頭地,才能功成名就,否則,只能落個像阿福這樣的下場。
魏明新一席話,說得滿桌人面面相覷,大家都把目光集集在老黑的臉上。
老黑嘿嘿一笑,帶頭鼓了掌,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魏處長說得好說得好,來,咱們共同為魏處長敬一杯。
魏明新站起身,卻沒有像慣例那樣挨個兒跟大家碰杯,他說,師兄啊,在座的都是自家人,我也就不見外了,俗話說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給我一個面子,咱們共同拉阿福一把,你剛才也看見了,阿福就是那么個實在人,給一個不長進的師傅當女婿,有點兒自暴自棄,有點兒不求上進,但咋說也跟我‘共患難’過呀,把他調進機關如何?給他一個副科長如何?
老黑被說得一愣一愣的,但他很快就換上了一副輕松的表情,把大家瞅了一遍,笑著說,聽見了吧?魏處長明明知道阿福一直是咱們這兒的技術尖子,也知道廠里幾次想把阿福調到機關來,油田機關也想把阿福挖走,這個阿福呢就是不去,說他就喜歡在基層做點具體工作。還有,這個阿福是有點死心眼兒,不喜歡當官,如果喜歡當官的話,肯定在我和魏處長之上。可是,魏處長剛才為啥要那樣說呢?你們不懂了吧?這就是幽默,魏處長的幽默!
魏明新瞠目結舌。
老黑繼續說,還有,咱們魏處長的師傅,阿福的老丈人,你們都知道的,也都認得,在烏爾禾,哪個敢不尊著敬著?還有一個小秘密你們都不知道,想當初,魏處長的師傅發現魏處長的性格不太適合搞專業,才一步一步把魏處長推到現在的位置,你們都傻眼了吧?想不通一個老工人怎么會有這么大的本事?告訴你們也不妨,郭處長你們肯定都聽說過,很牛皮的人,他也是從咱們烏爾禾出去的,他也是魏處長師傅的徒弟,也愛下棋,師徒兩個情同父子,每年春節,他都要來烏爾禾給師傅拜年,從不例外。可是,魏處長剛才為啥要那樣說呢?告訴大家,還是幽默,魏處長的幽默。閑話說得多了,來來來,咱們喝酒喝酒。
魏明新手中的酒杯慢慢傾斜,酒一點一點地灑出去。
這一夜,魏明新酩酊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