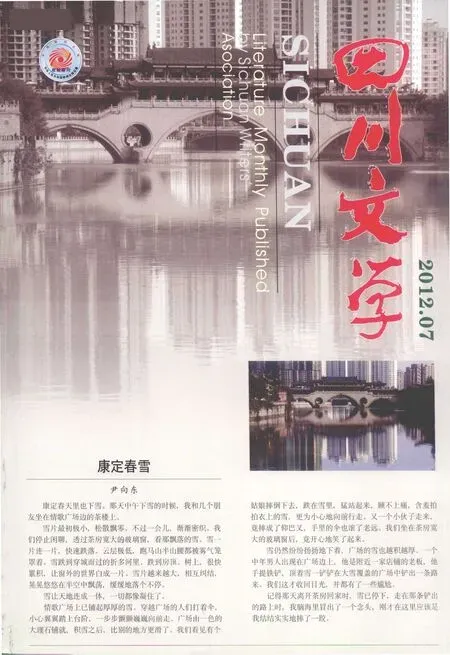川 斷
□汪文勤
清晨7點20分,川斷的手機響了,他的手機從來不會在這個點兒響。
剛剛過完59歲生日的川斷,每晚的睡眠都是支離破碎的,好像切成好幾截的臘腸。恰恰這個時間是他最重要的睡眠時間,一天的精力全靠這點覺撐著。
手機不停地響著,不像是打錯的。川斷勉強自己來接聽這個電話。
“爸爸、爸爸,起床了!”
川斷唔了一聲,便怔住了。
電話里是一個小男孩的聲音,這個聲音沖破川斷的耳膜,進入他半夢半醒的腦海里,好像一面響鑼掉進了山谷,立刻濺起一串回聲,不絕如縷。
川斷的大腦一片空白,小男孩叫爸爸的聲音竟不住地在空蕩蕩的腦殼里回旋起來。這個飽滿而明亮的聲音像一支小號,驟然吹響,川斷凝神聽著,整個人動彈不得。
按常理,川斷應該說三個字,“打錯了”,然后放下電話繼續睡覺。但是,他發現自己舉著手機緊貼著耳朵,一點兒不想放下來。于是,他的無語和猶豫,激勵著小男孩用更大的聲音叫起來,或許孩子以為爸爸睡得太香甜了吧。
“起來了,爸爸。別說我沒叫你啊!在學校運動場比賽,我們是黃隊。來不及了,我走了,再見,爸爸!”
小男孩掛斷了電話。川斷仍舊舉著,里面的嘟嘟聲,在川斷聽來,全部是“爸爸!爸爸!爸爸!”一聲比一聲緊密。
不知過了多久,川斷放下電話,躺下來想再睡一會兒,但闖進腦海里的那一聲爸爸卻怎樣都趕不出去了。
在一個59歲男人的世界里,四季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春天何時來,二月的風里飄蕩著春的氣息,興許已經不是這個年齡的男人所能夠感受到的。但是,小男孩不由分說,劈頭蓋臉叫爸爸的聲音,好像用春天柔軟的柳枝做成的柳笛,咂咂口,用力一吹就會響"啵——啵"——這哪里只是小男孩叫爸爸的聲音。
柳笛吹響了,春天發聲了,春天的聲音就是小男孩叫爸爸的聲音。
川斷不睡了,柳笛在耳邊那么一吹,心中竟有了一小片春色,癢癢的,絨絨的,這種感覺久已不在了,興許是在他23歲,或者25歲時,很不經意的一些瞬間里,閃過那么一絲絲,好像柳絮飛進了脖頸,楊花沾在唇上,留不下來,捉不住,也撣不掉,轉頭也就忘記了,不在春田里,不再經歷,便不再記憶。
“爸爸!爸爸,起床了!”小男孩兒誤打進來的一個電話,真把習慣睡懶覺的川斷叫起來了。他走進衛生間開始洗臉刷牙,許久以來,他都懶得多看自己一眼,胡子、眉毛、頭發都像野草,自由發旺,自由生長。
現如今導演、唱歌的都喜歡留胡子和頭發,對他們來講,這個裝扮是他們對世界的一個宣告,身份的宣告,說明什么呢?說明他們是人,但絕不是普通人,他們羞于和普通人為伍,似乎頭發不長,胡子不長,就不能入行似的,長發和長須是進入演藝界的護照。有時候,電門還沒摸著呢,先把胡子頭發留起來,束在腦后了。川斷從十七歲開始就觸電了,只不過那時說的觸電就是指電工,而不是指電影電視什么的。四十多年前,他是一個肩挎著灰白色帆布工具袋的英俊電工,在北京一家大型的兵工廠工作。后來,川斷很自然地把自己擺渡到影視制作行業,他自認為這是一個必然。
這些年來,川斷就一直混跡于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劇組里,游走在祖國大地上,劇組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生態環境,這里允許異類的存在。所以,不知不覺間,川斷原本中規中矩的人生軌跡偏行一隅了,許多該停的站沒有停靠,該看的風景沒有看,頭發一點點長長了,胡子也留起來了,他居無定所,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一部片子,一個劇,從頭至尾,再精彩的故事,拆開了再一點點拼裝起來,又熬人,又枯燥乏味兒,如同孩子們面對樂高玩具,拆開了看一塊一塊兒的,完全看不出名堂,一旦拼裝成形,才有了意趣。川斷在劇組里干雜活兒,什么都干過,每天看見的都是樂高的零配件。事實上,川斷并沒有玩過樂高,他覺得自己的工作是在孔雀的背后,看見的永遠是孔雀的屁股,開屏是從正面才能看到的風光。川斷是站在孔雀后面的人。孔雀屁股有什么好看,臭烘烘的。但是,有時候,臭也是一種香,好像榴蓮,好像臭豆腐。川斷習慣了,他已經離不開劇組這個特殊的環境了。好像有人吸毒成癮,無法戒除,不是不知道那趣味兒是惡趣,會害死自己,但人生太清醒不易過,半夢半醒就容易打發。
后來這三十年真是混過來的,好像數得出來,吃過幾頓飯,睡過幾次懶覺,有時工作到后半夜,其實常常是后半夜,喝得醺醺然,倒頭睡下,第二天上午起來時頭疼欲裂,看著鏡子里的自己,頭發胡子都灰白起來,好像小時候看見的街角糧店里打面的工人,除了眼珠兒以外,別處都白著。后來,慢慢地,川斷再也不愿意在鏡子里看見自己,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沒有誰在意他,也沒有誰能讓他在意。罷罷罷!他想放自己一馬。
就這樣59歲的川斷,從里到外透露出來的氣質就是對自己的放手。所謂放浪形骸大致就是他這種樣子吧。身體和臉都好像雞蛋煎餅,隨意地攤開去,誰還收得攏呢?
一直在刷牙的川斷,看著鏡子里的自己,覺得在看一個不認識的人,這是我嗎?他問自己。他用牙刷柄扎一下自己的腮,痛還是痛的,是自己沒錯,是一個叫川斷的人,但為什么會這樣陌生?像一個來歷不明,去向不明的人,有誰認得和記得這樣一個人呢?百年以后將沒有一個人會紀念他吧?
“我這他媽的,混成什么樣了?什么都不是。”
川斷的心往下沉,有點灰。
正當此時,又聽見小男孩在叫:“爸爸,爸爸!起床了!”
川斷使勁擺擺頭,想搞清楚狀況,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僅僅是一個打錯的電話嗎?為什么這個聲音又出現了?
如果一個人的早晨是在小公雞的“喔-喔喔”的叫聲中,在小男孩清脆的聲音“爸爸,起床了!”中開始的,那是何等真切的日子。陽光從墻肩上輕輕跳下來,一點點挪著,好像早年那些小腳的奶奶,從一面墻挪到對面那堵墻,正好是一天的光陰,日子被慢慢的暖暖的陽光烘焙著,厚厚的塵土都出了香味兒,可以咀嚼、品嘗。有人叫爸爸的早晨,是多么真切的早晨,那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生呢?那可能會是他川斷的人生嗎?他早已經不做這樣的夢了。像他的名字預示的一樣,川斷,川斷。生命一條河,他的生命之河斷流了。
川斷不無厭棄地看著鏡中的自己,這雞蛋煎餅已經不是新鮮的剛攤出來的煎餅了,而是一張殘剩的,沒有形狀的,也許從不曾規整過的,現在更是起了毛邊,缺了邊角的,快要被扔進垃圾箱的廢棄物……現在丟掉還有點不舍得,但吃下去一定會壞肚子。川斷第一次感到有一點傷心,覺得自己有點可憐。難道在這世上活著的川斷就不應該有另外一種生涯嗎?比如:在合適的時間,遇見了合適的女人,結了婚,生了一個兒子,每天早晨,兒子會用柳笛的聲音叫醒他,在他去學校之前。如果今天早晨的電話沒打錯,自己真的是被自己的兒子叫醒……川斷問了自己一個無解的問題:這樣一種再平常不過的、也本應該是自己的這種日子,自己什么時候丟掉了呢?應該叫自己爸爸的那個孩子在哪里呢?他本應有的兒子還會對他說些什么呢?
川斷仔細回憶小男孩在電話中所講的每一個細節,學校、比賽、黃隊……川斷在心里拼湊著這些碎片。這是誰正擁有的幸福生活呢?此刻,他無比痛恨自己是個沒有家,沒有孩子的老光棍。如今的時代比較寬厚,容得下各色人等,老光棍似乎沒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在川斷經歷過的、現在還記憶猶新的上個世紀,老光棍是一種很狼狽的人生,如果是在一個村莊里,他除了要背負“絕戶頭兒”的悲情名聲以外,差不多和身體有殘障的人在一個級別上。人家家里有喜事請客,這樣的人怕是不能上桌的。如今,時代變了,單身成了一種選擇,而不是無奈,在小男孩叫爸爸的聲音出現以前,川斷也許并沒有質疑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現在不同了,小男孩柳笛一樣的聲音叫川斷的心底里凍結的一種東西松動了。
川斷開始修剪滿臉的胡須,力求使自己的臉看上去有點形狀,起初只是想把野草似的胡須稍剪一下,川斷不是一個果敢的人,這滿臉的胡須到底也是一寸寸長出來的,他可以承受這個緩慢生長的過程,即使此刻想有點什么變化,也不會讓坡太陡,下得失去了方寸。可是,讓他自己沒想到的是,一寸又一寸,他居然把胡須弄干凈了,他看著鏡子中的自己,覺得很久很久沒有見過自己了。他用十根手指攏著頭發,心想,頭發也該收拾收拾了。
川斷一刻都不能停下來,只要停下來一駐足,一凝神就聽見那個聲音在叫:“爸爸,起床了!”收拾停當的川斷試圖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去干點平常事,想點自己慣常想的事,或許,給什么人打個電話,約點什么事兒談談,在咖啡館之類的地方,那個時間會過得很快,不覺就是一天,不覺又是一天。
手機上的聯絡人從頭看到尾,沒有哪個名字讓他有興趣去撥號。甚至排在最前面的白小姐的電話,以往,白小姐是一個他抗拒不了的誘惑,她在一家男士養生館工作,她大而深邃的眼睛,柔軟無骨的小手,尤其是她為他按摩頭部時,她鼻孔里呼出的氣息,小小的,溫溫的,帶著青草的香氣噴在他的臉上,那是他內心深處的美酒。他悄悄地,秘密地消受著,從來未向任何人說起過,他片刻地沉醉其中,有時候,他想自己是中了魔,對一種隱秘的刺激上癮,他說不清楚,也從來沒有細究過,每逢此刻,他會忍不住摁那個名字的號碼,約一個近在眼前的時間,飛速地趕過去,躲在那一雙小手下,陷在那一片氣息里,陷下去,不愿自拔。
可是今天,川斷的手指數次從那個名字上滑過,但他沒有撥號。緊接著他看見早晨那個誤打進來的電話號碼。
“爸爸,起床了!”
這次聽到的聲音不是從話機里,而是在身旁某處的空氣里,這個聲音沒有商量,更無歉疚,卻好似有一點命令的成分在里面。
川斷忽然想到,如果是這個聲音在耳旁,別說是睡著了,即便是長眠了,也會被激勵著翻身坐起的。這個聲音讓疲憊的人生有盼望,是興奮劑,一聽見就會起來去行動。
是的,川斷現在還不知道該怎么行動,但他已經開始行動了。他迷迷糊糊地剪掉了胡須,接下來,似乎還要發生什么不同尋常的事,川斷自己也不能確定。是的,他又不自主地走出門去,通常,他是不會這么早出門的。
走到大街上,看見有小孩子手里握著煎餅,一邊吃,一邊去上學,不是爺爺奶奶陪著,就是爸爸媽媽跟著。小一點的孩子被大人牽著手走。
“爸爸!”
身后又是柳笛一樣的聲音。
川斷急回頭,見一小男孩用雙手從背后托著沉甸甸的書包,一路小跑追一個腳步匆匆的男人。小孩可能在用一個鐵皮的鉛筆盒,他一跑,鉛筆在盒子里鐺鐺響著,川斷清晰地憶起自己的童年,也是這樣背著書包跑著,也有刷刷的響聲,只是自己那時沒有真正的鉛筆盒,幾根鉛筆頭裝在衛生所廢棄的裝青霉素針劑的紙盒子里。有一個真正的會發出清脆響聲的鉛筆盒,是川斷比天還大的夢想。
這樣的回想,讓川斷激動起來。原來自己也小過,也做過夢。
那個爸爸站住,歪過頭看自己的兒子。
“快點,要遲到了。”
兒子緊跑幾步追上爸爸,然后兩人用急行軍的速度向前趕。
原來并不清楚自己要何去何從的川斷,竟不知不覺地跟著小男孩往前去。來到一所小學校門口,小男孩兒和爸爸告別,揮揮小手跑進了校門,川斷和送孩子們上學的大人們都站在門外,川斷癡癡地站著看,盡管他沒有一兒半女在中間。孩子們進教室了,大人們也散了,校園里空空蕩蕩的,只有川斷還在門口站著,一間普通的小學校是他多少年都不曾多看一眼的陌生的地方,可這會兒突然變得親切極了。
他看著一扇扇四四方方的窗口,聽著孩子們清朗的讀書的聲音,竟有了一種莫名的感動。難道冥冥之中,真是自己的兒子在紅塵之外的遠方呼喚著自己嗎?
“爸爸,起床了!”
“請問,你有什么事嗎?”
保安觀察了半晌,覺得川斷形跡可疑。
“噢,沒什么,孩子上學了,我隨便看看!”川斷神色惶恐地說。
“沒事兒別在這兒轉悠,接孩子下午3點半再來。”
保安說著,用手晃了晃已經關上的學校大門。
“能進去看看學生們比賽嗎?黃隊……”不等川斷說完,保安說:
“有家長通知單嗎?”
看川斷一臉的張皇,保安又問:“孩子是幾年級哪一班的?打班主任電話也行。”
川斷仔細想著早上那個電話的細節,沒有提供這些內容,是啊!爸爸哪里會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幾年級幾班?但是他只知道今天他穿黃色球衣。突然,川斷擔心起來如果小男孩不再打電話找爸爸,爸爸或許會錯過看他比賽。小男孩一定會失望的。
川斷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是個心思縝密的人,居然會如此在意一個打錯的電話,后來,他驚奇地發現,小男孩的聲音并不在身體之外的什么地方,而是在自己的腦海深處,比想象的要深許多。同時,那個呼喚聲一直持續著,川斷注意時就聽見了,稍一分心就忽略了,無論聽或不聽,小男孩一直在叫:爸爸!
川斷痛苦地發現,這個聲音早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叫了又叫,從來就沒停下來過。只怪自己豬毛塞了耳朵眼,沒聽見。
叫聲迫使川斷沒有了退路,他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回到今早電話來之前的光景。回到昨天,繼續用一副沒心沒肺的樣子活下去。
在守門的保安眼中,川斷一定是一個失常的人。因為保安已回到自己的小門房里,一邊看手機,一邊吃吃地笑,不再理會川斷。
川斷看見馬路對面正好是本市最大的男科醫院,他知道,要想把在自己生命中呼喚著的那個小男孩變成真的,他必須得再干點什么。他想堂而皇之地進入這所學校的大門,大大方方坐在球場邊上,給穿黃球衣的自己的兒子大聲喝彩,鼓掌加油。一大早可以被一個柳笛一樣的小男孩的聲音叫醒,那是所有的日子里的幸福加起來都不及的幸福。想得到這個幸福嗎?川斷發現自己的回答一點都不含糊,那之前的玩世不恭,不在意,沒心沒肺都是偽裝。
川斷準確地從醫院專家一覽表上找出了能解決自己問題的一位老專家,看照片,足有八十歲了吧,是退休后又被返聘回來的,他叫胡開雪,似乎每一個老中醫都有一個不同尋常的名字,他們的名字預備了他們懸壺濟世的一生。
盡管這樣,老人家在寫下患者姓名時,還是被川斷的名字給吸引了。
“川斷,川——斷。你的名字是一味兒中藥啊!自己曉得嗎?”
川斷笑了,答非所問:“名字不好啊!給叫得斷子絕孫了呢!”
說話間,腦海深處又響起小男孩的聲音:“爸爸,起床了……”
“非也。”老中醫一手搭在脈上,一手在紙上劃字。“你知道嗎?川斷的后面其實還有一個字,叫做續。川斷續,斷了,再續上。川斷續專治骨折、骨裂。用川斷續外敷,骨頭在里面就接好了。”
川斷聽得渾身一陣酥軟,呼吸竟也急促起來,腦海深處那個爸爸的叫聲,一下子跳出來,在耳畔好像春天的第一聲柳笛,把耳膜鼓得生疼。
老中醫望也望了,聞也聞了,切也切了,只剩下問了,老中醫開始問。
川斷卻因為一個“續”字狂喜著,除了聽見不遠處叫爸爸的童聲,一時間,別的都聽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