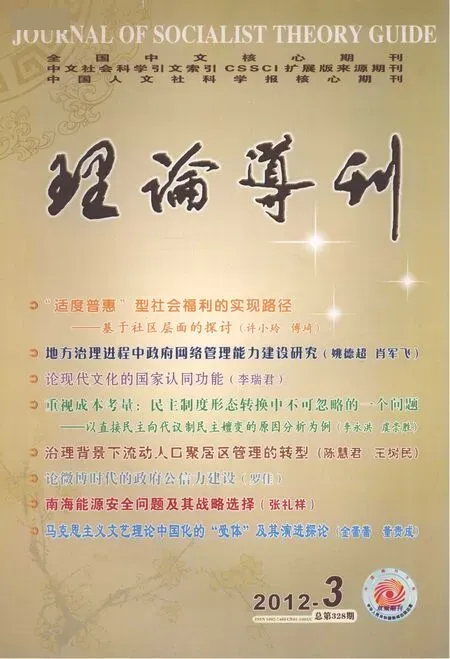倫理學視角下的弱勢群體關懷問題探究
梁德友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南京 210093)
倫理學視角下的弱勢群體關懷問題探究
梁德友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南京 210093)
作為人的基本道德需要,關懷是人在一定情境下產生的道德情感,它體現了主體間的一種倫理關系。弱勢群體關懷的核心是倫理問題,即“如何關懷”的問題。當前,在弱勢群體關懷實踐中,從理念設計到制度安排,從主體關系到組織程序都不同程度存在倫理失范現象,值得倫理審視與反思。在我國推進和諧社會發展建設的實踐中,必須通過物質幫助、制度倫理保障以及教育支持等策略實現對弱勢群體的倫理關懷。
弱勢群體;關懷;倫理審視
關懷本身是一個充滿倫理意蘊的概念,但關懷不一定都是倫理的。在某種程度上,有些關懷缺失倫理,甚至是反倫理的。在建構和諧社會的今天,弱勢群體關懷的倫理性問題,應成為學界研究的重要內容。
一、關懷的倫理意蘊
在漢語里,“關懷”一詞又同“關心”、“關愛”。從詞義學的角度講,“關懷”一詞的涵義偏重在“懷”上。在《辭海》中,“懷”的義項除了“胸前”和“心意”之外皆為動詞(懷抱、懷藏、想念、歸向、包圍、圍繞)。[1]32-34與“懷”相關的詞語有“關懷”、“懷念”等。因此“懷”在中國語言中是一個動作性、價值指示性很強的詞。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對“關懷”給予了很高的學術關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豐富的“關懷文化”。①“關懷”在英文里是“care/caring”,即照料、照顧、看護、養育等意思,主要是對處于不利地位的人或群體的一種關切和幫助。當然,這種照料、照顧、看護等主要是上對下、強對弱、優對劣,是對處于相對弱勢的人或群體的一種愛護、幫助和關照。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把關懷界定為人類生活的真正存在,是對其他生物的一種掛念的態度、認真做事情的一種觀念、最深切的真實的渴望、短暫的關注及所有屬于人類生活的負擔和痛苦。[2]15在西方話語中,“關懷”又表示一種“全身心投入”的狀態。
在當代,從倫理學的角度對“關懷”進行解讀和研究的是西方倫理學界的“另一種聲音”——關懷倫理學。關懷倫理學是上世紀60年代伴隨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而率先在英美社會逐漸興起的、建構在女性等弱勢群體視角基礎上,肯定女性的獨特道德體驗,強調關懷、情感和關系的一種倫理學理論。關懷倫理學代表人物有卡羅爾·吉利根、內爾·諾丁斯和薩拉·拉迪克等人,而其中又以當代美國倫理學家內爾·諾丁斯為主要代表。本文選取內爾·諾丁斯的關懷倫理思想,對關懷進行倫理學解讀。
內爾·諾丁斯借鑒海德格爾的觀點,認為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關懷,也都沉浸在關懷中,關懷體現了生活最終極的本質。[3]13由于在人生的各個時期我們都需要他人的理解、接納、尊重和認同,因此關懷他人和被他人關懷是人的基本需要。諾丁斯把關懷分為兩種,自然關懷和倫理關懷。對于自然關懷,她認為主要來源于人類自然的“愛的情感”,是人類情感的自然反應和基于義務的倫理情感,如同現實中當他人陷入“不利境地”向我們求助時,我們自然而然就會產生的一種“我必須”的道德意識。故這種關懷不需要人們在倫理上做出任何努力,僅僅表達了當事人的一種渴望和自然傾向,而不是對責任的認同。因此諾丁斯認為這種關懷是一種“自然”狀態,把它稱作為“自然關懷”。但是人的復雜性又常常使人們在實施“自然關懷”時,“我必須”的自然傾向遭到來自內部的抵制,也就是我們雖然看到了他人的需要,但卻因種種原因不愿予以關懷,這時就必須借助我們的倫理理想。那么何謂倫理理想?諾丁斯指出,“倫理理想是一系列關于關懷和被關懷的記憶,體現了自我和人際關系中最好的一面。因為我們珍視自然關懷中的關系,所以倫理理想就能激勵我們維持最初的‘我必須’,對他人的需要做出反應。”[3]14諾丁斯認為,這種關懷有別于上面的自然關懷,需要做出倫理努力才能實現,她稱之為倫理關懷。
諾丁斯特別重視道德情感在關懷中的作用。她認為自然關懷來源于愛的情感,倫理義務感的產生也不是來自“上帝的指示”或出于康德式的絕對律令。關懷的產生離不開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道德情感,都體現了人與人的一種關系性。不論是自然關懷還是倫理關懷,莫不如此。為此,諾丁斯指出關懷倫理就是要“建立、恢復和增強關懷的關系。在這種關懷關系里人們能根據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做出反應”。[3]14因此關懷的產生取決于雙方及特定的環境,諾丁斯認為在關懷中需要考慮的是具體情境中特定的人、特定的需要和特定的反應及體驗,而非從某種普遍性法則做出推理和判斷。諾丁斯的關懷倫理還承認人性的弱點,特別是人的情感容易受到外部環境或他人的行為影響,強調了營造有利于他人和整個社會道德生活環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132,[5]
正如諾丁斯所言,“關心其實是一種關系……”[6]但現實中,我們把關懷感性地理解為一種美德,屬于一種個人品質的范疇。這就把原本表示“關系”的關懷置于“個人的范疇”。因此諾丁斯特別指出“……但是,過分強調關心作為一種個人美德則是不正確的,將關心者置于關心的關系之中更為重要。不管一個人聲稱他多么樂于關心,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創造了一種能夠被感知到的關心關系”。[6]國內學者肖巍在《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一書中對諾丁斯的“關懷”作了闡釋,認為諾丁斯的“關懷”有著兩種基本含義:“首先,關懷與承擔是等同的,如果一個人承擔或者操心某種事態,并為之煩惱,他就是在關懷這些事情;其次,如果一個人對某人有一種欲望或者關注,他也是在關懷這個人。換句話說,如果他注意到某人的想法和利益,他就是在關懷這個人。”[4]132通過這種闡釋我們可以發現諾丁斯的“關懷”主要揭示了關懷雙方的互動關系,是一種雙邊的關系行為。那么關懷與被關懷雙方是一種什么性質的關系呢?是不是一種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回答是否定的。關懷所表示的關系是一種互為主體關系,是一種“主體間性”,即“關懷的形成一方面取決于關懷方對這種關系的維系,另一方面也有賴于被關懷方的態度和感受能力。就是說,關懷實際上是人們在身心上對他人或他物所承擔的責任,是關懷方把握他人的現實性,盡可能地滿足他人需要,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實現,并能夠得到被關懷方回應的一種關系行為”。[4]132
由此可見,關懷不僅是一種道德情感,更是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存在狀態,它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在關懷實踐中,關懷主客體之間是平等、雙向的互動關系,二者具有不同的道德分工和倫理責任。
二、轉型期我國弱勢群體關懷的倫理審視
關懷弱勢群體的核心是倫理問題,即如何關懷的問題。在感性層面上,人們通常認為弱勢群體是需要幫助的群體,只要我們去幫助、去關心,就是道德的行為,而很少有人從倫理角度反思,我們的關懷行為是否契合“倫理”。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關懷是人的基本道德需要。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關懷,也都沉浸在關懷中。關懷體現了生活最終極的本質,[2]15這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之一。關懷弱者體現了人對“應該”世界的訴求和對自身價值的深刻關注,同時也是人的“類”意識從自發到自覺直至實現道德自律的過程。這種“類”意識就是倫理規范的源頭,是人類擺脫“獸性”到達“人性”的主要標尺。隨著這種“類”意識的衍生、發展,最后逐漸精致就發展成今天人類共同的“道德律令”。“類”意識最初表現為對同伴、身邊人同類的關心,尤其是關注那些處境困難、身受痛苦、生命垂危及遭遇各種打擊、挫折和不幸的人。因為,人不同于世間萬物的地方,是對本身的生存有一種不滿足感,總希望有一種理想的生活,這種理想的生活就是倫理學揭示的道德生活。[2]649關懷他人、關懷弱者,就是人的一種道德生活,但是,綜觀我國對弱勢群體關懷的實踐,不得不說,關懷雖然已經行動起來了,但離“倫理”還有一段距離。甚至,有時是與倫理相悖的。
從對弱勢群體關懷行為雙方的主體關系來看,相對弱勢群體來說,關懷主體無論是政府、社會組織,還是強勢群體,往往擁有較高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地位;而作為關懷客體的弱勢群體身處社會底層或弱勢的地位,兩者之間的身份落差,構成了一種類似傳統社會的等級。強勢向弱勢施予的關懷活動,無可避免地帶有儒家倫理中“等差之愛”的性質,這是不平等關系中上層對下層施予的單向、無原則的關懷。因此,這種關懷是否合理和適度,只能由施予者憑借自身的德性修養和習慣偏好支配,并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正義原則作為公平的保障。[8]作為關懷者,在關懷過程中不時出現的“恩賜”、“救世主”的心態使被關懷者產生“恥辱感”。這種對弱勢群體的“強勢”關懷,使本來充滿倫理意蘊的關懷活動變成了令人難以忍受的“施舍”。
從關懷弱勢群體的動機來看,功利色彩濃厚。政府官員炫耀政績的大張旗鼓、社會組織帶有廣告性質的虛張聲勢,以及某些個人帶有炒作成分的作秀都使關懷行為成為了一場“表演”。廣大的弱勢群體被當作某些機構、個人撈取政治資本、吸引世人眼球,或樹立“社會形象”的“道具”和“演員”。在某種程度上,弱勢群體成為了某些人、某些機構消費的對象和作秀炒作的工具。弱勢群體在關懷實踐中往往得不到作為社會平等一員所應有的尊重。這種更多地從關懷者自身的某種功利出發的“關懷”多少使受關懷者在人格、尊嚴、自由和自主方面受損。作為社會的人,弱勢群體雖然在經濟等方面處于社會底層,但是,弱者在人格、尊嚴、自主性等方面絕不處于弱勢。在人格上,大家是平等的。弱勢群體絕非為了“五斗米”就會彎腰,去接受“嗟來之食”。所以,這種沒有倫理內涵的關懷不可避免地導致受關懷者生出一種心理上的自我防御,一旦當關懷的內容與其所持有的價值觀、信仰、風俗習慣等發生沖突時,或過多展示與現狀格格不入的奢華,或過多直露地體現,或宣揚與主流文化背道而馳的生活態度,關懷行為就會受到強烈抵制。弱勢群體就會下意識地“說服”自己“不被關懷”。那么,“關懷”也可能衍生出無所顧忌的傷害,更談不上“倫理”的關懷了。[8]
從弱勢群體關懷的機制安排上來看,也有很多經不起倫理考量的地方。例如,在關懷對象的選擇上,傳統計劃體制思維依然存在。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有的地方出臺的政策帶有很強的地方保護色彩,關懷中依然以戶籍為標準,內外有別,沿襲早已喪失現實合理性的歧視性規定,把廣大的農民工排斥在外。看似關懷弱勢群體,實為制度歧視。再如,關懷缺乏長效機制,沒有形成制度保障。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只在某些節日等特殊的日子才大張旗鼓地表現出來,是一種“臨時性”、“救急性”的關懷行為。另外,關懷形式比較單一。物質形式的關懷多,精神層面的關懷少,對弱勢群體進行倫理救助的關懷就更是沒人提及。凡此種種,都與倫理關懷的本意相去甚遠。
一位哲人曾經說過,重要的不是給予什么,關鍵是如何給予。關懷他人,關懷弱者,是人的一種道德生活。同時關懷又是一種關系行為,一種在任何時期我們都需要他人的理解、接納、尊重和認同的主體間關系,也就是說,關懷實際上是人們在身心上對他人或他物所承擔的責任,是關懷方把握他人的現實性,盡可能地滿足他人需要,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實現,并能夠得到被關懷方回應的一種關系行為。所以,關懷行為應該是一種充滿倫理情感的社會行為。由于種種原因,弱勢群體在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體驗不到自身價值,甚至還會遭到一些強勢群體的鄙視、嘲弄、疏遠和厭棄。尊重弱勢群體是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因為,作為社會關系中的人,弱勢群體有著與生俱來的權利和尊嚴,他們與社會其他人一樣渴望得到理解與尊重。
總之,弱勢群體關懷的核心是倫理問題。在弱勢群體關懷實踐中,必須對原有關懷理念、模式、行為方式進行倫理反思。轉變關懷理念,由“施恩”轉為“權利”,由“道義性關懷”轉為“義務性關懷”,由“臨時的節日性關懷”轉為“制度性關懷”。改進關懷的方式方法,運用主體間性原則,突出被關懷者的主體地位。根據弱勢群體接受程度的差異,制定具有倫理內涵的關懷方式、方法,讓弱勢群體有尊嚴地悅納關懷。同時,結合弱勢群體的倫理生態,對弱勢群體進行倫理救助。提高弱勢群體的倫理道德水平,恢復和重構弱勢群體的自我價值感。健全心理咨詢網絡,加強弱勢群體社會心態的監測、評估和預警,幫助弱勢群體達到心理和諧,實現全面發展等。質言之,在弱勢群體關懷中,關懷主體要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尊重、理解弱勢群體,讓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愛成為溫暖的陽光、及時的甘霖、沁人的春風,不僅使弱勢群體在逆境中得到關懷,而且,能夠在關懷中享受關懷。
三、弱勢群體倫理關懷的實現策略
弱勢群體倫理關懷以“人是目的”作為指向和尺度,是對人的尊嚴與符合人性的生活條件肯定的一種深層次關懷。弱勢群體倫理關懷的核心是倫理問題,但又不僅僅是倫理問題,它關涉到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是一個社會綜合工程。
首先,弱勢群體的倫理關懷應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倫理關懷不是排斥物質關懷,相反,物質的關懷應成為倫理關懷的主要部分,或者說是倫理關懷的基礎。沒有了物質作為基礎,倫理關懷就成了空中樓閣。物質需要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9]79而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把人的需要分為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社會需要,而且把生產滿足生理需要的物質資料作為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社會弱勢群體最大的弱勢就是物質上的貧乏,不僅處于初級的物質層面,而且幾乎處于物質層面的最底層。對他們來說,最需要的就是物質上的幫助。毛澤東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10]467轉型社會的今天,對弱者進行物質幫助是最大的倫理關懷。只有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一個社會才能具備相應的社會經濟資源,才能為解決弱勢群體的弱勢地位提供必要的條件、途徑和物質基礎。沒有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不論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多么“倫理”,也只能是紙上談兵,沒有實際意義。
其次,弱勢群體倫理關懷需要制度倫理保障。世界銀行《2005年全球企業經營環境報告》提出:消滅貧困,必須從消除制度貧困開始。在這里制度貧困并不是缺少制度,而是說不合理的制度容易導致貧困,合理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因此制度貧困主要表現為因缺乏制度的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匱乏和不合理制度產生的制度剝奪而導致的貧困現象。[11]制度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倫理道德的體現,對弱勢群體進行倫理關懷必須消滅制度貧困,建立公平公正的倫理制度。轉型社會的制度安排是“強者”優先,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群體的弱勢。所以,弱勢群體的產生與轉型社會的制度安排有關。消滅貧困、關懷弱勢群體,首先應消除制度的貧困,加強制度倫理建設。要根據弱勢群體的實際情況,制定有利于激發弱勢群體潛能的公共政策,創造一個讓弱勢群體自由、有信心地進入某個領域發揮才智的良好的政策環境、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使他們都有充分發揮其能力的平等機會,有憑借自身能力改變處境的發展機會和空間。目前我國的社會救助體系還很不完善、很不健全,國家必須盡快建立多層次的社會救助體系,在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中多考慮弱勢群體的利益,多傾聽弱勢群體的呼聲,使制度更多的體現對弱勢群體的倫理關懷和道德支持,并逐步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和規范化,盡可能使經濟發展中各群體做到起點公平、程度公正、經濟活動成本合理等。唯其如此,對弱勢群體的倫理關懷才可能實現。
再次,弱勢群體倫理關懷需要教育支持。社會學家阿馬蒂亞·森將現代社會的貧困看作是由收入貧困、能力貧困、脆弱性和社會排斥等因素構成的,并認為消除這種貧困的根本途徑是發展人的可行能力,以促進人的實質性發展。通過對弱勢群體成因的分析,除了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客觀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自身素質和自身能力的問題。必要的社會支持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最終擺脫弱勢地位還是要靠弱勢者自身的努力。1959年,美國學者奧斯卡·劉易斯首次提出“文化貧困”的概念,認為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結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點等,即“貧窮亞文化”。這種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就會對生活其中的人產生影響。要消滅貧窮,首先必須要改造貧困文化。所以,必須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教育支持,把“輸血”式救助變為“造血”式救助,在外部因素的幫助下提高弱勢群體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能力,走出困境,成為生活的強者。唯有如此,弱勢群體的潛能才有可能得以開發,社會才能夠實現真正平等、有效的合作,弱勢群體才能與社會其他群體一道共同發展,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注 釋:
①更多的學者把中國文化的特質概括為倫理文化,該觀點已為大家熟知。筆者認為,倫理文化的稱謂主要體現了中國文化中對他人、社會、自然的一種“關懷”關系,用關懷文化來表述中國文化更符合我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1]侯晶晶.內爾·諾丁斯的關懷教育理論述評與啟示[D].南京師范大學,2004.
[2]Nel.Noddings.The Challenge to Care in Schools[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2.
[3]Nel.Noddings.Educating Moral People[M].New York:Teach ers College Press,2002.
[4]肖巍.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M].北京出版社,1999.
[5]何藝,檀傳寶.諾丁斯的關懷倫理學與關懷教育思想[J].倫理學研究,2004,(1).
[6]王亞琳.母親的聲音——試述諾丁斯關懷教育理論及對我國道德教育的影響[J].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6,(1).
[7]余衛東,戴茂堂.倫理學何以可能?——一個人性論視角[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
[8]周永姣.弱勢群體人文關懷心理探微[DB/OL].http://dx.fuyang.gov.cn/upload/Attachment/2008-11-27.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張小軍,裴曉梅.城市貧困的制度思維[J].江蘇社會科學,2005,(6).仇婷婷.我國傳統社會弱勢群體救助思想與制度的歷史變遷[J].政法論叢,2008,(3).
B82-05
A
1002-7408(2012)03-0030-0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1YJCZH093);江蘇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重點資助項目(B-a/2011/018);南京大學國家社科基金預研項目;江蘇省博士后科研基金(1102030C)。
梁德友(1971-),男,安徽宿州人,法學博士,南京大學政治學流動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政治社會學、社會保障理論。
[責任編輯: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