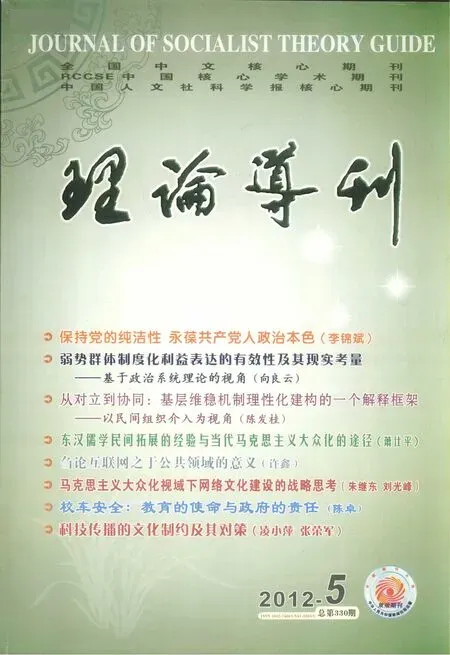關于檢察機關參與環境公益訴訟問題的幾點思考
馬梅鳳
(陜西警官職業學院,西安710043)
關于檢察機關參與環境公益訴訟問題的幾點思考
馬梅鳳
(陜西警官職業學院,西安710043)
環境公益糾紛近幾年不斷發生,如何通過公力救濟方式來解決環境糾紛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環境公益訴訟的出現對檢察院傳統的司法監督職能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國應盡快修改和完善相關實體法以及相關程序法,構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并對檢察院的職能進行重新定位,以實現環境公益訴訟實踐與立法的協調和統一,加速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制化進程。
環境公益訴訟;檢察院;職能
隨著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問題日益嚴重,環境保護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門話題。“佛山首例公益訴訟案”判賠百萬拉開了環境公益訴訟的序幕。環境公益訴訟目前處于一種“實踐先行,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它的出現對檢察院現有的司法監督職能提出了新的挑戰:不僅要求檢察院發揮原有的司法監督職能,而且要求檢察院發揮啟動環境公益訴訟的職能,即在環境公益訴訟中以原告的身份出現,以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使破壞和污染環境者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充分發揮環境公益訴訟的法治功能。
一、環境公益訴訟的基本涵義及檢察機關的現行職能
“公地悲劇”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個現象,在國外有人做了一個實驗來說明“公地悲劇”這一現象:取一塊草地,草地周圍被劃分成幾塊給幾個牧羊人分別專屬使用,草地中間作為公共領域用地——每一個牧羊人均可自由使用,一年后發現,被劃分給個人專用的草地能夠有計劃和有節制地使用,而作為公共用地的草地因為過度放牧而寸草不生。該實驗說明:公共利益處于無人管理和保護時最易受到侵害,而公益訴訟是解決“公地悲劇”的一種訴訟手段,公益訴訟的實踐先行反映了“公地悲劇”的嚴重性以及對其保護的迫切性。對于公益訴訟的界定,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尚存爭議,從世界各國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來看,公益訴訟多集中在環境領域,因而在公益訴訟中環境公益訴訟占據了很大的比重。環境公益訴訟是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的一種訴訟形態,1970年美國《清潔空氣法》最早確立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我國,隨著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以及人們環境維權意識的不斷提高,環境公益訴訟逐漸浮出水面,特別是被稱為環境公益訴訟第一案的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中心訴江蘇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環境污染侵權糾紛案,引起社會各界以及有關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1]關于環境公益訴訟的界定,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觀點認為,環境公益訴訟是指自然人、法人、政府組織、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其他組織認為其環境權即環境公益權受到侵犯時向法院提起的訴訟,或者說是因為法律保護的公共環境利益受到侵犯時向法院提起的訴訟;[2]還有觀點認為,環境公益訴訟是指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權對污染環境、破壞自然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提起經濟公益訴訟,由人民法院依經濟公益訴訟程序進行審判,依法追究責任人的民事、經濟、刑事責任;[3]還有觀點認為,環境公益訴訟是指社會成員,包括公民、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據法律的特別規定,在環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壞的情形下,為維護環境公益不受損害,針對有關民事主體或行政機關而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制度。[4]本文認為環境公益訴訟應以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為目的,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不是僅為獲得賠償由環境污染而致的經濟損害,而是為了預防、減少和消除可能嚴重影響環境公共權益的環境污染和破壞事件的發生,因此,筆者較為贊同第三種觀點對環境公益訴訟所做的界定。
實踐往往是推動立法的先行者,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在法院受理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既有公民個人作為原告,也有社會團體、行政機關以及檢察院作為原告的情形,其中,檢察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比較常見。在我國,檢察院是否可以作為原告提起環境污染訴訟,理論界尚存爭議。至于檢察院是否能夠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可以從檢察院的現有職能這一角度進行分析。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范圍無疑應該包括環境公益訴訟,其監督形式不應局限于事后監督,而應該拓展到事前和事中監督,提起訴訟的方式屬于事中監督的形式。持“否定說”的學者認為:在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第14條、第15條和《行政訴訟法》第10條規定了檢察機關有權實施“法律監督”和“支持起訴”,但是這些規定僅局限于審判監督和支持起訴,并未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與行政案件享有訴權。[5]迄今為止,檢察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仍停留在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層面,檢查院突破現行法律關于其職能定位的限制而大膽啟動環境公益訴訟可解環境污染受害者燃眉之急,但從“法無明確授權即禁止”原則來看,這種義舉不能不說是一種“良性違法行為”。在師出無名的陰影下,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無法掩蓋其推動司法改革和司法能動表象下逾越法律的尷尬處境。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首先自己得恪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其參與司法實踐的前提須得到法律的認可,“循規蹈矩”是法律對公權力的基本要求。[6]解決檢察機關這一尷尬處境的“靈丹妙藥”,筆者認為應該從法律層面對檢察機關的職能進行重新定位。
二、檢察機關作為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的應然性分析
環境是一種公共資源,全體社會成員均對之享有環境權益。當環境遭受污染或破壞時,就意味著整個環境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既然環境侵權具有公害性,那么,所有社會成員都應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尋求司法救濟。傳統的以個人救濟為中心的民事訴訟,很難對公共利益起到保護和救濟作用。而能夠代表社會公共利益進行訴訟的國家機關中,最稱職的非檢察機關莫屬。通過構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由檢察機關擔當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可以彌補我國環境保護制度的不力,使環境公共利益得到司法救濟和保護;環境公益訴訟將復雜的環境社會問題轉化成環境法律問題來加以解決,可防止矛盾升級,推進了法治的完善。
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通常被認為是各種利益的代表,因此,賦予檢察機關以原告資格是許多國家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中的選擇,如德國《行政法院法》確立了檢察官在行政訴訟中的公益代表人制度,并規定為維護公益,檢察官可以提起任何行政公益訴訟,而此處的公益包含環境公益。[7]檢察機關由“法律監督”和“支持起訴”職能轉變為啟動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即以原告身份起訴可以節約更多的司法資源,從而避免濫訴發生和訴訟程序的復雜化;同時,檢察機關職能轉變也是實現環境公益訴訟法治功能的要求與體現。具體來講,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通過環境公益訴訟可加強相關部門對環境法等相關法律的遵守,這要求檢察院職能發生轉變。環境公益訴訟以及環境法治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其他國家迅速發展,關鍵是環境公益訴訟的法治功能能夠推動環境法律規則以及相關程序法的不斷完善。檢察機關通過被動監督和支持起訴職能轉變為主動起訴職能,可以強化對實施環境公害、環境污染及環境破壞者的法律制裁和抑制功能,為環境法等相關法律的執行提供了有效的實現平臺,同時也可以促使政府相關部門積極履行管理、監督之職,恪守環境法所課以的保護公共環境權益的義務。由于重視公眾參與環境法律的實施,環境公共利益訴訟對美國環境法律的發展和環境保護產生了及其深刻的影響,同時也有力地保障了美國環境法的良好實施。[8]而我國的環境管理體制呈現出“重管理,輕公眾參與;重行政包攬,輕司法監督”的特點。環境管理部門由于受到僵化的環境管理權的制約,面對諸多環境糾紛顯得束手無策。國外的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證明,環境公益訴訟本身就是遵守和執行環境法的重要方式。但是如果沒有能夠承載環境公共利益的代表來啟動環境公益訴訟,那么再完備的環境法律體系也只是空中樓閣。因此,檢察機關的職能轉變對完善和實現環境公益訴訟的法治功能起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的法治功能也促使檢察機關的職能發生轉變。
2.實現環境公益訴訟的法治功能促使新的權利的生成,該新型權利需通過檢察機關職能轉變來實現。環境公益訴訟常常把沒有得到相關實體法加以規范以及傳統法理承認的利益作為法律上的概括性權利加以主張。通過環境公益訴訟提出的訴訟主張具有公共利益的內容,該訴訟主張背后的環境公共利益得以承認,即邁向了生成權利的第一步,新的實體權利或法的內容有可能在其后的訴訟過程及訴訟結果中得以形成。環境公益訴訟既是一場法律運動,也是一場權利運動。當某類社會沖突大量涌現時,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必須與時俱進地提供相應的救濟,及時創設權利、設定義務,以便對未來糾紛的再生和擴大形成約束。[9]當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與資源匱乏危及到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時,環境權的理論與實踐就會應運而生。許多國家通過憲法或法律的形式明確了環境權,如1980年《智利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生活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中,國家有義務監督、保護這些權利,保護自然。”我國關于環境權的規定已初步形成體系,如《環境保護法》規定,任何人都享有在良好的環境下生存的權利;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我國的環境權正在從應有權利向實體權利過渡,然而,環境權從應然權利轉為實然權利須借助于司法實踐即環境公益訴訟活動來推動,而能夠有效承載此功能的最有資格的機關乃為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啟動環境公益訴訟已有多起環境污染案例進行印證,司法實踐的踐行推動相關法律的完善和修改,以期對檢察機關作為訴訟主體作出明確界定。
三、檢察機關參與環境公益訴訟法制化路徑:職能的重新定位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該條是檢察院支持起訴權的法律依據。基于《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許多學者認為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職能定位是支持起訴。如果檢察機關的職能是支持起訴,那么檢察機關就僅僅扮演了為環境公益訴訟吶喊助威的啦啦隊的角色,實質上并未介入環境公益訴訟本身。毋庸置疑,檢察機關不以當事人的身份參與環境公益訴訟過程有利于法官客觀公正地裁判案件,但是檢察機關不以訴訟當事人的身份直接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的整個審判過程,其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作用將難以發揮,也就難以最終履行我國《憲法》所賦予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倘若將檢察機關的這種支持起訴權作為一種權利配置的基本路徑和運作模式去推廣,檢察機關必將面臨說話乏力而難以為眾多環境污染受害者伸張正義的尷尬。故檢察機關支持起訴者身份難以推動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制化進程。有的學者堅持“訴訟代理權說”,認為檢察機關介入環境公益訴訟的身份是原告的訴訟代理人,筆者認為該觀點混淆了檢察官與一般民事訴訟代理人之間的職責區別和法律地位的差異。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機關其權力配置來自于《憲法》的規定而非環境公益訴訟當事人的委托授權,其法定身份與民事代理行為的直接沖突導致其法定職責弱化和權限范圍受限,所謂“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豪言壯語,必將束之高閣,成為檢察機關不能承受之重。[9]因此,“訴訟代理權說”將使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流于形式。
檢察機關應該以何種身份參與環境公益訴訟是學界和實務界討論的熱門話題。檢察機關介入的公益訴訟案件共有200余件,其中近一半是檢察機關以原告資格直接提起訴訟。[10]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在公益訴訟中定位于公益訴權備受青睞。“訴權是法律監督權的核心權能,訴權能夠使法律監督權欲達到的目的最終付諸司法程序,并使違法行為通過審判受到應有法律制裁……如果沒有訴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將是一種被架空的抽象權力,而法律監督本身將必然是疲軟的、無助的。”[11]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可以作為原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公益訴訟在我國雖有實踐但沒有制度層面上的設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諸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俄羅斯、我國澳門地區等都賦予了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6]國外的立法經驗和成功的司法實踐可以為我國借鑒和參考。我國立法機關可通過修改《民事訴訟法》108條第一項關于“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規定而對原告資格進行擴張,為檢察機關作為適格原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提供法律依據。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權與其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不僅不沖突,而且檢察機關以原告身份啟動環境公益訴訟可以將發揮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作用與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司法保護有機地結合起來。此外,無論檢察機關作為原告還是作為監督者,其目的均在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而與自己的私利無關,檢察機關在環境公益訴訟中作為原告比其他主體更具有優勢。
檢察機關以原告身份啟動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踐已走在了現行立法前面。為了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加強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國家立法部門應該從法律層面對檢察機關的職能進行重新定位,以更好地推進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制化進程,解決實踐與理論的脫節問題。
[1]廖煥國.中國環境公益訴訟之興起與走勢——基于環境正義與環境訴訟價值進路的分析[J].太平洋學報,2010,(5).
[2]蔡守秋.論環境公益訴訟的幾個問題[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9).
[3]韓志紅,阮大強.新型訴訟——經濟公益訴訟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3.
[4]顏運秋.公益訴訟理念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210.
[5]張式軍.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原告類型和體系探討[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6]梁玉超.民事公益訴訟模式的選擇[J].法學,2007,(6).
[7]李傳軒.環境訴訟原告資格的擴展及其合理邊界[J].法學論壇,2010,(7).
[8]陳虹.環境公益訴訟功能研究[J].法商研究,2009,(1).
[9]呂金芳,郭林將.科學發展語境下民事公益訴訟檢察監督權的構建路徑[J].河北法學,2010,(1).
[10]張先昌,蔣偉亮.和諧社會語境下的檢察監督權——基于民事公益訴訟的闡釋[J].河北法學,2007,(9).
[11]張晉紅,鄭斌峰.論民事檢察監督權的完善及檢察機關民事訴權之理論基礎[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1,(3).
D926.304
A
1002-7408(2012)05-0096-03
馬梅鳳(1973-),女,河南安陽人,法學碩士,陜西警官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經濟法。
[責任編輯:陳合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