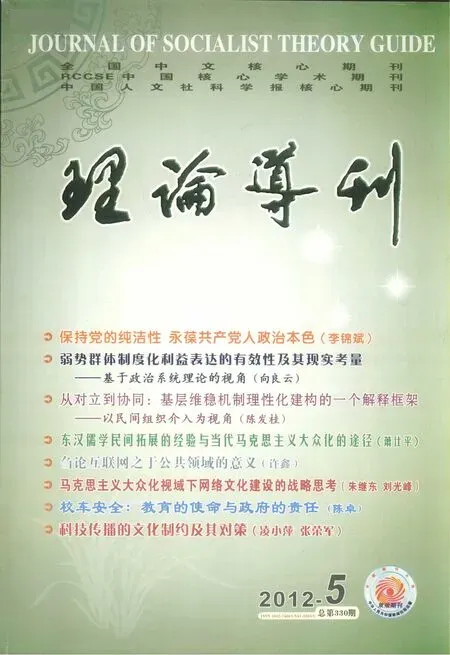江南文人李漁的陜西之行考略
趙海霞
(咸陽師范學院,陜西咸陽712000)
江南文人李漁的陜西之行考略
趙海霞
(咸陽師范學院,陜西咸陽712000)
江南文化名人李漁與陜西有著很深的淵源。李漁在游歷秦地期間,對以長安文化為代表的陜西文化印象深刻,陜西的風土人情,人們的淳樸、好客,以及秦地的方言都被記錄在他的筆端。李漁對陜西文化的接受及其互動代表了南北文化的一種交融,在當今推進文化發(fā)展和繁榮中仍有一定的表率和借鑒作用。
李漁;陜西;秦地;方言;賈漢復(fù)
引言
李漁生于1611年,卒于1680年,浙江蘭溪人,是我國明末清初文壇一位有思想、有追求的具有很高審美修養(yǎng)的奇才,他雖然一生未曾入仕,在當時卻名滿天下。平生詩詞歌賦皆通,著作等身,尤以《閑情偶寄》《笠翁十種曲》《無聲戲》(《連城璧》)、《十二樓》等影響廣泛。李漁一生很注重生活質(zhì)量,喜好大自然的美景,多次出游,他的游歷主要集中在50歲之后。從1666年(康熙五年)到1675年(康熙十四年)短短不到十年時間,李漁頻繁出游,先后游京師、游秦隴、游粵、游閩、游漢陽、再游京師等,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李漁曾自豪地說自己的足跡“四海歷其三,三江五湖則具未嘗遺一,惟九河未能環(huán)繞,以其迂僻者多,不盡在舟車可抵之境也”。[1]2571666年(康熙五年),旅居京師的李漁應(yīng)陜西巡撫賈漢復(fù)等人之邀,開始遠游燕秦。陜西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在漢代和唐代積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蘊。雖然到了明清時期,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有所轉(zhuǎn)移,但在明末清初浙江籍的小說家、戲曲學家、園林美學家李漁的眼中,陜西的風土人情,人們的淳樸、好客,以及秦地的方言仍有著震撼心靈之處。他的小說亦與秦腔有一定文化上的緣分。
一、秦地獨特的壯美風光深深吸引了李漁
李漁游燕秦的往返路線為:京師—正定—山西平定州—平陽—蒲州—陜西潼關(guān)—長安—甘肅蘭州—涼州—甘泉—陜西涇陽—華山—潼關(guān)—河南陜州—汝寧(汝南)—江南徐州—江寧。秦地,特別是長安讓李漁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長安曾經(jīng)是十三朝古都,特別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兩個鼎盛時期漢代和唐代,所形成的獨特、豐富的文化樣態(tài)讓李漁大為欣賞,徜徉在長安的大街小巷,李漁發(fā)出了由衷的感嘆:“壯哉,長安!”看慣了江南的小橋流水,陜西的壯美景色深深地吸引了李漁。李漁在秦地游歷期間,攜家眷登上了以險著稱的西岳華山,并作《登華岳四首》[2]104-105抒發(fā)自己的豪情。
由于華山太險,所以唐代以前很少有人登臨。至唐朝,隨著道教興盛,道徒開始沿溪谷而上開鑿了一條險道,形成了“自古華山一條路”。華山以其峻峭吸引了無數(shù)游覽者,自隋唐以來,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留有詠華山的詩歌、碑記和游記不下千余篇,摩崖石刻多達上千處。李白登上南峰感嘆說:“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還有一個關(guān)于唐朝大文學家韓愈登華山而痛哭的故事。相傳當年韓愈被貶出京城,途中登上了華山。因華山蒼龍嶺處過于險要,韓愈無法下山而痛哭,并寫信投下山與家人訣別。后在華陰縣令派人接濟下,才得以下山。當然,有人亦指出韓愈在山上痛哭,并非因為害怕山勢險峻,而是因為華山之奇景難以形諸筆端,為此感到惋惜而哭。無論是哪種說法,都證明了華山是一座險要的山。但從江南來陜的李漁對以奇險聞名天下的華山則有著別樣的體驗。
《登華岳四首》《其一》云:“不必曾游過,名山故友同。終朝書卷上,徹夜夢魂中。思熟蒼龍徑,題殘玉女松。興由齠齔始,相對已成翁。”
《其二》云:華岳多奇巒,以蓮花、明星、玉女三峰為最。“五丁非愛力,妙在不須平。地是云鋪就,山由天削成。三峰奇入格,四岳幸齊名。自有昌黎哭,巉巖愈著聲。”
《其三》小序中說:“頂有落雁峰,家太白謂‘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一問青天’,即其所也,希夷峽,為陳摶蛻骨處。”詩云:“誰設(shè)扶人索,功高實可謳。升騰猶鳥捷,輕便若云浮。太白攜詩未,希夷入夢不?問天須及早,去此便無由。”
《其四》云:時家姬四人隨游,頗嫻竹肉,予令至青柯砰而止。諸姬目癢不肯息,視予所在,尾而從之。予上二索,彼上一索,相去只一間,雖怒訶不止。予嗔其頑劣,亦復(fù)許其清狂,遂聽偕行。襪敝鞋穿,無可更替,乃裂裙幅補綴復(fù)行。至谿壑稍平處,鋪氈坐飲,使之度曲。昔韓昌黎痛哭不得下,投書與家人永訣處,即予挾諸婢子高歌處也。及今三秦好事者,猶傳為話柄云。詩云:“怪殺登山勇,誰堪奈爾何。前賢猶痛哭,我輩卻高歌。鳥過停飛翼,樵聽罷斧柯。主人游興癖,從者盡成魔。”
李漁的這四首游華山詩,表達了不以為苦反以為樂的獨特感受,引起了很多人的好評和共鳴。如,王山史評道:“四首雋逸可人,為華岳諸詩之冠。”又評:“四詩惟登過華山者能知其妙,又惟登過華山而作過登華山詩者能知其好,不則以詞采見稱而已。”吳修蟾評其:“千古游記中未有之奇,為華岳另辟一洞天矣。”顧赤方評:“好婢子,赤松之玉女郎?秦宮之毛女耶?飛行之天女耶?”王左車評:“健句風生。”
從詩中可以看出李漁攀登華山時的情境。華山是險要的,眾女子“襪敝鞋穿,無可更替,乃裂裙幅補綴復(fù)行”,可見登山之艱苦。但李漁登山感受的卻只有樂而沒有苦,不僅隨從眾多,而且有剛剛得到的女子為他演曲助興,他一邊欣賞大好風光,一邊聽戲賞曲,李漁在輕松和愉悅中征服了險峻的華山,真是讓人羨慕。難怪郭九芝在評這幾首詩時說:“此有華岳以來第一韻事。有昌黎之痛哭,不可無笠翁之高歌,二事并傳,為后來作詩者增一佳偶。”
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中征服了華山,對于南方的一位文人來說,以為北方的環(huán)境也是和風細雨的,但在出潼關(guān)時,李漁卻遇到了瓢潑大雨,他沒有了“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雅致來欣賞,而是真正感受到了韓愈“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的無奈和焦灼。于是他作了一首《潼關(guān)阻雨》,[2]329詩云:“陸行何異在舟中,行止難憑計亦窮。莫德青山徒怨水,車輪也阻石尤風。”顧赤方評:“未經(jīng)道過。”是啊,在江南如畫的美景中生活慣了的李漁,怎見過如此疾風驟雨?瓢潑大雨幾乎將他乘坐的車子都浮起來,好像是在江南乘舟行一般。一向多才多思的他也發(fā)出了“計亦窮”的慨嘆。看來,在李漁的視野中,陜西的山是“高”而“險”,而陜西的風和雨也很有威力。陜西的風光與陜西文化都不愧“壯美”二字!
二、西北人的豪爽、熱情給李漁留下深刻印象
陜西不僅風光美,陜西人更是熱情好客,讓李漁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邀請人陜西巡撫賈漢復(fù)將李漁視為座上客,“館諸別宮,謬稱上客。”不僅如此,賈漢復(fù)還將李漁介紹給自己的屬下,“又復(fù)遍諭屬僚,交相拂拭,饑則齊推,寒則并解,食五侯之鯖而衣千狐之腋者,凡四閱月。”
賈漢復(fù)接待李漁不僅時間長而且極為周到,這讓李漁甚是感動。李漁在《寄謝賈膠侯大中丞》[3]169中表達了自己對賈漢復(fù)的感激之情:“晚漁一介庸儒,寡才鮮識,自分老死牖下,不望見知于當代名公卿矣。詎意明公謬耳虛聲,不緣介紹,特受弓旌于數(shù)千里之外,使得應(yīng)聘入秦……”“漁何人,而獲蒙此異數(shù)哉?亦大幸矣!”“拜別逾時,未陳謝悃,總以朝東西夕,身無定在。茲幸稅嫁甘泉,始克尋鴻覓鯉,一致感私。近遇西來之口,備言近履亨嘉,與時并懋;新公相得甚歡,督撫同心。此地方之福,三秦黎庶,可比戶而封侯矣。”“漁止皋蘭彌月,隨走甘山。地主情殷,不忍遽而言別,非夏杪秋初,不能旋轡。歸時直走涇陽,不復(fù)迂道奉謝,以混起居,只遣奴子叩首而已。先此告罪。不盡。”李漁眼中的陜西是百姓安居之樂土,三秦黎民百姓能遇上如此清明有作為的父母官是一件幸事。
賈漢復(fù)是一位很有思想和作為的官員。賈漢復(fù)(1605-1677)字膠侯,號靜庵,山西曲沃人。明時曾任淮安副將,入清,任工部右侍郎、河南巡撫,康熙元年以兵部尚書巡撫陜西。在明時曾保潼關(guān)有功。為官有作為,能為民謀福利。在任陜西巡撫時,免除宜川、延安、分州、白土關(guān)等貧困地區(qū)的部分錢糧;修葺褒城至寶雞的棧道,便利川陜交通;還捐資興修水利。在陜西任職期間,又組織人員重修《陜西通志》,還補刻了《孟子》石經(jīng),重修關(guān)中書院。
賈漢復(fù)賞識李漁的才華,李漁也深為賈漢復(f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于是李漁便寫了一首《華山歌壽賈大中丞膠侯》[2]59來為自己喜愛和崇敬的陜西巡撫祝壽,并贊美和歌頌了其政績。“太華峰高高插天,我游幾及升其巔。生平目力為之竭,迄今夢寐凌蒼煙。主其地者為誰氏?膠東再出名尤熾。先撫中州后撫秦,功與此山相并峙。棧道千年斷又連,五丁袖手蠶叢穿。蜀道最難今最易,六馬并進還游畋。西秦帖貴洛陽紙,十三經(jīng)惟缺《孟子》。公補全文續(xù)圣經(jīng),經(jīng)亡合出媧皇氏。秦俗驕悍鄰邊陲,風行草偃流亡歸。盡識小廉由大法,不使豺狼狐貍威。我昔謬充秦上客,侯鯖食遍公之力。大廈千間庇者多,其間雨露殊豐嗇。糜骨難酬國士知,焚香但祝摩天翼。遠作分茅萬里侯,近登賜履三公席。莫教髀肉老英雄,空貽四海蒼生戚。七年不進萬年觴,今日來歌天保章。仍指太華為公壽,功與同高歲與長。”許茗車評:“勁筆可匹華峰,贈言堪補聃語。以此詩壽此人,俱堪不朽。”詩中巧妙地將賈漢復(fù)的事跡嵌入其中。
為了報答賈漢復(fù)的知遇之恩,作為一位園林設(shè)計高手的李漁親自為賈漢復(fù)設(shè)計了園林——半畝園。在《贈賈膠侯大中丞》[3]257中李漁寫道:“公以絕大園亭棄而不有,公諸鄉(xiāng)人,凡山右名賢之客都門者,皆得而居焉。義舉也,僅事也,書以美之。”“未聞安石棄東山,公能不有斯園,賢于古人遠矣!漫說少陵開廣廈,彼僅徒懷此愿,較之今日何如?”
李漁將賈漢復(fù)及陜西其他官員的案牘文章收入《資治新書》中。賈漢復(fù)的案牘《察弊催糧檄》位列《資治新書》二集第一卷《文移部》的第二篇,陜西方伯顏澹叟及賈漢復(fù)兒子賈國楨等人的案牘亦收入其中,[4]擴大了陜西文化在全國的影響。李漁還給賈漢復(fù)送過一副壽聯(lián)《壽賈大中丞膠侯》[3]261“公茹胎齋,于冬至后一日初度。”其聯(lián)正文:“茹長齋于岳降之先,現(xiàn)一世宰官身,不但壽民兼壽物;祝大誕于陽生之后,聽四方歌頌語,才經(jīng)添線又添籌”。且不說作為著有《笠翁對韻》的寫對聯(lián)高手,李漁所寫的對聯(lián)如何工整,單就其所含深意,很難有人企及,正如許茗車在評此聯(lián)時所說的:(該聯(lián))“妙在移用不得,又使再贈聯(lián)者措筆不得。”
李漁還有一首《題西安旅舍》[2]110抒懷。他一生游歷了那么多地方,但對“游秦隴”一事卻多次提及,他言“唯有游秦收獲頗豐”。雖然在李漁眼中,秦地是不可能與富庶的江南相提并論,但讓他未曾料到的是卻不虛此行,用李漁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收獲頗豐。而這個“頗豐”到底是個什么情境呢?李漁在此次“游秦隴”過程當中,不僅受到了盛情款待,也得到了豪爽的陜西人的很多饋贈。在《秦游家報》中,李漁寫到:“此番游子橐,差勝月明舟。不足營三窟,惟堪置一丘。心隨流水急,目被好山留。肯負黃花約,歸時定及秋。”倪闇公評:“似杜老入秦州諸詩。”[2]111另有《游秦頗壯,歸后僅嘗積逋,一散無遺,感而賦此》,“入門諸事逼,萬有盡歸無。費盡終年力,難嘗積歲逋。買山更何日,托缽又窮途。贏得歸來夜,花間酒一壺。”[2]111從“惟堪置一丘”、“萬有”等語可見,李漁游秦歸來時還是囊中滿滿的。
三、李漁對陜西方言的評價
到過京城,走過很多地方,李漁聽慣了吳儂軟語和各色語言,突然聽到了“怒吼”的秦音,李漁在多年后回憶各地方言時,仍對秦地方言印象深刻:“難學呀!”在《閑情偶寄》的《聲容部·習技第四·歌舞》一節(jié)中,李漁提到了秦地方言:“九州以內(nèi),擇其鄉(xiāng)音最勁、舌本最強者而言,則莫過于秦晉二地。”
雖然秦音難學,但音韻修養(yǎng)甚高的李漁在短短的接觸中也發(fā)現(xiàn)了規(guī)律:“不知秦晉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無東鐘,晉音無真文;秦音呼東鐘為真文,晉音呼真文為東鐘。此予身入其地,習處其人,細細體認而得之者。”“秦人呼中庸之中為‘肫’,通達之通為‘吞’,東南西北之東為‘敦’,青紅紫綠之紅為‘魂’,凡屬東鐘一韻者,字字皆然,無一合于本韻,無一不涉真文。豈非秦音無東鐘,秦音呼東鐘為真文之實據(jù)乎?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朝訓夕詁,導(dǎo)之改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1]151-153
李漁認為方言給人們的交往帶來很多不便,“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辯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撲,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誤人,豈淺鮮哉!”“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聲音判如霄壤,或此呼而彼不應(yīng),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通過“改唇易舌”,“求為同聲相應(yīng)而后已。”
李漁認為大家只有在與外地人交流時,才能發(fā)現(xiàn)自己所說的是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為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為方言,及入他境,對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為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李漁還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告訴大家,我們要認識自己在說方言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李漁兒時讀《孟子》一書,其中有“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看到朱熹的注釋:“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存疑惑。因為李漁看到南方穿褐的人很少。即便有穿的人,那也多半是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為絨,怎么會是貧賤之人的衣服?李漁問自己的老師,他的老師也不知道,答案在游秦地時才找到。“及近游秦塞,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無論絲羅罕覯,即見一二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yǎng)自活。織牛羊之毛以為衣,又皆粗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其為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見其寬則倍身,長復(fù)掃地。即而訊之。則曰:此衣之外,不復(fù)有他,衫、裳、襦、褲,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為衾,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履其足。《魯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即是類也。”(《閑情偶寄·詞曲部·賓白第四·少用方言》)[1]53-54親眼所見才使李漁解開了謎團:“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所謂秦塞人的穿著而并非南方富人所衣。
認識到了方言的地域性和局限性,那么,該如何減少大家之間的交往障礙呢?李漁指出“予謂教人學歌,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既諳,使之學曲,可省大半工夫。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為學歌而設(shè),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為一方之士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在青云,有率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音,講求韻學,務(wù)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李漁說,應(yīng)“察其所生之地,禁為鄉(xiāng)土之言,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1]151-153李漁呼喚一種民族共同語的產(chǎn)生,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普通話,有了這種共同語,大家就可以增進彼此的理解。可見,陜西文化要走出陜西,走向世界,陜西人就要學習普通話和英語這些大家普遍認同的“共同語”。
結(jié)語
作為江南文人的李漁,一生著述頗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短篇小說集《十二樓》中的《奪錦樓》[5]36-50爾后被改編為同名秦腔劇,也悄然地將他與陜西的戲曲文化聯(lián)系了起來。李漁在秦地既收獲了禮遇、饋贈,又豐富了閱歷。他不僅獲得物質(zhì)上的滿足,秦地文化的豐富多彩也讓他受益匪淺,精神上得以充盈。李漁在陜西逗留數(shù)月,對以長安文化為代表的陜西文化印象深刻,在他的詩文中多次提及陜西的風土人情和人物,在登華山、出潼關(guān)時都有詩吟詠,他對秦地的方言也留下難忘的印象。西北特別是陜西人的淳樸、好客,讓李漁大為感動,他便以實際行動回饋,為時任陜西巡撫的賈漢復(fù)建造園林、寫感謝信、寫壽聯(lián),并將其與陜西其他官員的案牘文章收入《資治新書》中。李漁的小說也在秦地留下了印記,時至今日,還有與他的小說同名的秦腔名作《奪錦樓》。這一切都表明,李漁是一位與陜西文化有著深刻淵源的文化名人,他對長安文化的接受及其互動代表了南北文化的一種交融,在當今文化發(fā)展和文化繁榮中仍有一定的表率和借鑒作用。李漁對秦地風土人情的感受,他對此的評價也讓身在其中的秦人們更客觀、更真切地理解了自己的文化和所處環(huán)境的特色。
[1]閑情偶寄[M]//李漁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2]笠翁一家言詩詞集[M]//李漁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笠翁一家言文集[M]//李漁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資治新書[M]//李漁全集(第10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5]笠翁小說五種[M]//李漁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K825.6
A
1002-7408(2012)05-0098-0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0BZW060);陜西省教育廳基金資助項目(09JK279);咸陽師范學院專項科研基金資助項目(10XSYK105)。
趙海霞(1973-),女,陜西周至人,咸陽師范學院副編審,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及傳播學的研究。
[責任編輯: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