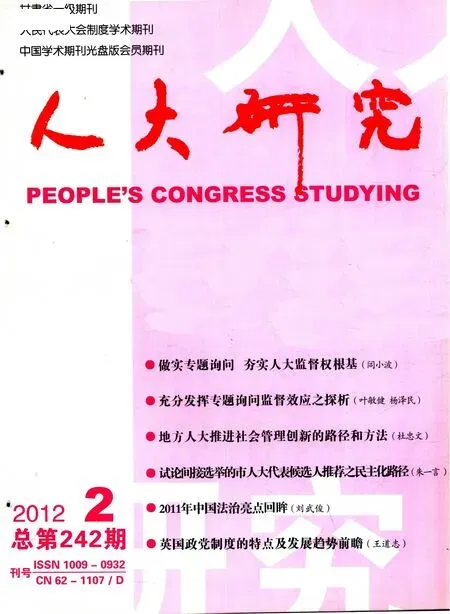做實(shí)專題詢問 夯實(shí)人大監(jiān)督權(quán)根基
□ 閭小波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所以作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只是因?yàn)檫@一制度設(shè)計(jì)使中國式民主在世界上占據(jù)了民主的道德高地,而在于憲法賦予人大擁有的四大權(quán)力:立法權(quán)、任免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及重大事項(xiàng)決定權(quán)。只有讓這四權(quán)循名質(zhì)實(shí),我們才有底氣稱其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否則將使權(quán)力系統(tǒng)跛足而行。如此行政,不僅使黨和政府權(quán)威與公信力流失,而且增加政府行政的風(fēng)險(xiǎn)和官員尋租的機(jī)會,乃至危及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地位。
2011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召開聯(lián)組會議,就國務(wù)院關(guān)于城鎮(zhèn)保障性住房建設(shè)和管理工作情況的報(bào)告展開專題詢問,全國人大網(wǎng)作了現(xiàn)場圖文直播。受國務(wù)院委托,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shè)部、國家發(fā)展改革委、財(cái)政部、國土資源部、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jiān)會等相關(guān)部委負(fù)責(zé)人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牟新生、吳啟迪等10余位委員就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設(shè)計(jì)、保障范圍、建設(shè)進(jìn)度、資金保障、分配管理等人民群眾普遍關(guān)心的問題提出詢問,相關(guān)部委負(fù)責(zé)人一一作了回答。11月25日,河南省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召開聯(lián)組會議,專題詢問全省保障性住房建設(shè)情況,河南省副省長趙建才率領(lǐng)8個相關(guān)政府部門負(fù)責(zé)人到會,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問詢一一給予明確答復(fù)。同日,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也首次啟動“專題詢問”,來自6個部門7位領(lǐng)導(dǎo)就保障房建設(shè)接受委員們詢問。媒體在報(bào)道此事時圖文并茂,并用了“副省長起立作答”、“開門見山、直截了當(dāng)”、“你來我往”、“面對面考問”的字樣,表明社會對各級人大加強(qiáng)對“一府兩院”的監(jiān)督有著強(qiáng)烈的期盼。
詢問,本是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一府兩院”最低度的監(jiān)督。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專題詢問,是在舉國、朝野高度關(guān)注住房,而各級國家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人民代表大會)一直失語的情形下出現(xiàn)的,故而引起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guān)注,也使得人大代表問責(zé)于政府這一早在“五四憲法”就有規(guī)定(“質(zhì)問”,“八二憲法”改為“質(zhì)詢”)、實(shí)踐中也曾行使過的監(jiān)督權(quán)(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北京團(tuán)代表就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資最大的“上海寶鋼工程建設(shè)問題”向冶金部提出質(zhì)詢)再次進(jìn)入公眾的視野。
其實(shí),現(xiàn)行憲法中并沒有“詢問”一詞,憲法第七十三條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組成人員在常務(wù)委員會開會期間,有權(quán)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提出對國務(wù)院或者國務(wù)院各部、各委員會的質(zhì)詢案。受質(zhì)詢的機(jī)關(guān)必須負(fù)責(zé)答復(fù)。”詢問作為法律用語,首次出現(xiàn)在地方組織法第二十九條:“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議案的時候,代表可以向有關(guān)地方國家機(jī)關(guān)提出詢問,由有關(guān)機(jī)關(guān)派人說明。”2007年1月1日實(shí)施的監(jiān)督法第三十四條作出更為具體的規(guī)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會議審議議案和有關(guān)報(bào)告時,本級人民政府或者有關(guān)部門、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應(yīng)當(dāng)派有關(guān)負(fù)責(zé)人員到會,聽取意見,回答詢問。”在質(zhì)詢前面加上詢問,其實(shí)是為質(zhì)詢增設(shè)了一道門檻,也可謂是在“議”與“行”之間劃出一個緩沖地帶。這一制度設(shè)計(jì)符合中國走漸進(jìn)主義政改的思路,但若要使這一良好的思路走通,必須做實(shí)專題詢問,否則將使“思路”變成“死路”。
監(jiān)督法實(shí)施以來,何時、誰先啟動詢問受到人們的關(guān)注。中國的各級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并無上下級的領(lǐng)導(dǎo)關(guān)系。啟動詢問,各級人大常委會機(jī)會均等。在上世紀(jì)90年代,破冰啟動質(zhì)詢的是地方人大。如1998年浙江德清縣、1999年遼寧省以及2000年廣東省人大或常委會均啟動過質(zhì)詢,而同期全國人大或常委會并未啟動質(zhì)詢。此次率先啟動詢問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0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bào)告中提出“依法開展專題詢問和質(zhì)詢”。同年6、8和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就“中央決算”、“國家糧食安全”和“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進(jìn)行了3次專題詢問。同年,部分地方人大迅速“復(fù)制”,上海市、湖北省和安徽省也開展了專題詢問。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計(jì)劃進(jìn)行4次專題詢問,計(jì)劃開展專題詢問的省級人大常委會增至18個。現(xiàn)在的問題是,已經(jīng)上路的詢問將以什么速度穩(wěn)步走下去,夯實(shí)人大行使監(jiān)督權(quán)的根基,并盡快改變跛足的權(quán)力運(yùn)行結(jié)構(gòu)?
首先,制定規(guī)范專題詢問的議事規(guī)則。開會欲收實(shí)效,必須遵循明確而合理的議事規(guī)則。在監(jiān)督法頒布實(shí)施之前,地方人大廣泛開展了述職評議,并制定了相應(yīng)的議事規(guī)則或條例,對“促進(jìn)行政機(jī)關(guān)、審判機(jī)關(guān)、檢察機(jī)關(guān)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探索地方人大監(jiān)督制度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有益的影響”。監(jiān)督法實(shí)施后,各地紛紛廢止議事規(guī)則。2007年,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廢止1996年12月24日通過施行的《四川省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評議工作條例》的原因時,“有關(guān)人士指出,述職評議在實(shí)踐中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監(jiān)督法未作規(guī)定;而條例有關(guān)工作評議的規(guī)定又與監(jiān)督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在監(jiān)督主體、監(jiān)督程序和法律責(zé)任等方面存在不一致,為保證監(jiān)督法在我省順利貫徹實(shí)施,有必要廢止條例。”[1]要使專題詢問收到實(shí)效,不僅要確立社會普遍關(guān)注的有價值的議題,更要對詢問議題的確立程序,詢問前的準(zhǔn)備、聯(lián)組會議上的詢問者與到場的詢問對象、詢問過程(包括問答的時間、次數(shù)等)以及詢問后政府的回應(yīng)作出極其嚴(yán)格的規(guī)定,為此,全國人大應(yīng)率先垂范,制定“全國人大常務(wù)委員會專題詢問議事規(guī)則”。
其次,增加專題詢問的頻次。當(dāng)下中國在快速發(fā)展的同時,各類問題也成增生之勢。執(zhí)政黨面臨著“四大考驗(yàn)”(執(zhí)政考驗(yàn)、改革開放考驗(yàn)、市場經(jīng)濟(jì)考驗(yàn)、外部環(huán)境考驗(yàn))、“四個危險(xiǎn)”(精神懈怠的危險(xiǎn)、能力不足的危險(xiǎn)、脫離群眾的危險(xiǎn)、消極腐敗的危險(xiǎn)),凡此,迫切要求各級人大加大對“一府兩院”尤其是政府的監(jiān)督,促使政府執(zhí)政為民、依法行政、防止腐敗。就全國人大常委會而言,應(yīng)使專題詢問成為每兩個月一次的常委會的規(guī)定議題,必要時還可就專題詢問增加常委會開會的次數(shù)。這樣,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示范,帶動地方人大常委會加大對政府監(jiān)督的力度。人大系統(tǒng)忙碌起來,中國的民主也就能有效地運(yùn)轉(zhuǎn)起來。
第三,盡快啟動質(zhì)詢。憲法賦予各級人大的質(zhì)詢權(quán)在實(shí)際的政治過程中已懸置多年,詢問其實(shí)只是一種最為低度的監(jiān)督,擱置質(zhì)詢,僅有詢問,不足說明人大享有充分的監(jiān)督權(quán)。憲法賦予的權(quán)力若長期不行使,無異于瀆職。當(dāng)然,也不是為質(zhì)詢而質(zhì)詢,使質(zhì)詢成為形式。事實(shí)上,當(dāng)下中國,有太多的議題需要人大向政府質(zhì)詢,否則無法解釋不斷上升的政府高官違法、貪腐案例。反之,若各級人大自主地啟動質(zhì)詢案,許多大案要案雖說不能完全杜絕,但至少可以減少發(fā)案率。
當(dāng)下中國已經(jīng)步入一個高風(fēng)險(xiǎn)的社會,隨著信息技術(shù)的快速發(fā)展,使得微博時代網(wǎng)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呈爆炸性增長的趨勢。網(wǎng)上的泄憤雖然不像廣場政治呈現(xiàn)出可以刺激人眼球的物理形態(tài)意義上的抗?fàn)帲鋵φ蜗到y(tǒng)沖擊力卻比廣場泄憤更大。網(wǎng)民的意見其實(shí)只是碎片化的民意,但若不將其引入到具有法律意義上的民意并納入政治過程,將無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對話、政治妥協(xié)與政治共識,而作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在法定的制度框架內(nèi)對政府部門或官員提出詢問、質(zhì)詢,才是形成政治共識的有效渠道。
注釋:
[1]《叫停述職評議》,載《四川日報(bào)》2007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