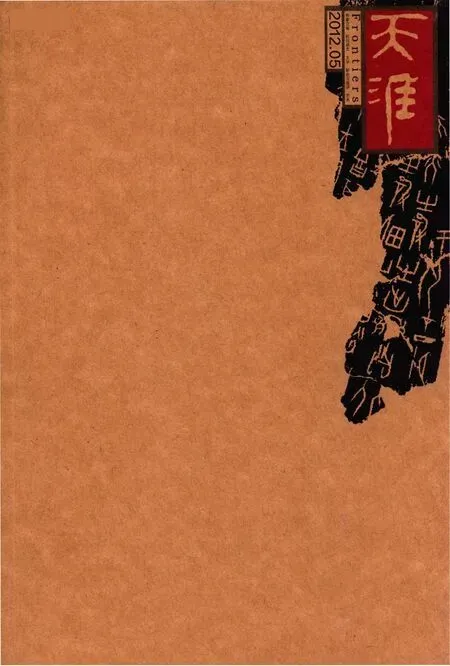新人文主義的建構
胡水君
新人文主義的建構
胡水君
一般來說,從人出發,以人間事務為中心,以人的道德、能力、尊嚴和自由發展為價值準軸,重人力和人事而輕宗教,是人文主義的基本特質。從文化比較的角度看,人文主義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中西之別。
西方人文主義構成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經過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之后形成的現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如果把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作為西方文化的第一個發展階段,中世紀的希伯來宗教文化作為西方文化的第二個發展階段,那么,西方人文主義可被視為西方文化的第三個發展階段,它至今已經歷近五百年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文主義是對中世紀宗教文化的一次否定。盡管它也表現出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回歸,但它與古希臘羅馬文化也存在很多差別。對于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中國來說,西方人文主義可謂對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化形態。
大體而言,西方人文主義表現出這樣幾個基本特點。一、擺脫宗教和神的束縛,從人出發并以人為中心來觀察、思考和界定世界。二、承認意志自由,充分認可人的能力和尊嚴。三、扎根于自然世界和人的自然本性。四、在認知上,以人的經驗和理性為判斷根據。在西方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宗教文化逐漸走向衰落,歷史上以宇宙秩序以及宗教、道德或自然義務為基點的倫理政治,最終轉變為從“自然權利”出發的自然政治,旨在保護人權和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因此得以建立。不過,與以往古希臘、羅馬文化以及中世紀的宗教文化對照起來看,西方人文主義也實際促成了自然權利與“自然法”以及神法的斷裂、“意志自由”與“自然道義”的斷裂、權利主體與德性主體的斷裂、道德精神與民主法治的斷裂。可以說,在造就現代政治法律文明的同時,西方人文主義附帶著與之相關的“現代性”問題,如“自由帝國主義”、“做錯事的權利”等,它因此也需要探尋新的出路,并不足以被視為一種終極的、更高級的乃至最高級的文化形態。
如果說,西方人文主義主要立足于人的身體、生理本性以及認知理性,那么,與之相對照,中國人文主義則一直表現出以人的道德精神、道德本性以及道德理性為基礎。立足點或出發點的不同,使得中西人文主義呈現出發展路徑的差異,這種差異并不能因為西方在現代的一時強勢而被簡單地歸結為發展層級的高低之別。中國人文主義大致形成于周代,一直持續至今,但在近一百多年里受到西方人文主義的巨大挑戰。
大體而言,中國人文主義表現出這樣幾個基本特點。一、非宗教性。在以儒教、道教、佛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中,缺乏作為“第一主宰”的上帝觀念,人自身一直被認為具有超凡入圣的超越性。因此,中國人文主義有時也被人稱為“超越宗教的宗教”。二、內在超越和主體性。人被認為是天然具有善性、神性和佛性的主體。人與神、佛之間并沒有嚴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也不是上帝與選民的關系。只要努力,“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成佛。這是一種道德上的意志自由,它意味著人經過自身的努力可以改變在塵世的命運,而且這種能力是人本身完全具備的。三、公共責任。中國文化中有一種源遠流長的“天地萬物為一體”、所有的人都與己相關的觀念,并由此生發出“民胞物與”、“四海一家”的道德情愫。每個人被認為對天下人都負有仁慈的道德責任,而此種道德責任的實現實為人之為人的基本要素。四、德性認知。在經驗和理智之外,中國文化中還包含著一種獨特的“德性之知”。它是人在可感知的自然世界之外發現同樣對人具有實際制約作用的道德世界、發現自身的道德“良知”的基本認知途徑。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文主義所表現出的這些基本特質,盡管遭受西方人文主義的劇烈沖擊,而且在構建現代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方面顯得力不從心,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它們對于重建現代人的價值系統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在“古今中外”的時空背景下,現時代有必要結合中西人文主義之精華來形成一種新的人文主義。這樣一種新人文主義旨在實現生理本性、認知理性、見聞之知、自然權利、民主法治與道德理性、道德本性、德性之知、“自然正當”、道德精神的銜接或匯通。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的政治和法律發展道路之時,尤其需要這樣一種融會古今中外智慧的新人文主義,以為其構建民主法治國家及其未來發展設定合理的理論基礎。
回顧歷史,不難看到,二十世紀是中國文化屢遭摧殘、飽經風霜的一個世紀。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國傳統文化被長期置于“古今中外”和“海陸黃藍”的簡單對比結構中,由此形成了一種錢穆所說的“惟分新舊,惟分中西,惟中為舊,惟西為新,惟破舊趨新之當務”的文化觀。在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中,中國傳統文化更是遭受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否定,終致飄搖破敗、花果凋零。可以說,在現實政治和西方文化的雙重沖擊下,政治形勢、社會功利乃至群情激奮明顯蓋過了對于根本道理的終極追問。
這種狀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發生了一些改變。近二十年,是“冷戰”結束后文化獲得相對平穩發展的一個歷史時段,其間不僅相繼出現“國學熱”、“人文精神”討論、“傳統文化復興”等文化事件,而且,現代“人權”和“中華文化”在國家層面都得到了明確認可。在文化和理論界,一種試圖彰顯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文化自覺”正在興起,立足普遍因素來承接融會“古今中外”、沿著中國文化理路來開拓中國的政道法理的文化姿態也日趨明顯。總體來看,如果說中國近一個半世紀是外來文化大勢涌入的“低谷”時期,那么,經歷近二十年乃至以后更長的時期,中國文化可望以其擇善處下、兼收并蓄而重現“百谷王”的態勢。
在此現實條件和趨勢下,沿著自身的文化理路、歷史脈絡和社會現實來重構據以長遠發展的道統、政統、法統和學統,可謂近代以來的中國至為基本的歷史任務。套用中國“內圣外王”這一傳統理論框架,此任務歸根結底涉及的是“內圣”與“新外王”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是人的道德精神與民主法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的關系問題。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一個與“現代性”密切相關的普遍問題。在通向現代民主憲政的道路上,是完全舍棄“內圣”來開“新外王”,抑或與傳統思路一樣秉承“內圣”開“新外王”,還是在“內圣”與“新外王”之間建立某種共生并濟的外在銜接,是這個時代迫切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完成現時代的歷史任務,至少需要從價值、政制、法律、學術,或者,道、政、法、學四個方面作根本考量。
在價值方面,需要處理好道德精神與自然權利的關系。自然權利,是現代政治和法律道路的新的出發點,也是西方人文主義在價值層面的集中表現形式。從自然權利出發的現代政治,明顯有別于以德性或道德、宗教義務為基點的傳統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現代權利政治在有效保障人權和個人自由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與“現代性”相關的政治和道德問題。就政治而言,權利發展在國內層面與現代國家權力的精微伸展相伴隨,在國際層面則與“自由國家主義”乃至“自由帝國主義”相伴隨,這使得人權保障在全球范圍仍然面臨現實困境。就道德而言,在“意志自由”以及“無害他人”的自由主義原則的主導下,權利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伴隨著人的道德精神的衰落,由此呈現出一定的道德危機。在這些方面,中國人文主義表現出廣闊的作用空間,中西人文主義之間也呈現出實現歷史結合的可能性。從中西人文主義相結合的觀點看,現時代正可以也需要同時立足人的生理本性和道德本性,來重構現代民主法治、權利政治的道德根基,開拓一種作為道德責任或義務的人權,實現同為普適之道的人權與德性的融合或銜接。如此,既避免單純從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理性出發而抑制人的生理本性和認知理性,乃至抑制自然權利和民主法治生發的傳統倫理道路,也避免單純從自然權利出發而完全剝離人的道德精神的“單向度的”現代發展道路。事實上,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自然權利與自然法、自然權利與自然正當之間的縫隙或斷裂,在西方被更多也更深刻地意識到,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重構人權和權利的道德根基的歷史需要。倚重豐厚的道德人文資源,實現道德精神與自然權利的歷史銜接,對于處在發展中的中國來說,構成了一種歷史機遇。
在政制方面,既需要處理好“道”與“政”的關系,也需要處理好“政”與“治”的關系。中國傳統政治被梁啟超、錢穆、牟宗三等人,或者判定為有“道”無“政”,或者判定為有“治道”無“政道”。“政”與“道”、“政”與“治”之間的關系在當前仍可謂中國政治發展的兩個關鍵。從“政”與“道”的關系視角看,現代政治并不扎根于仁義道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非道德乃至反道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主要表現為一種自然政治。此種政治迥異于道德與政治同構的中國傳統政治,也與秉承內圣開外王的傳統政治哲學背道而馳。就近一百多年的近代進程而言,構建和完善現代民主之“政”仍構成中國的重要歷史任務,而在此過程中,如何將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重新結合起來,實現民主政治與仁義道德在當代的融合或銜接,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理論問題。從“政”與“治”的關系視角看,盡管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但民主政制的構建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長期被擱置,對“治”理的擅長在很大程度上也減弱了對民主之“政”的需求,由此長期存在著一種以“治”統“政”的格局。就此而言,如何從社會“治”理最終轉向民主之“政”,實現現代民主政治與傳統民本治理的合理結合,也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中國語境下的“道”與“政”以及“政”與“治”這兩層關系,與中西兩種人文主義有著內在關聯。如果說,政制意義上的民主政治主要是與西方人文主義相聯系的歷史現象,那么,中國人文主義在歷史上則更多地體現于治道與治理兩個方面。就此而言,無論是在“道”的方面實現自然權利與自然正當的結合,還是在“政”的方面實現民主政治與仁義道德、民本治理的銜接,都需要在中西兩種人文主義之間做出協調和融會。
在法律方面,需要理清“法治”的道德、功利、治理、政制四個層面,并擺正四個層面的關系。從中國自古以來文治武功的實際發展看,法治在中國大致出現過三種歷史形態。一是作為武功的法治。這是人們所熟知的法家法治,它以嚴刑峻法、信賞必罰、通過法律追求國家富強為重要特征。二是作為文德的法治。這在歷史上主要為儒家所主張。儒家法治的精髓在于“德主刑輔”,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把法律放在第二位。三是作為憲政的法治。這是以通過政治和法律制度設計來有效約束和規范國家權力或政治權力,保障人和公民的權利為基本特征的民主法治,也是中國近代以來努力尋求建立的一種法治。如果以道德、功利為縱欄,以政制、行政為橫欄,那么,大體可以說,作為武功的法治是一種功利、行政層面的法治,作為文德的法治是一種道德、行政層面的法治,作為憲政的法治或民主法治是一種功利、政制層面的法治,也可以說是“新外王”層面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儒家法治蘊涵有中國人文主義的要素,而民主法治起初則是主要在西方人文主義的基礎上建立的,它以啟蒙時代以來的現代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為理論基礎。從這樣一種比較看,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法治忽略了道德層面,而法家法治和儒家法治則忽略了民主政制層面。中國目前的法治實踐,事實上融合了這三種法治的某些特點。同民主之“政”相聯系,現代中國的要務正在于拓展政制層面的法律,著力打造中國自古以來長期缺乏的政制層面的法治。而在此過程中,法治各個層面之間的關系也是需要理清和協調的,以使一些傳統的治理和道德因素也得以涵容于作為憲政的法治之中,發揮其積極功效。在形成中國法治道路的過程中,從政治或憲制層面建立起民主法治是首要的,同時,為避免重走法家法治的老路、防止西方人文主義的某些“現代性”后果,在新人文主義的基礎上加強道德對政治和行政的影響、實現道德精神與民主法治的現代連接也是必要的。
從新人文主義的視角看,現時代需要一種新的法治理論——法治的道德理論。熟為人知的是,道德在現代社會與政治、經濟、學術等系統發生了很大分化,這種分化也發生在道德與法律以及權利之間。講法治的道德理論,并不意味著通過法律來強制執行道德倫理,或者像歷史上所做的那樣,通過政治和法律力量來建立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和倫理秩序,而是要在道德精神與民主法治之間建立連接。具體來說,受西方人文主義影響的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構成了民主法治的理論基礎,它是立足于人的身體、自然本性和認知理性建立起來的;而按照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政治必須基于人的道義、道德本性和道德理性來構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從“內圣”開“外王”。在新人文主義語境下,這樣兩套政治思路可以結合起來,也就是同時立足人的認知理性和道德理性來構建民主法治。一方面,基于人的身體,建構權利主體、市場法則和憲政制度,另一方面,基于人的道義,建構德性主體,建立以人的道德精神為核心的價值系統,并由此讓道德通過作為德性主體的人在市場競爭、民主法治以及國際政治中發揮積極功效。這樣有助于把人從權利角逐、市場競爭、政治斗爭和法律糾紛中解脫出來,使民主法治成為精簡有效機制,同時也有助于人找尋到生命的終極意義,成為真正的主體,使法治成為蘊含人的道德精神的法治。
在學術方面,尤其需要協調好“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關系。近代以來的中國學術,明顯有一個從“德性之學”、“通人之學”轉向“專門之學”,從“六藝之學”、“四部之學”轉向“七科之學”的歷史變遷過程。在此過程中,科學知識以及科學認知方式明顯占了上風,以至于價值和道德領域也受到了并不完全適用于該領域的科學認知方式的影響乃至支配。在現代社會,欲重建現代人權、民主、法治以及現代學術的道德和精神基礎,首先必須區分“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及其各自適用的領域,以使價值系統和知識系統并行不悖。就此而言,重開中國的學統,未必意味著從中國的道德知識體系中開出科學,而在于在現代科學研究中,存留并發揚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德性認知”方式,由此為開辟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提供可能,也為在現代民主法治體制下弘揚中國文化所蘊涵的道德主體精神、公共責任精神和內在超越精神創造條件。
胡水君,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政治分析》、《法理學的新發展:探尋中國的政道法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