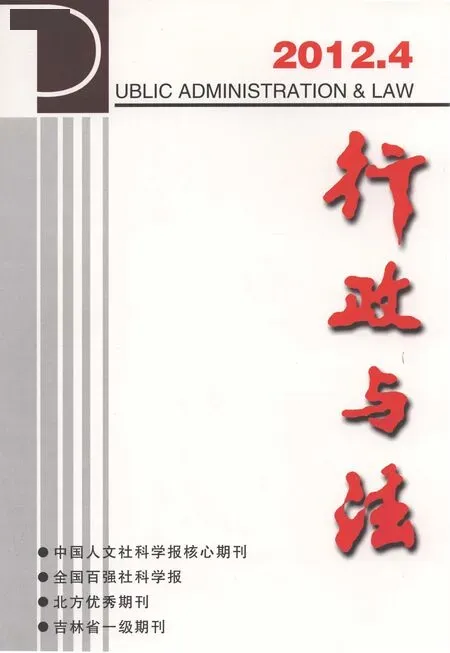城管執法的權威與困惑
□ 王洪芳,李 錚
(四川警察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
城管執法的權威與困惑
□ 王洪芳,李 錚
(四川警察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
當前,我國城管執法問題凸顯。加強并完善城管立法,合理配置城管執法的職責權限,回歸城管機構的行政機關性質,明確城管執法人員的公務員身份,既是合理有效回避城管執法現實尷尬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是積極、正確應對城管執法難題的當務之急。
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城管執法;困惑;權威
現代行政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正在進行著 “從搖籃到墳墓”式的全方位管理,政府行政的理念已經摒棄了“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之傳統,正沿著“能提供更多服務的政府才是更好的政府”之時代方向變遷,百姓不僅要求政府把社會管理好,還期盼政府能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謀求更多的福祉。盡管“小政府、大市場”已然確立了在一個國家中“官、民、市場”各有分工、融洽相處、和諧發展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行政權的作用范圍和作用力度仍在一定程度上呈現擴張和深化之勢,學界做出的“我國目前階段的行政權處于‘積極行政’的狀態”之結論并不為過,[1](p11)而城管執法正是這種“積極行政”的結果。
一、城管執法的法律和現實意義
(一)城管執法是我國法律確立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必然結果
一直以來,在行政權的積極作用過程中,我國行政管理存在“多頭執法、職責交叉、重復處罰、執法擾民”等問題,執法效果也不盡如人意,這些問題在城市管理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鑒于“七八頂大蓋帽管不住一頂破草帽”之現實揶揄,1996年3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16條確立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我國城管執法的產生正是得益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確立。
所謂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是指將若干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集中起來,交由一個行政機關統一行使,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后,有關行政機關不得再行使原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確立和實施是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需要,它對于提高行政執法水平和效率,降低行政執法成本,建立“精簡、統一、效能”的行政管理體制,解決行政管理中長期存在的多頭執法、職權交叉、重復執法、行政執法機構膨脹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為了貫徹實施該制度,1996年4月,在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知》中指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認真做好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工作,……”據此,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在北京等城市進行試點,隨后,國務院又下發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和《關于繼續做好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進一步明確規定了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相關要求。在此過程中,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作為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一種重要形式,也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廣,可以說,“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確立,催生了城管的誕生與發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建立和實施過程即是城管部門的產生和發展過程”。[2]
(二)城管執法是我國城市管理的現實需要
城管執法作為我國政府應對和解決現代城市管理問題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手段和方法的總稱,其作用的產生主要源自政府對以“健康衛生、整潔有序”等目標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管理秩序的積極追求,以及市民對以“安全安定、清靜宜人”等標準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管理秩序的迫切需求;其作用的范圍主要有針對城市管理中的有關市容環境、規劃、城市綠化、市政、環境保護、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等行政管理事務;其作用的手段主要是采取柔性的勸導說服、批評教育以及剛性的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其作用的法律依據主要在于《行政處罰法》規定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其作用的目的是重在規范和提高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的效率和水平,充分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切實加強城市管理和服務。必須肯定,城管執法的存在,不僅緩解了無證經營、以街為市、亂搭亂建、占道停車等城市頑疾,還相對有效地解決了行政機關多頭執法、重復處罰、效率低下等問題,在加大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服務水平、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滿足百姓在城市生產和生活的多元需求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城管執法不能回避的現實尷尬
然而,城市管理作為一項需要對城市的一切活動進行政治、經濟、社會和市政等全方位管理的復雜系統工程,其對管理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法治性的要求隨著我國城市發展步伐的日趨加快而與日俱增。
城管執法是現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城管則是現代城市管理的生力軍,一方面,文明、整潔、有序的城市秩序離不開城管的執法管理與服務,但是城管所面臨的問題大多是城市管理中的復雜、尖銳、棘手的問題,面對的執法對象多為下崗工人、無業游民等生活困難、缺乏保障的弱勢人群,被管理者的多元利益訴求常與城市執法所追求的一元目標以及具體要求不相協調甚至矛盾或背離,這些客觀困難的存在使得城管執法常常處于因各地政府所要追求的城市管理目標不能無縫對接市情民生的現實需求而產生堆積起來的矛盾交織中,城管執法不被理解、接受,甚而遭遇敵視乃至抗拒,由此,“暴力抗法”現象在很多地方不斷出現。另一方面,城管從上個世紀末產生至今,國家一直沒有制定出臺專門的法律法規對其執法活動進行規范,城管長期性地“借法執法”,執法活動經常性地面臨“師出無名”、“底氣不足”之質疑。同時,法律規范的缺失必然帶來法律監管的缺位,城管執法頻頻暴露出執法違法、執法不當等問題,“暴力執法”也成為部分行政相對人心目中城管執法的代名詞,我國各地城管執法面臨著一系列不能回避的現實尷尬。
(一)各地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不盡統一
城管是在日趨加快的城市化進程中,根據《行政處罰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法律規定,應地方政府解決日漸紛繁復雜的城市管理問題而成立的一種執法機構。縱觀我國當前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多以地方政府規章、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為主,其在“法律位階”上的依據除了《行政處罰法》第16條針對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所做的總括性規定外,并無全國統一適用的法律規范,即使地方性法規也為數不多,且呈現出執法依據各自為陣和法律位階的低層次性特點。城管執法依據的不完善,無疑會讓城管執法權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的規范和控制,而對于城管執法權威的樹立也是有所削弱甚至損傷的。
(二)各地對城管執法職權范圍的劃定不盡相同
城管執法管理的事務具有典型的城市區域特征,由于各地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各自為陣,故而各地對城管執法職權范圍的劃定也不盡相同,不像其他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具有全國統一性的特點。
據統計,目前全國有400多個城市開展了城市管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其中,多數城市根據國務院國發[2002]17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決定》的規定,重點在市容環境衛生、城市規劃、城市綠化、市政、環境保護、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管理以及其他適合綜合管理的領域,合并組建綜合執法機構,在執法的職權范圍上實行“7+1”模式。①依據國發[2002]17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決定》的規定,我國城管執法的職權范圍由七類確定的職能和一個兜底條款構成,即所謂的“7+1”模式。隨著城管執法在全國范圍的不斷推廣,有的地方在城管執法職權范圍上則實行“4+1”模式或者“10+1”模式。
(三)各地對城管執法機構的稱謂、性質和執法人員身份的規定不盡一致
城管是城市管理中行使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機構,從對《行政處罰法》第16條“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的規定理解來看,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機構應為行政機關,國發[2002]17號文件進一步明確:“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應作為本級政府直接領導的一個獨立的行政執法部門,依法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城管作為各地政府應對城市管理需要而設立的執法機構,理應作為本級政府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一個行政機關而設立存在,但是,各地城管執法實踐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在稱謂上,城管執法機構在全國范圍內沒有統一的名稱。有的地方叫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例如北京;有的叫城管執法局(大隊),例如上海;有的叫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例如廣州;有的叫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例如成都;還有一種可能出現的最新稱謂叫城市行政執法部門,例如四川。②《四川省城市行政執法相對集中處罰權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第3條:“城市行政執法部門是本級人民政府設立的行使城市行政執法相對集中處罰權的行政機關,依法獨立履行職責,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其次,在城管執法機構的性質上,目前主要表現為三種:一是作為當地政府職能部門之一的行政機關,二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三是事業單位。未能形成與其職能履行相適應的、統一規范的執法機構。城管執法機構性質的不同決定了其執法人員身份的差異。在城管執法人員的身份確定上,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的則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再次,城管在省級以上政府中并不像國內其他行政機關一樣擁有對口的行業主管部門,這在我國法定和慣行的“國——省——市——縣(區)”四級政府行業管理體制中實屬罕見。與此同時,城管也就自然而然地回避了來自于上級政府的必要約束和監督。這種狀況極易縱容城管因隨性膨脹成為城市管理中的權力野馬而難以馴服。
三、城管執法權威的樹立
在我國當前城市管理中,城管執法存在的正當性在于各地政府對城管執法存有的借助于城管執法之手,以達到管理城市、服務于民的理想和預期。由此,每一個城管執法機構和執法人員都應當成為城管執法權的嚴格實施者和忠誠捍衛者,不能對手中的權力有所圖謀或者恣意妄為,而每一個生活、學習、工作在城市中的人都不僅有權成為城市管理成果的受益者,而且也有義務成為城市管理成果的自覺維護者和城市管理行為規范的模范遵守者,“城管”不應成為“暴力執法”的代名詞。
筆者認為,把握和順應我國大力提倡和踐行的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脈搏,完善并健全城管立法,合理配置城管執法的職責權限,回歸城管執法機構的行政機關性質,明確城管執法人員的公務員身份,既是合理有效回避城管執法現實尷尬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是積極、正確地應對城管執法難題的當務之急。
(一)厘清城管立法思路,確保城管執法有法可依
依法行政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和重要環節,其基本要求在于“權自法出、法律優先、法律保留、行為有據、程序規制和司法審查”,[3](p36-38)其中“行為有據”不僅要求行政行為應有事實根據,而且要有法律依據,旨在強調行政權的行使必須做到“有法可依”。
當前,我國各地城管執法呈現出“依據不足、分散立法”的狀況,故而加強城管立法,提高城管執法依據的位階,完善城管執法程序就成為破解城管執法困境的首要舉措。
在完善城管立法的過程中,專家們普遍認為,突破當前城管執法分散立法的局限,統一全國城管立法實乃現實所需,且勢在必行,但同時大家也客觀地指出,目前統一城管立法的時機尚不成熟。馬懷德教授認為,“雖然目前由于涉及行政體制改革等問題,城管立法還受到一些客觀條件的限制,但沒有法律依據,城管部門終究難以更好地完成工作。如果條件不成熟,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待條件趨于成熟后,還是應該及早出臺全國統一的城管法。”[4]
筆者認為,在統一城管立法短期內難以實現,而城管執法又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城市管理現實所需之下,著眼于未來全國性城管立法的統一規范,立足于各地城管立法的科學完善的確不失為當前的務實之舉。
(二)通過城管立法,科學設定和細化城管行政處罰權
環顧我國各地城管的執法范圍,既有“7+1”模式,也有“4+1”模式,還有“10+1”模式,其中在“7+1”模式中,主要涉及城市規劃管理、市容環衛管理、市政公用管理、城市園林綠化管理、環境保護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處罰權,而在“10+1”模式中,還增加了對國土、水利漁業和煙花爆竹管理方面的行政處罰權。[5]不同模式的選擇,一方面固然是各地城管執法實際的現實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各地城管執法在職責權限設定方面的困惑和迷茫。
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的確立是城管執法的基本依據,因而行政處罰自然成為城管執法的主要方式,但根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 “應當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城管執法既不能單純地以罰代管,也不是簡單地只罰不教、重罰輕教,而應通過處罰的方式達到預防、糾正違法行為,教育行為人不再違法和引導社會公眾自覺守法的目的。要充分實現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僅僅賦予城管概括籠統的相對集中處罰權是不夠的,必須通過全國性的城管統一立法和地方分散立法的途徑,合理配置城管執法權力,對可以交由城管相對集中行使的行政處罰權的范圍進行科學的設定和細化。
(三)以《行政強制法》為依據,合理規范和控制城管執法所需的行政強制權
“城管執法是將以行政處罰權為中心的執法權進行集中,減少和避免行政執法權之間的交叉重復。”[6]在城管執法中,行政處罰權是城管執法權力的核心,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行政處罰作為針對行政違法實施行政管理的一種結論性處理手段,并不是每一樁、每一件、每一次城管執法的必經環節和必然選擇,因而立法單單賦予城管行政處罰權還遠不能適應城市管理的需要以及對城市管理問題的解決,在科學設定、細化城管行政處罰權的基礎上,還需賦予城管執法實效得以有效發揮的其他管理權限,例如合理規范和控制行政強制權。
在行政強制的適用過程中,亂用、濫用行政強制和行政強制手段不足一度成為長期困擾我國行政強制的兩大問題。就城管可采用的行政強制措施而言,除了暫扣權和強制拆除權以外的權力是相當有限的,因而無法有效滿足城管執法的實際需要,而在城管是否擁有行政強制執行權的問題上,城管自身雖然沒有獲得法律授予的行政強制執行權,然而,在整治城市違章建設、亂搭亂建、城市房屋拆遷等城管事務中經常性地扮演著強制執行機關的角色。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賦予法院強制執行權的過程中,除了人身權利之外,可以賦予城管必要的財產方面的行政強制執行權,對當事人的財產進行查封和暫扣等。
2011年7月1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人們盼望已久的 《行政強制法》,該法以規范行政強制避免公權力濫用為立法宗旨。隨著2012年1月1日起該法的正式施行,城管行政強制權的行使和運用將會于法有據,更趨科學規范,而人們對城管執法素來保持的 “行政強制權會否被城管亂用、濫用”的警惕和擔憂也將不再成為立法賦予城管執法所必需的行政強制權的掣肘。
(四)通過立法,回歸城管執法機構的行政機關性質,明確城管執法人員的公務員身份
如前文所述,在各地城管制度構建和執法實踐中,城管表現為一個在此時彼地性質皆不盡相同的 “不定性”機構,其中的尷尬與無奈令人深思。
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作為行政處罰權的一種特殊運用方式,是通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改變行政處罰各自為陣、分散行使的傳統執法模式,將那些可以集中起來的行政處罰權交由一個行政機關統一行使,這種權力分配和運行模式的改革,其實并沒有改變城管處罰權力的行政處罰權性質,因而在城管執法機構的性質確定上應當還其國家機關的本來面目,明確其行政機關性質和執法人員的公務員身份。筆者認為,立法對城管是國家行政機關性質的明確定位,既不是行政機構“簡而不減”的惡性循環,也不是對城管執法權力的擴權沖動,而是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這一行政管理模式的固有要求。這種名符其實的權力回歸和身份定位對于改善和推動城管執法實效是必要的。
首先,能讓行政相對人了解城管執法活動的公務性質,服從、配合城管執法,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其次,通過城管自身的“嚴格、規范、文明、和諧執法”,讓行政相對人對其執法活動萌發內心的理解和認同,進而轉化為行動上的自覺配合和支持。
再次,能夠幫助城管執法人員樹立正確的權責意識,依法合理行使法律賦予的執法權力。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增強城管執法人員的職業歸屬感和職務保障感,從而更加積極熱情地投入城管執法工作,提高執法效率。
“權威就是對權力的一種自愿的服從和支持。”城管執法權威的樹立除了依托于法律的保障外,在現實管理中,國家和各地政府必須厘清城市管理發展思路,科學規劃,民主決策,健全社會保障機制,積極回應、合理平衡城管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利益訴求,力爭做到求同存異,恢復和重建政府與社會、城管與行政相對人之間本應具有的管理與服從、服務與監督關系。當然,城管也應對自身執法進行因時、因地制宜的經驗積累、教訓總結和方式方法改革,惟有通過城管自身的積極有效作為,城管執法才能獲得行政相對人的內心認同和自覺支持,而唯有建立在科學、民主、法治基礎上的權威才能成為令行政相對人心悅誠服的真正權威。
[1]胡錦光.行政法專題研究(第二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2]韋紅霞.城管執法存在問題及對策探析[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0,(03):63.
[3]王鷹,金光明.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成都時代出版社,2004.
[4]城管屢遭暴力抗法 執法改革試點12年仍難全國立法[EB/OL].http://www.chinanews.com,2009-04-18.
[5]四川省城市行政執法相對集中處罰權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第八條[Z].
[6]楊小軍.城管執法機構性質與城管執法體制[J].行政管理改革,2010,(04):26.
(責任編輯:牟春野)
Confusion and Authority of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
Wang Hongfang,Li Zheng
Current issues for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 are get ting tough in China.The correct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can avoid the embarrass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and the measures are also the priority to positively or correctly tackle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problems.The measures are as follows:First,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urban management legislation.Second,rationally allocating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obligation and right's limits.Third,resuming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ion bureau's nature as an administrative organ,making it sure that the 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 are civil servants.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urban management inspectors'law enforcement;confusion;authority
D922.112
A
1007-8207(2012)04-0024-04
2011-12-23
王洪芳(1975—),女,苗族,貴州遵義人,四川警察學院副教授,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李錚(1969—),女,四川綿陽人,四川警察學院副教授,教育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文學。
本文系2010年瀘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課題 “城管執法的權威與困惑”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LZ10A46。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