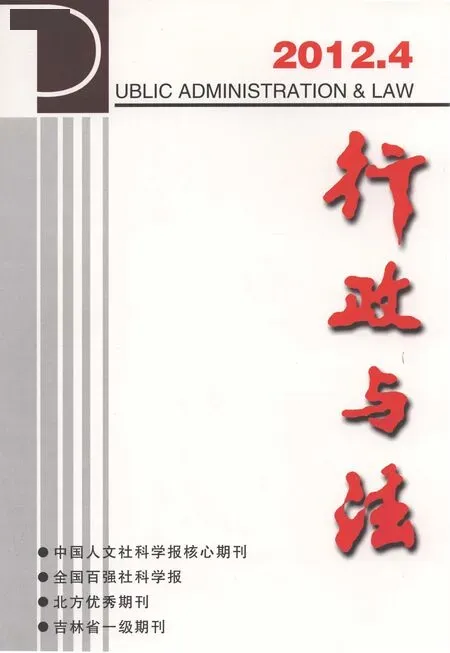論無因管理的法律適用
□ 焦清揚
(西北政法大學,陜西 西安 710122)
論無因管理的法律適用
□ 焦清揚
(西北政法大學,陜西 西安 710122)
無因管理作為債的一種形式,是指沒有法定或者約定的義務,在考慮他人真實意思或可推知意思的基礎上,有為他人管理、服務事務的意思,且客觀上符合他人利益而在管理人與本人之間直接產生債權債務的適法事實行為。見義勇為的法律適用一般宜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無第三人侵害情形時的見義勇為,作為無因管理的特殊形態,適用無因管理的法律規定;二是在有第三人侵害情形下的見義勇為,作為阻卻第三人侵害的一種行為,可以適用因阻卻侵權行為之見義勇為的相關法律規定。立法應當完善對因實行無因管理而受損之人的保護,特別是應當擴大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范圍以及賠償范圍。
無因管理;見義勇為;法律適用
一、問題的提出
2009年7月中旬的一天,13歲少年甲與同班同學乙等人到河灘游泳。乙因水性不好被河水淹沒并掙扎呼救,甲見狀急忙游至乙身后奮力將其推向河岸。在其他同學共同幫助下,乙得救,而甲卻因體力不支沉入水中,因溺水時間過長經搶救無效死亡。事發后,甲的父母與乙的監護人因賠償問題發生糾紛,訴至法院。案件審理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甲舍己救人的行為屬無因管理,乙作為受害人應當承擔甲因救助而支出的費用和損失。第二種意見認為,甲舍己救人的行為符合我國《民法通則》第109條規定的防止侵害行為中的見義勇為行為的特征,因沒有侵害人,乙作為受益人應給予適當補償。[1]
無因管理是民法中的一項重要制度。由于我國立法對無因管理的界定尚不完備,司法實踐中適用無因管理時出現分歧在所難免。結合本案,筆者認為應認真對待以下兩個問題:第一、該案應該如何定性?即甲舍己救人的行為適用無因管理的相關法律規定還是適用因阻卻侵權行為的相關法律規定?第二、現今關于因無因管理與阻卻侵權行為而引起的損害賠償的立法能否最大限度地維護并平衡各方利益?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模式因襲了事實認定——法律適用這一傳統分析風格。本文試圖通過對無因管理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舍己救人等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律適用之研究,進一步完善相關立法,提升司法適用的準確性,以更加完備地平衡并維護各方當事人權益。
二、無因管理的界定
無因管理是一種適法的事實行為,在大陸法系國家,其直接形成法定的債權債務關系。我國《民法通則》第93條一般被認為是對無因管理所作的立法定義,即“沒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進行管理或者服務的,有權要求受益人償付由此支付的必要費用”。界定無因管理概念,規制無因管理行為,需要面對兩種價值的劇烈沖擊——既包含了不得隨意干涉他人事務的法律要求,又融合了推進人類社會互助互愛的精神內涵。[2]兩者之間的矛盾調和無疑對立法技術提出了較高要求。我國學者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一般將無因管理的內涵概況為三個方面:第一,為他人管理事務;第二,有為他人謀利益的意思;第三,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3](p498-499)為他人管理事務即為他人進行管理或者服務;有為他人謀利益的意思,簡稱為管理意思,是構成無因管理的主觀要件;而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是成立無因管理的前提條件。學者們試圖僅通過“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的表述就能概括出無因管理的主客觀要件,而諸如管理者的心態、管理后的客觀實際效果等均未提及,結果當然是定義界定難以周延。
關于無因管理,大陸法系各主要國家(地區)基本上都有明確的立法定義。《德國民法典》第677條規定:“為他人處理事務而未受他人委托的人,或為他人處理事務而對于該他人物權以受委托以外的方式為之處理事務的人,必須斟酌本人真實的或可推知的意思,像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樣,管理該事務”。其第679條繼續規定:“本人的某項義務的履行關乎公共利益的,如不管理事務就不能適時地履行該項義務或本人的法定扶養義務,則不考慮本人的與事實管理相抵觸的意思”。[4](p274)“為他人處理事務而未受他人委托的人, 或為他人處理事務而對于該他人物權以受委托以外的方式為之處理事務的人”指出了無因管理的適用前提——管理者是一切無權利也無義務管理他人事務之人;“必須斟酌本人真實的或可推知的意思”足見其立法理論的嚴謹——既體現出無因管理制度適用的主觀要求,又將此細化為“真實”與“可推知”,從而將在難以得到他人明確意思的情況時,管理者依照本人一般可能的做法而做出的行為,“推定”為符合本人利益的情況巧妙將其納入規制范疇;“像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樣,管理該事務”不僅明確了客觀要件,還提示出管理者管理他人事務時的注意義務的要求程度——須達到 “本人利益所要求的那樣”;而第679條更是規制了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不考慮本人的相抵觸的意思,該條的設立是對第677條所規定的一般情形及條件即應當依照本人的意思進行管理之補充。從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德國民法典》對于無因管理的界定是較為全面而科學的,其特點在于充分照應理論,并且糅合了主客觀構成要件。日本民法第697條規定:“沒有義務而為他人開始管理事務的人,須按其事務的性質,以最適于本人利益的方法管理其事務”。[5](p149)縱觀該條規定,其亮點在于“按其事務的性質,以最適于本人利益的方法管理其事務”,從而嚴格規定了無因管理中的“管理人”在實施管理時,其行為應該具備的要件,并將管理人的主觀意思與實際效果相聯系,更加倡導“本人”利益的最大化。《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980條規定了 “為他人利益行為的條件”:“未經利害關系人的委托,未接受其他指示或者預先允諾同意,為防止利害關系人人身或者財產受到損害,為履行其債務或者為了他的其他合法利益的行為(為他人利益的行為),應從利害關系人的明顯利益和好處出發,以及根據利害關系人實際的或可能的意思,以實際情況所必需的關心和審慎態度實施”。[6](p337)俄羅斯聯邦民法典關于無因管理的界定可謂是十分完善的,其規定了充分的前提條件、明晰的主客觀要件,特別是“為履行其債務或者為了他的其他合法利益”將“本人”的“利益”做擴大化解釋,這樣就賦予了諸如為他人代繳稅費等涉及公法性質的行為能夠適用無因管理制度調整的正當性。《荷蘭民法典》第六編債法總則專設一節對無因管理進行了較為科學的規制,其第198條規定:“不具有根據法律行為或者法律規定的其他法律關系所賦予的權力,自愿地根據合理理由照管他人利益的行為,構成無因管理。”[7](p220)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成功的繼受《德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也于第172條較為科學完備的規定了無因管理制度,即“未受委任,并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本人之方法為之”。[8](p406)
與德、日、俄羅斯、荷蘭等諸個大陸法系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相比,我國關于無因管理的立法定義除了有較為粗放的不足以外,還涉及同義反復的瑕疵。根據無因管理形成的理論基礎以及運行時的必備要件,我們理應更為精準地定義無因管理,以期在立法上邏輯嚴密,在實踐中運作流暢。日本學者我妻榮認為, 無因管理就是債約性很強的債權法律關系。[9](p1-38)無因管理理應突出為本人管理、服務事務的意思。同時,根據現代民法理論,無因管理制度中,“為他人利益”有主觀符合(適法)與客觀符合(適法)兩種,①適法無因管理有主觀適法和客觀適法之分,前者是指管理人事務利于本人且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的無因管理。后者是指管理人事務違反本人的意思,但管理是為本人盡公益上的義務或履行法定扶養義務的無因管理。參見張俊浩.民法學原理[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870.這一點也應在定義中有所體現。具體說來,我國民事立法在規制無因管理概念時,首先,應明確無因管理適用的前提要件,即“沒有法定或者約定的義務”;其次,應體現無因管理的主觀要件,即明確規定“在考慮他人真實意思或可推知意思的基礎上,有為他人管理、服務事務的意思”,并且通過“推知”將“客觀適法”這種情形涵攝到規制范疇中來;最后,應強化無因管理的法律性質,即“客觀上符合他人利益而在管理人與本人之間直接產生債權債務的適法事實行為”。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筆者建議將無因管理定義為:沒有法定或者約定的義務,在考慮他人真實意思或可推知意思的基礎上,有為他人管理、服務事務的意思,且客觀上符合他人利益而在管理人與本人之間直接產生債權債務的適法事實行為。通過科學規制無因管理的概念,以明確無因管理內涵的三個方面要素:第一,客觀要件是他人利益;第二,無因管理的主體范圍僅限于“管理人”與“本人”,而不涉及第三人;第三,無因管理是非意表行為,符合要件作出行為即構成,故其屬于“事實行為”,且用“適法”以視與侵權行為相區別。
三、無因管理的認定
德國法學家耶林在其頗有影響的著作《法律:作為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中明確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實際的動機。他宣稱,法律是根據人們欲實現某些可欲的結果的意志而有意識地制定的。根據他的觀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有意識地達到某個特定目的而制定的。[10](p115-116)加拿大學者溫里布認為:“學者的任務便是:將這些目的特定化為與事故相關的目的,用私法這個特定的法律部門來予以規制;表明不同的目的如何得到平衡;評價當下法律學說是否實現了這些目的;以及呼吁可能增進這些成就的變革。”[11](p4)王澤鑒先生也認為:“任何法律均有其規范意義和目的,解釋法律乃在實踐法律的意旨,因此解釋法律時必須想到:‘為何設此規定,其目的何在?’需注意的是,法律目的具有多種層面,有為具體的規范目的;有為抽象目的,如法律的社會作用,經濟效率以及公平正義等,應視情形,一并加以斟酌。”[12](p184)因此,科學認定無因管理必須首先直面并闡釋無因管理制度的目的與功能。
無因管理制度肇始于羅馬法。羅馬法將無因管理歸類至準契約, 視作是債務發生的一種原因。[13](p396)有學者研究認為,從目的與功能視角分析,無因管理制度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偏重保護本人利益階段;二、兼顧管理人利益階段;三、注重公益階段。[14]羅馬法上,“無因管理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通過為那些樂于助人者提供補償來鼓勵保護不在場者利益的行為”,[15](p239)從而體現了無因管理第一階段的發展是以保護“本人”為立法初衷與價值追求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理性“經濟人”的真實心態與無因管理中對“管理人”的要求心態發生抵牾,且更為重要的是,將保護重點僅僅放在受益的“本人”上,對于付出時間、金錢、精力的“管理人”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不公平的,與民法公平之基本理念相悖,倘若對“管理人”不加以關注,這種人類互助之美德必將因為經濟之失衡而逐漸喪失殆盡,所以,無因管理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在保護本人利益的前提下,兼顧管理人的利益,以期調和與衡平雙方利益,做到利益獲得與損失的不偏不倚。時至今日,縱然“自決權”亦或是“不得隨意干涉他人之事務”的法律原則愈演愈烈,但是社會互助的傳統風尚和助人為樂的政策導向仍然值得倡導并加以弘揚,加之無因管理制度所蘊涵的一系列精神風尚對社會整體帶來的是積極功效,所以加強無因管理的制度規制并加以科學適用,有助于與整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導向相契合。近時的法學研究與司法實踐均顯示出有必要進一步擴張無因管理的認定與適用。日本學者我妻榮指出,無因管理“不僅僅只指他人財產上的事務,還包括有關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范圍較廣的無因管理。除此之外,在處理他人既存的民事法律關系以及在為他人創設新的民事法律關系方面,也承認無因管理的成立。基于此,德國有些學者主張:因無因管理名稱的內涵比較狹窄,應該稱之為‘人類扶助’。在法國也有同樣的主張。日本的學者一般也傾向于這一主張”。在他看來,“即使我們生活在一個重視私法的環境內,也要尊重社會所倡導的相互提攜、相互扶助的社會理念”,“作為有社會價值的行為,也應該得到尊重,并在某種程度上予以支持和推廣”。[16](p2-3)正因為如此,在司法實踐中有時確實難以認定諸如本案中甲舍己救人的見義勇為行為是適用無因管理的相關法律規定還是適用因阻卻侵權行為之見義勇為的相關法律規定。
對于見義勇為,由于我國統一立法上的暫付闕如與理論研究的相對不足,使得其在法律適用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困境。見義勇為,在民法意義上,一般是指在緊急情況下,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行為人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或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侵害或危險而積極實施的不顧個人安危之危難救助行為。第一,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這是見義勇為構成的前提條件;第二,有非為自己利益的意思,這是見義勇為構成的主觀要件;第三,為他人利益而為一定行為,這是見義勇為構成的客觀要件。基于此,無因管理與見義勇為行為的交集一目了然:均有無法定或約定的義務這一前提條件;均有為他人利益之主觀意思;均有為他人的客觀利益而有所作為。但是見義勇為又不完全等同于無因管理。為了更好地區別見義勇為與無因管理,宜從立法目的與立法技術兩個層面加以深入分析,以探求見義勇為行為的特殊性。王澤鑒先生認為,“無法律上義務而為他人管理實務 (真正無因管理),究應如何規范,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此乃干預他人事務(如修繕他人房屋,出租他人房屋),原則上應構成侵權行為。唯人之相處,貴乎互助,見義勇為,乃人群共謀社會生活之道。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維護‘干涉他人之事為違法’的原則,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條件下,容許干預他人事務得阻卻違法,俾人類互助精神,得以發揚”。在他看來,“立法者及法學家所應致力者,乃如何調和上開‘禁止干預他人事務’及‘獎勵人類互助精神’兩項原則”。[17](p257-258)無因管理制度的設立,使得為他人利益的且無法定或約定義務的作為行為有了正當性的法律依據,并且在管理人因此行為造成損失時,能夠得到一定保障,使得本人受益與管理人受損得到了平衡。反觀見義勇為,其在我國傳統文化意識中彰顯得淋漓盡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等行為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支持與敬仰,這種“英雄行為”一般都是帶有一定的危險性,特別是帶有對于自己生命健康的危險性,且多體現于維護社會治安、救死扶傷方面。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英雄”不僅需要我們從道義上肯定,也需要社會在經濟上給予支持,至少不再出現“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尷尬境遇。基于此,多數國家對于“見義勇為”或類似行為程度不等的進行了立法上的規制。無因管理多基于平和狀態下為他人利益而受損的情況,見義勇為多建立在危難狀況且很大程度對行為人會造成身體損害的境況,兩者的規制目的自然有所區別。
然而,希冀僅僅通過探求立法目的而分析立法價值對于界定無因管理與見義勇為這兩者的關系,顯然是不夠的,而且,僅從外觀情形來判斷無因管理還是見義勇為也是不嚴謹的,在某種意義上其只能作為判斷的輔助標準。我們還需要從立法技術層面進行剖析,方能從宏觀再回歸于微觀視角,從而有助于我們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定性問題。
無因管理形成的是一種法定之債,其效力是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法定債權債務關系,而于此情形下的當事人理應限定于管理人與本人。無論如何,無因管理的主體范疇中不應再出現第三人,或是所謂的侵權人以及由間接因果關系所追溯的任何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132條明確指出:“民法通則第93條規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務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償付的必要費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務活動中直接支出的費用,以及在該活動中受到的實際損失。”這一規定也充分說明無因管理及其所引起的損害賠償費用均僅立足于管理人與本人兩者之間,不涉及第三人。反觀《民法通則》第109條以及《民通意見》第147條關于“侵害他人身體致人死亡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依靠受害人扶養而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要求侵害人支付必要生活費的,應當予以支持,其數額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的規定,無論是對“見義勇為”的法律化定性還是規制損害賠償費用的補充性司法解釋,均認為見義勇為的主體有三方,即侵害人、受害人與受益人。對比無因管理,受害人即相當于管理人,受益人即相當于本人,而見義勇為或類似行為在主體上擴充了“侵害人”,這無疑是厘清《民法通則》第93條與第109條法律適用的重要條件。進而,筆者認為,見義勇為的法律適用一般宜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無第三人侵害情形時的見義勇為,作為無因管理的特殊形態,適用無因管理的法律規定;二是在有第三人侵害情形下的見義勇為,作為阻卻第三人侵害的一種行為,可以適用因阻卻侵權行為之見義勇為的相關法律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還應當正確把握《民法通則》第109條及相應的《民通意見》第147條與《侵權責任法》第23條的銜接。《侵權責任法》第23條規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權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責任。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責任,被侵權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由此,筆者大膽認為,《侵權責任法》這一規定是針對于見義勇為中具有加害人的情形下受有侵害者的補償請求權,而且此處明確提及“侵權人”,所以,立法上第二種“見義勇為”類型必須具有侵權人這一要件,這是對《民法通則》第109條的完善與補充,而類似于搶險救災等對于基于天災而引起的情況所作出的行為理應歸為無因管理,這種分類從《民法通則》第93條的規定來看,也是能圓潤自洽的,因為此類情形符合無因管理的所有要件;且從立法成本和法律制定的穩定性看,將無因管理制度適當泛化而涵攝見義勇為中無侵害人的情形無疑是符合立法經濟性與穩定性的。
基于上文分析,筆者認為本案中應定性為無因管理,適用《民法通則》第93條的規定,雖然本案從事發情形看似乎是危急的,但是外界情況只能作為輔助標準,在案件中,主體只有兩方,這才是定性的關鍵點。對于此類舍己救人等見義勇為案件,宜遵循以下分析路徑:判斷主體范圍,若僅有管理人與本人,即案件中管理事務之“因”并無第三人侵權因素,則一律定性為無因管理,法條依據為《民法通則》第93條;至于因阻卻侵權行為而生的見義勇為行為,則應適用《民法通則》第109條和《侵權責任法》第23條的規定。外觀情形只可作為輔助參考,不可作為定性之唯一依據。依此標準,既可以迅速而準確地定性案件,又不至于混亂現行立法結構思路。
四、無因管理的法律救濟
正是由于本案中甲舍己救人的見義勇為行為定性為無因管理,因此法律救濟理應適用與無因管理制度相對應的《民通意見》第132條的規定,即《民法通則》第93條規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務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償付的必要費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務活動中直接支出的費用,以及在該活動中受到的實際損失。本案中,甲之父母可以請求受益人支付因救助乙導致甲死亡這一結果的相應費用。
至此,本案的兩個相關問題似乎已經得以解決,問題在于如此法律救濟的法律規定本身是否合理?根據相關立法各方利益能否得到最大化的實現與相對平衡?結合本案,認真研析《民通意見》第132條,深感我國關于無因管理之債而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立法過于粗糙,難以真正實現維護受損者的利益以及協調各方利益平衡之目的。
第一,立法規定了“管理人”或“服務人”的請求權,然而當“管理人”或“服務人”死亡時,其近親屬(本案中為甲之父母)是否能以適格當事人的身份提起賠償之訴?既然認定屬于無因管理之債,根據債的相對性原規則,似乎甲之父母又無權向受益人提起訴訟?建議通過擴充解釋或通過立法完善,將請求賠償的主體從“管理者或者服務人”擴大至 “管理人或者服務人及其近親屬”,實現程序法與實體法的對接。第二,基于民法的基本原理與相關法律規定,甲之父母無法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然而,本案中,甲行為的崇高性與結果的悲劇性之反差必然會給其父母帶來無以復加的精神痛苦,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于情于理都顯得正當無疑,而目前的相關法律法規對此并未進行保障,并且在相關司法實踐中,對于界定為無因管理的賠償一般都未支持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如在楊國新與徐仙月等人因無因管理糾紛上訴案中,二審法院認為:“原判將不屬于管理而支付的作為精神撫慰金的死亡補償費62800元”,“列入實際損失的范圍,系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錯誤,本院予以糾正”。[18]其實,精神損害理應歸為《民通意見》第132條的“實際損失”,“實際損失”當然的涵蓋財產權與人身權損害,因為生命價值作為人身權最為重要的一項權利,其受保護理所應當。當然,訴請精神損害賠償的前提必須是有損害事實且造成嚴重精神痛苦。若實際損失中沒有精神損失,則精神損失費自然不為“必要費用”,也就當然的無法提出賠償請求。但是此處也面臨著一個問題,即精神損害必須緣于侵害人的侵害行為,在無侵害人的見義勇為情形下,管理者是無從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筆者認為,倘若擬制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此處,是有違民法基本理論的,且無限擴大民法的調整范圍也將使得民法不堪其重。所以,在此種情形下,筆者建議通過相關社會保障等救濟機制對管理人加以保障。至于利益平衡問題,由于管理人的行為是為受益人之利益且此種行為是為社會所提倡的,其理應得到更為周密的保護;受益人在許多情況下正是因為管理人的出現而免遭損失或減少損失,其當然的應在管理人利益難以得到彌補時承擔相應的責任。根據民法的公平原則,即使受益人本人并未受益,其也應該與管理人共同分擔損害后果。在這里,受益人承擔的是一種類似于補充責任性質的責任,其充當的是不完全意義上的終局責任人。《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984條明確規定:“為他人利益的行為未達到預期結果時,仍保留要求補償必要費用和其他實際損失的權利。但為防止他人財產受損失而實施行為的,補償的數額不得超出財產的價值。”[19](p338)《魁北克民法 典》第1486條也規定:“如具備管理他人事務的條件,即使未達到預期結果,本人也有報銷管理人已發生的全部必要或有益費用,并賠償其因管理且非因其自身過錯承受的任何損害。”[20](p187)《瑞士債法典》第422條也有類似的規定:“管理人行為時已經盡到其應盡的注意義務的,即使行為的后果尚未實現,管理人也有權請求賠償和補償”。[21](p135)從俄羅斯與瑞士相關的立法規定看,立法首先肯定了在預期的、理想的管理結果并未出現時,管理人仍然是具有要求賠償、補償以及實際損失的請求權的。《俄羅斯聯邦民法典》更是進一步明確了補償費的限額。如此規定有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其一,基于無因管理的特殊性,“可能受益人”理應基于“受益的可能性”而與謹慎管理者共同分擔管理者的損失,這樣的風險分擔機制更加關注法律的實質正義,并且通過傾向于保護管理者的立法技術反映出立法的指導精神;其二,基于實際管理結果的非理想化,對于“管理者”的補償也應該有一定的限度,否則對于“實際未受益人”而言是極其不公正的,同時,此時的補償也應是雙方共同承擔,而非僅為本人的義務。如此立法規定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得失,并且鼓勵社會成員的互助。
為此,筆者建議,立法上宜進一步完善因無因管理而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的范圍:(一)管理人在管理服務行為中受到損害的,管理人及其近親屬可以要求受益人償付必要費用,包括在管理服務中直接支出的費用,以及由此受到的實際損失,若管理人或其近親屬受到嚴重精神損害,實際損失中應包含精神損失。以上費用由侵害人承擔,無侵害人或侵害人無力賠償的,受益人承擔相應補償責任。(二)管理人行為時已經盡到其應盡的注意義務的,即使行為未達到預期結果,管理人仍有權請求補償必要費用以及實際損失,費用承擔順序同前款規定。
[1]馮朝陽.舍己救人是無因管理還是防止侵害[N].人民法院報,2009-12-01(6).
[2]徐同遠.無因管理價值證成的追尋[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1,(03).
[3]王利明.民法(第五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4]德國民法典(第3版)[M].陳衛佐譯注.法律出版社,2010.
[5]最新日本民法[M].渠濤編譯.法律出版社,2006.
[6]俄羅斯聯邦民法典[M].黃道秀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荷蘭民法典[M].王衛國主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8]楊立新.中國百年民法典匯編[M].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9](日)我妻榮著.我妻榮民法講義:債法總論[M].王燚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1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11](加)歐內斯特·J·溫里布著.私法的理念[M].徐愛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2]王澤鑒.民法思維: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3](意)彼得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M].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14]李文濤,龍翼飛.無因管理的重新解讀——法目的論解釋和論證的嘗試[J].法學雜志,2010,(03).
[15](英)巴里·尼古拉斯.羅馬法概論[M].黃風譯.法律出版社,2000.
[16](日)我妻榮著.我妻榮民法講義V4:債權各論(下卷一)[M].冷羅生,陶蕓,江濤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17]王澤鑒.債法原理[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8]唐楠楠,蔣昆玲.無因管理的法律適用與見義勇為者損害救濟制度比較研究——《民法通則》第93條或《民法通則》第109條的選擇適用[J].改革與開放,2009,(05).
[19]俄羅斯聯邦民法典[M].黃道秀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0]魁北克民法典[M].孫建江,郭站紅,朱亞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1]瑞士債法典[M].吳兆祥,石佳友,孫淑妍譯.法律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張雅光)
On Application of Law of Negotiorum Gestio
Jiao Qingyang
Being a form of the debt laws,Negotiorum Gestio refers to the appropriate factual behavior,causing directly from credit and debt between dominus reigestae and gestor,according with others’ benefits,without neither legal obligation nor contractual obligation,basing on concerning with others’ true intention or the intention which can be referred,meaning to manage and serve affairs for others.The righteous behavior ought to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One is a special form of the negotiorum gestio,for it not having others’ infringes;Being a behavior,witch impedes of the third party’s infringe,under the condition of suffering damages from the third party,the other type is able to be applied by the legal provisions correlated with the righteous behavior.The protection for damagers ought to be reinforced in legislation.Especially,the subject range for the right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and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as well should be enlarged.
negotiorum gestio;righteous behavior;application of Law
D923
A
1007-8207(2012)04-0124-06
2012-03-02
焦清揚,江蘇揚州人,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