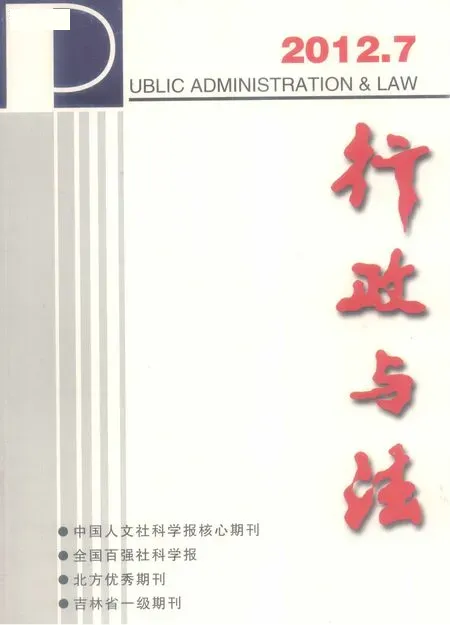論我國德治的法治化流轉
——兼評《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中的“三公”消費規定
□ 宋環環,徐玉生
(江南大學,江蘇 無錫 214122)
論我國德治的法治化流轉
——兼評《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中的“三公”消費規定
□ 宋環環,徐玉生
(江南大學,江蘇 無錫 214122)
德治與法治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可轉換性。基于此,德治與法治在傳統的互補結構形態下,還存在著一種局部流轉的結構形態。由于市場經濟的沖擊、公共生活本土化資源的缺失以及傳統文化的弱化,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實踐中出現了德治的失范問題,因此,德治的法治化流轉將成為一種必然。 《機關事務管理條例 (征求意見稿)》將過去政府以德治理的范疇法制化,體現了德治的法治化流轉傾向。
法治化;德治;流轉
德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一直被理論界廣泛討論,人們對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以及法治與德治的關系的認識有所不同,對德治與法治的現實適用和側重也存在著差異,從而造成了各國治國方略以及管理體制的差異。就我國而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德治的法治化流轉①流轉在《辭海》中的解釋為:流落轉徙、流通周轉、運行變遷、輪流等。本文采運行變遷之意。法治基于德治,不僅僅是一種補充修正、參與關系,更有在一定范圍、限度內的轉化代替關系。在德治失范情況下,將一定的人們必須遵循的基本道德行為運用法律加以規定 (即德治),從而達到有效治理的一種方略的轉變和發展的趨勢。成為一種必然,德治的失范②失范,亦稱脫序,由于社會規范失調產生的一種社會反常的狀態。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首次引入這一概念,將失范注釋為:“一種規范缺乏、含混或者社會規范變化多端,以致不能為社會成員提供指導的社會情境。”迪爾凱姆認為,失范主要指一種對個人的欲望和行為的調節缺少規范,制度化程度差,因而喪失整合的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簡單來講,失范是社會所倡導的文化目標與現實中這些目標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之間的斷裂或緊張狀態。不斷得到重視和立法的彌補。2011年11月21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條例》),對規范“三公”消費問題,征求社會各界意見。《條例》的公布對我國德治與法治的發展方向起到了引導作用,是我國政府機關對“三公”消費所進行的統一規定。
一、德治法治化的理論基礎
⒈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理論。道德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是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關系的反映,是依靠人們的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和傳統習俗等維持的,用以調整人們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的總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道德已不能完全調整社會關系,社會需要一種具有強制力和普遍約束力的社會標準和規范,法律便應運而生。關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我國從來都不是一個過時的問題。③在西方,關于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從古希臘開始就展開了討論,主要有三種學說:自然法學派主張包容說,認為“惡法非法”,法律與道德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必然聯系,法律必須符合道德的要求。以凱爾森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法學派主張分離說,認為“惡法亦法”,法律只要通過國家規定的程序制定出來,不管其內容如何,都是有效的。以哈特為代表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主張法律與道德存在偶然聯系,但不是必然的聯系。我國歷史發展進程說明了道德與法律在本質上的必然聯系。周公制禮,引禮入法,出禮入刑,事實上體現了禮的規范的系統化。到了漢朝,“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將一部分符合儒家原則的道德通過法律加以約束。隋唐諸帝先后完成了自漢代以來的“引經決獄”、“引禮入法”到禮法合流的演變。統治者事實上將法律與道德視為一種互補的聯系,二者服從并服務于統治者的階級需要。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雖然肯定道德與法律的必然內在聯系,但是并不必然得出二者在統治上的作用是一致的,事實證明,歷代帝王對二者各有側重。同時,道德與法律在事實上的互補關系亦并不當然決定德治與法治的未來發展走向。此外,正如博登海默的預言“也許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隨著其他國家的發展,幫助處于嚴重危難中的人的義務,會在某個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領域轉入強制性法律的領域。”[1](p376)筆者發現,法律與道德的內在互補關系也一直影響著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種法律化流動的傾向在現實需要的情況下正在不斷地體現出來,而且這樣一種趨勢在實踐中正在蔓延。隨著社會的發展,為了增強對某類行為的調控力度,一部分原本屬于道德領域規范的社會行為,轉由法律調控。
⒉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從古到今,每個國家或民族都在尋求適合其生存與發展的有效的治理方式,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正確處理法治與德治的的關系,對于一國的發展尤為重要。法治即“依法治國”,旨在建立法治化社會;德治即“以德治國”,旨在建立人性化社會。對于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學術界的觀點幾乎一致認為二者是一種互補結構形態。法治與德治并重,是治國方略的兩個同等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二者優勢互補。《唐太宗集·薄葬詔》的“失禮之禁,著在刑書”正是儒、法互補,“德治”、“法治”并用的政治結構的典型。當今中國,江澤民同志在提出依法治國方略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方略,并指出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筆者認為,一方面,法治與德治互補共存;另一方面,在德治與法治的互補結構形態下還存在著局部流轉的結構形態。依據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①價值理性也稱實質理性,即 “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統一于人類的社會實踐。在國家的治理中,德治體現的是一種價值理性,而法治則體現出的是一種工具理性。德治是法治的精神動力,法治是德治的現實支撐,二者相互補充。正如M·謝勒所說:“每次理性認識活動之前,都有一個評價的情感活動。因為只有注意到對象的價值,對象才表現為值得研究和有意義的東西。”德治與法治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統一于人類的社會實踐之中。②對于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由于是學界長期以來形成的觀點,其理論支持較多且角度各異。比如,基于人性的角度(鄭維東,2002);從道德與法律的優缺分析的角度(曲諫,2003;王志強,2006);從功能主義的角度(洪波,孫少華,2002);從社會治理的角度(楊榮,2007)等等。然而,由于社會的進步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轉型的特定時期,在某些領域,③本文所指的德治法治化流轉,是基于一定范疇內事實上的流轉,而不是完全。具體就該范疇,主要由以下幾部分構成:首先,一部分原本屬于德治的范疇,但德治失范且無更優替代。其次,基于德治與法治存在界限的模糊性,可由德治或法治規制的部分。此外,在道德與法律的控制之外還存在其他如宗教等其他的第三地帶。價值理性日益失落,工具和價值理性二者的關系也逐漸疏離。現實中存在的社會冷漠,道德淪喪,“三公”消費鋪張等問題依靠道德約束已難以解決。基于道德與法律的可流轉性,在不同的時期,為了適應不同的社會需求,德治與法治也存在著局部流轉的傾向。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來看,整體上呈現出了一種從完全依靠道德約束到重視法律規范的趨勢,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德治與法治的范圍與運用均存在著一種動態的調整趨勢。
二、德治失范與法治化流轉的必然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在多元化社會里,不同的利益主體在道德和價值觀念上的差異逐步加大。現實中,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已經在無形中弱化,在有形中缺失。從民眾的“路不扶人”、“見死不救”到官員的“樓脆脆”、“賺足走”等等,道德的邊界早已被逾越。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始終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加強思想道德教育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2006年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就是德治的典型。然而,在現實中,道德建設遠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三公”消費一直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許多地方政府對此諱莫如深,對于有的公民提出的公開“三公”消費的要求,某些地方政府更是如臨大敵。[2]雖然黨和政府出臺了相關的政策對其進行整頓,但是這些政策只是抽象的、概括性的,沒有具體的標準,或者只是書面和口頭的提倡,并寄希望于官員的自律和道德的約束,更沒有做出具有實質意義的統一立法加以規制。在公車配備、公務接待等標準的執行上,寄希望于官員的道德良知和利益自省已經遠遠不夠。德治試圖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干部以及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就此,德治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⒈市場經濟的沖擊及倫理缺失。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人是有利益屬性的,“每個人都努力地利用自己的資本,最大化自己的產出。他這樣做,既不是為了公共利益,他也不知道自己創造了多少公共利益。他只追求自己的安定,追求自己的私利。”[3]然而,市場經濟以承認個人利益為前提,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人們注重私利。同時,利益格局的調整導致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在客觀上,逐利的事實外溢到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造成了人們主觀上的價值判斷錯誤。市場經濟實質上應該有其自身的倫理,而不是一味的逐利。
⒉公共生活本土化資源的缺失。由于我國長期分散的小農經濟導致了公共生活本土化資源的缺失。道德的實施范圍是寬泛的,不特定的,這就要求人們像對待親人一樣去同等地對待陌生人。然而,我國古代思想觀念強調的道德、禮儀、孝道等,主要圍繞的是以血緣為紐帶的親屬鏈條。這在本質上造成了公共道德意識的缺乏,取而代之的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的排他性道德。我國雖然一直強調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但卻只是口號上的提倡和形式上的表彰,公共生活對道德建設的重要性認識問題始終沒能徹底解決。
⒊傳統文化的弱化與自律的失控。正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弱化,文化缺少根基,才會使人格產生扭曲,倫理道德才會接連失范、滑坡,才會使人喪失了原本承擔責任義務的本性。我國傳統文化促成的是一個以強制為基本特征的道德氛圍,道德的他律性在一定程度上因刺激形成了自律。然而,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傳統文化的丟失使得道德的他律性淡化,自律性失控。
在這種情況下,要使社會秩序重新得到規范,憑借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就成為必然。當然法律并不是唯一的調整和控制手段,龐德認為社會控制主要有三種:宗教、道德和法律。在歷史的某些階段,道德和有組織的宗教曾經占據了社會控制的主要地位,但是,從16世紀以來,法律已經成為社會控制的首要工具。事實上,在德治失范的情況下,法治是最優的流轉方向,也是一種必然的走向。依照龐德的社會控制理論,①社會控制,按照羅斯科·龐德的說法,就是保持人類對于內在的本性的支配力量的手段,通過作為每個同胞的人對每一個個體的人所施加的壓力來保持社會控制,施加這種壓力是為了迫使他盡自己的本分來維持文明社會,并組織他從事反社會的行為,即不符合社會假定的行為。引自柳冰玲.試析法律作為社會控制主要手段的正當性——讀羅斯科·龐德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J].商品與質量:理論研究,2011,(07):193.法律就是人們對每個人所施加的壓力,施加這種壓力是為了迫使他盡自己的本分來維持文明社會,并阻止他人從事反社會的行為,即不符合社會秩序假定的行為。法律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具有難以比擬的優越性,是發達政治社會中的一種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形式。[4](p9)只有把法律作為控制社會的手段才能實現文明社會的發展,才是社會控制的有效手段。目前,社會越來越需要法律的引導和規制。在國際上,眾多國家主張法治,而道德只是一種輔助。美國是典型的法治國家,昂格爾認為法律至上,無論是公民還是政府官員都從屬于法律。美國的法治不只是反映某個階級的意志,而是協調各種利益并凌駕于他們之上的力量。[5]
總之,在一定的社會轉型期內,德治的法治化流轉是一種必然,在某些領域需要以法治來規制,同時德治在政府的規制方面需要代之以法治的嚴格約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取代和排除德治,在一定程度上,社會的發展以及市場經濟建設需要法治,但又離不開德治。正如諾斯所說:一個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配合外,還需要有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
三、德治的法治化流轉的規范與實踐
馬克思主義科學唯物史觀認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應該是以生產力為標志的歷史尺度和以道德水平為標準的道德尺度的統一。從宏觀發展趨勢上考察,這種一致并不排斥二者在一定時期內的非線性演進。的確,在德治的法治化流轉過程中,也要處理好德治的地位和法治的運用問題。在我國,這一問題尤為明顯。目前,法治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適概念,但真正意義上典型的法治是西方文化中自然長成的近現代法治。在非西方社會,如在某些西方思想家(如馬克斯·韋伯)認為不可能生成法治的東亞社會,也發生了法治推進,嚴格依此說法我國屬于后者。一方面,在德治的過程中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理性地推定法治進程。但這種非自生、自發而刻意追求人為建構的姿態也帶來了弊端。應從現在開始就要充分認識到在不久的將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一定會漸漸露出它的極限。因此,必須時刻關注政府主導、威權推進與法治強調對權力的制約控制之間的矛盾沖突、對結果和績效的關注與對形式合理性的漠視之間的反差等問題。[6]
具體來看,在“三公”消費問題的處理上,就體現了德治的法治化流轉。2011年11月21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通過《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廣泛征求社會意見。這標志著我國政府向著陽光、透明方向所作的努力,將過去政府以德治理的范疇法律化,通過《條例》的形式,給予了法規形式的強制性規定,讓機關管理走上了法治的軌道。此后,“三公”消費將有法可依,經費不透明、公款接待鋪張浪費等問題有望得到解決。
⒈《條例》的制定將建立統一的標準化制度。事實上,在過去,對于各部門、各單位的“三公”消費均有相關規范,部分還與《條例》中的內容重復。但為何實施無效或者說并未引起重視,究其原因還是規范的集中性和約束力的問題。該《條例》的制定將讓過去各部門分散的規定具有統一的形式,確立標準化的制度,使其有法可依。而且《條例》第18條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機關運行經費支出公開制度,定期公布公務接待費、公務用車購置和運行費、因公出國(境)費等經費的預算、決算、績效考評情況。”這實質上為“三公”消費公開提供了法律依據,體現了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原則。
⒉《條例》內容豐富,將原本口號性的道德規范劃入法律的具體范疇,但相關配套措施仍不完善。《條例》分為六章,分別為總則、經費管理、資產管理、服務保障、法律責任、附則。其中,對“三公”消費問題,立法做了明確表態。如第30條規定:“政府各部門應當配備符合經濟適用、節能環保等要求的中低檔公務用車,不得超編制、超標準配備公務用車。”第36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務接待管理機構和政府各部門應當執行國內公務接待制度和標準,不得超標準接待。”立法明確規定了“三公”消費開支不得挪用其他預算資金,不得攤派、轉嫁費用,對于預防“車輪腐敗”、“超標接待”、“大手大腳”等問題均給予了規制。然而,立法規定用“不得”、“應當”等字眼以明確的強制性規范的形式進行禁止性規定,而其中關于“標準”、“控制比例”、“實質性”等范圍卻沒有明確。對此,筆者建議,該《條例》的實施必須有相配套的制度來確保相關標準的落實。如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制定并發布的 《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選用車型目錄管理細則》在一定程度上為《條例》第30條的公務用車提供了適用標準。然而,《條例》中提到的多處標準及比例仍為模糊概念,需要有相關配套規定進行補充。
⒊《條例》的一大亮點就是對法律責任的明確。責任的承擔是法治化的一個重要體現。《條例》第5章專門規定了違法本條例的責任承擔,如果違反了條例的規定,會承擔行政性的或其它方面的法律責任,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法律的強制性不僅體現在必須遵守,而且其追責機制的威懾力更大。任何規定倘若沒有對責任的追究就會形同虛設,而本《條例》明確地規定了責任的承擔。
事實上,當人們逃避甚至抗拒道德的約束,公然不作為卻沒有得到實際制裁時,他們就不會感受和認同道德規范的價值。博弈論原理表明,只有當人們違反道德的行為受到懲罰時,才會驅使人們將法律精神內化為個體的行為準則,形成內心的自律。美國法學家昂格爾認為,現階段中國依然沒有形成有效的法律控制機制。[7](p63)當前,我國政府在調整社會關系的方式上也已經開始逐漸將德治向法治化方向靠攏,部分道德問題的法律化成為現實的需要,法律的控制事實上已經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德治的法治化流轉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一種必然,十分明顯地體現在《條例》中,相信我國法治化的發展也將更多地體現在政府守法以及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真正實現上。
[1](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2]季建民.三公消費的堡壘終于被一個鄉政府攻陷[J].新西部,2010,(04):72.
[3](英)斯密著.國富論[M].唐日松譯.華夏出版社,2005.
[4](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M].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08.
[5]See R.Unger,Law in Moder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976,pp.67-80.
[6]孫莉.德治及其傳統之于中國法治進境[J].中國法學,2009,(01):69.
[7](美)昂格爾.現代社會中的法律[M].吳玉章,周漢華譯.譯林出版社.2008.5
(責任編輯:牟春野)
On Chinas Legalization Transferred from Rule by Morality
Song Huanhuan,Xu Yusheng
Rule by morality and rule by law has transformation in a certain range.Based on this, beside in the traditional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form of rule by morality and rule by law,there is also a local circulation structure form.In China,a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pening policy is carrying on,the disadvantages of rule by morality eventually exposure.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market economy,the lack of the public life and native resources and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rule by morality change to rule by law has became inevitable.The “Administrative Affairs Management Ordinance (Draft)” law's promulgation legalized the category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virtue,which is reflected more the moral legalization in circulation.
rule by law;rule by morality;transformation
D63
A
1007-8207(2012)07-0025-04
2012-03-13
宋環環 (1990—),女,江蘇揚州人,江南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法學;徐玉生 (1967—),男,江蘇鹽城人,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執政黨建設。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和改進江蘇黨的建設”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9DJB006;江南大學2011年度教改課題 “《概論》課專題教學的研究與實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JGB20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