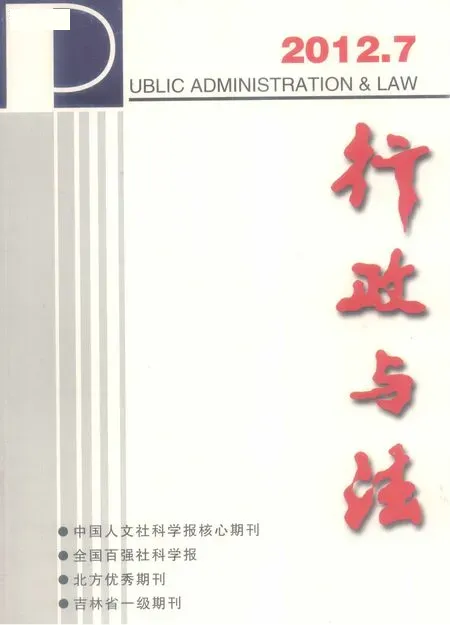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及實現路徑研究
□ 張培春
(渤海大學,遼寧 錦州 121013)
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及實現路徑研究
□ 張培春
(渤海大學,遼寧 錦州 121013)
本文從“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產生入手,分析了了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制約可持續發展的諸多問題,提出了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發展機制,通過加速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統籌人口、資源和環境和諧發展,完善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法律體系等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的路徑的建議。
可持續發展;制約因素;實現路徑
一、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產生
胡錦濤主席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性。黨中央提出的我國可持續發展問題既針對我國的現實發展,也反映了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對我們的要求。恩格斯曾經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1](p284)因此,可持續發展思想作為一種理論思維,也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自人類進入工業文明社會以來,伴隨著人類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和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人口激增、自然災害頻發等問題愈來愈困擾著人類社會。問題究竟出在哪里?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是什么?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是什么?這些問題迫使人們去思考。
早在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和《自然辯證法》等著作中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思想。盡管他們并沒有使用“可持續發展”一詞。但是,針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粗放式的利用、資產階級的奢侈性的消費、社會再生產關系的失調等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涵義和本質、自然與人類關系思想、循環經濟思想、協調發展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思想。不過,由于當時人類社會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尚不尖銳,工業文明對環境的破壞尚不嚴重,因而他們的上述思想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現代可持續發展思想萌芽于美國科學家萊切爾·卡遜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靜的春天》。萊切爾·卡遜在其著作中通過分析殺蟲劑對鳥類和生態環境的危害提出了全新的生態觀。1972年3月,D·梅多斯教授等人提交給國際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的題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提出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會導致全球性的環境退化和社會解體的觀點。1981年,美國科學家萊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一書,首次對可持續發展觀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書中分析了全球人口激增、土地沙化、糧食短缺、資源耗竭等問題,并且針對上述問題論證了控制人口增長、資源保護、開發可再生資源等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在學者們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影響下,國際組織、各國政府開始對可持續發展問題重視起來。1983年11月,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把布倫特蘭夫人等人撰寫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交給聯合國大會。該報告首次明確給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的發展。該報告對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及基本思想也作了清晰的、系統的理論闡述。至此,現代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基本成型。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指導下,1992年6月3~1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大會通過了《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熱內盧宣言》、《21世紀議程》和《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3項文件,并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進行了開放簽字。這次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人類已經將可持續發展理論變成了全球性的行動。
二、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⒈經濟發展方式尚未轉變。早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就提出了經濟建設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變到以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的要求,黨的十五大和十七大等報告中又多次強調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但由于我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經濟體制尚未形成,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因而迄今為止,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并未發生根本轉變,甚至在21世紀初反而出現了由粗放經濟發展方式所引發的過度投資和經濟過熱現象。在“十五”期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8.3%,而“十一五”期間貢獻率卻下降為31.6%。[2]這反映了我國經濟仍然是資本驅動增長模式和粗放型增長模式,這種粗放型增長模式嚴重制約著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⒉經濟增長與資源利用不協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以9.8%的年均增長率快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這樣的高速度是以資源的高消耗為代價取得的。中國科學院發布的《2006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對世界59個主要國家的資源績效水平進行了調查排序,中國資源績效居倒數第6位。目前,我國資源綜合利用率僅為33%,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其中,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個行業主要產品單位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0%,萬元GDP用水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3]廢鋼鐵的回收利用率是45%,廢銅是30%,廢橡膠是40%,而在發達國家均逾90%。[4]上述數據說明我國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狀況始終制約著我國的可持續發展。而導致這種高速度與高消耗并存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我國科技水平低,難以保證在資源的開采和利用過程中減少損失和浪費;二是有利于資源節約的法律法規不完善,沒有形成依法強制節約資源的制度體系。
⒊人口因素與環境、資源矛盾尖銳。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污染嚴重,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人口和資源矛盾方面,我國有13.4億人口,盡管資源總量很大,但是人均資源占有量卻很少。例如:人均耕地只有1.43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淡水資源人均徑流量為2200平方米,是世界人均人均徑流量的24.7%;人均森林占有面積1.9畝,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45種主要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5](p80)在環境方面,由于企業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環境保護法制不夠完善,GDP能源資源消耗過高,相應增加了單位GDP的污染物的排放量等因素,導致我國環境問題嚴重。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世界銀行發展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了16個。
⒋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目前,科學技術在各國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美國、日本平均科技貢獻率現已達到80%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歐國家為50%~60%,而中國的平均科技進步貢獻率為 20%~40%。[6]這個水平距離我國《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綱要(2006-2020)》提出的“2020年力爭科學技術的貢獻率達到60%以上。”的要求還很遠。形成上述局面除了我國與發達國家歷史上形成的科學和技術的差距因素外,主要是由于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失靈導致科技創新的動力不足和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比率低以及我國龐大的勞動力供給對科技應用的擠壓。
⒌產業結構調整存在的問題多。首先,傳統制造業“大”而不“強”。我國傳統制造業總量擴張迅速,但產業結構不合理而且升級緩慢。其次,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乏力。這主要是由于新興產業缺乏核心基礎技術支撐,缺乏發展所需的資金,缺乏發展的制度環境。再次,第三產業總體水平和質量不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第三產業有了較快的發展,但由于在認識上重視不夠,在稅收、收費、融資等方面缺乏優惠政策,導致該產業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測算,目前世界上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水平都在60%以上。然而在我國,2011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43.1%,與發達國家甚至和發展中國家相比均有較大差距。
⒍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不完善。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知識和技術的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或變遷也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7](p3)可見,法律制度與經濟發展方式有著相互制衡、相互促進的關系。推動和保障我國可持續發展有許多層面的因素,其中法律制度以其具有的普遍的約束性、強制性以及相對的穩定性和調控的超前性等特點成為諸多因素中的關鍵因素。然而,我國卻缺乏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法律環境。誠然,從黨的十三大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通過了 《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審議修改了一些阻礙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法規,國務院也制定或修改了相關行政法規。但是有關促進和保障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某些體現舊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制度依然存在,并成為嚴重阻礙可持續發展的羈絆。因此,不及時通過立法調整這些法律法規和實施機制,就不能消除制約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束縛。為此,必須清理和廢除帶有舊體制特征的制度,進行法律制度的創新,構建起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法律系統。
三、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實現路徑
⒈加快發展觀念的轉變,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觀念是行動的先導,有何種發展觀念,就會有何種發展模式。因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投入結構的調整,更需要進行經濟發展理念的變革。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經濟增長就是經濟發展,認為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生產商品和勞務能力的增長,因而將經濟發展速度作為經濟活動的主要追求目標。這種傳統的經濟增長觀念是早期工業文明的產物,本質上蘊涵了人與自然對立的理念。這種經濟增長觀認為,社會發展離不開人對自然的占有和開發,離不開人對自然的統治。在這種觀念下,人類利用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工具對自然資源進行了肆無忌禪的掠奪和消費,導致了生態的不斷惡化以及社會的危機。因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轉變發展觀念,必須徹底改變既有的思維方式束縛。要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還包括國民的生活質量,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的總體進步。因此,要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在“以人為本”的核心內涵上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和諧發展。
⒉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發展機制。資源利用的約束機制是決定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要使我國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就必須構建資源節約型的發展機制。首先,建立資源使用的硬約束制度。要建立健全節約資源的法律制度體系,將節約資源由過去的軟約束變為硬約束,對節約資源的行為依法予以獎勵,對浪費資源的行為依法加以懲處。其次,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在人和自然資源以及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產品生產和消費以及廢棄的整個過程中,實現生態型資源循環。要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目標,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來實現經濟的發展。再次,建設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用價格杠桿調節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目前,我國資源浪費的原因之一是自然資源價格過低,因此,要通過建設科學的資源價格體系,將自然資源國內市場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結合起來,這樣,既可以減少對資源的浪費,也有利于我國對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第四,完善相關的產權制度。主要包括完善自然資源的產權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因為只有自然資源產權清晰,才能充分發揮資源效益,做到物盡其用,使資源的浪費降到最低限度;只有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才能提高企業和科技人員開發、推廣應用資源節約型技術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降低我國在科學技術尤其是在提高資源利用率技術方面的對外依存度,從而使我國成為創新型國家。
⒊統籌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和諧發展。首先,控制人口的增長,實現適度人口目標。要提高全體社會成員對計劃生育的認識,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管理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采取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確保人口控制在預定目標以內。其次,建立人口生產與資源開發、利用聯動的中長期規劃機制。根據對資源普查和資源開發利用規劃制定我國的人口發展規劃,把人口生產與資源開發利用結合起來。再次,處理好人口生產與環境保護的關系。要隨著城鄉人口的增長加大環境保護資金的投入,解決環保建設資金不足問題;要完善環境保護方面的稅收、收費制度,使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⒋把推進科技進步與產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科學技術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主要表現在科學技術的進步能夠促進產業發展及其結構的不斷更新改造上。具體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發展能夠創立新的產業和產業部門,科學技術進步必然要求對原有的產業和產業部門進行改造,科學技術進步改變著各個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我們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把產業結構調整與科技進步緊密結合起來,要提高采用新興技術、高科技裝備企業在各個產業中的比重,以此促進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應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推動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優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的核心基礎技術,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金投入,完善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其次,利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擴大技改專項資金規模,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再次,努力發展現代化的第三產業。要實施有利于第三產業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尤其是要制定和落實對“小微企業”的優惠政策;要支持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促進服務業發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第四,進一步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政策扶持力度,積極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加速農業產業化、集約化進程。
⒌建立健全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針對一些法律法規體系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必須建立和完善推動和保障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
首先,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一是,完善財稅法規,實行真正的分稅制,按照“責權利”統一的原則,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稅收關系,實現中央、地方的財權與事權的合理劃分,解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二是,修改《增值稅條例》和《企業所得稅法》,通過完善稅制強化稅收制度激勵自主創新的功能。三是,完善資源方面的法律法規。提高資源稅稅率,防止對資源的過度開采;完善資源稅征收的方式,由從量征稅改為從價征稅;將稅收與資源市場價格直接掛鉤。
其次,制訂和實施新的法律法規。一是,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我國應在生態文明理念的指導下,制定一部健全而完善的《氣候變化應對法》,從而減緩和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為我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二是,我國還應該抓緊研究制定《生態補償法》,以促進生態補償的法制化。該法應當規定生態環境補償的基本原則、主要領域、補償辦法,并以此為依據,進一步細化森林、草原、水、礦產資源等各領域的法規。三是,針對區域發展不平衡影響我國可持續發展問題,必須盡快出臺《發展規劃法》,對規劃體系、編制程序、審批和實施等做出明確規定。同時做好《發展規劃法》實施的相關配套工作,著手起草《發展規劃實施評估條例》。
[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胡鞍鋼.全球危機下開創科學發展模式——“十一五”規劃資源、環境目標的進展[J].綠葉,2009,(04):108.
[3]陳世海.我國能源總體利用效率[J].資源節約與環保,2009,(02):19.
[4]程恩富,王新建.中國可持續發展:回顧與展望[J].中州學刊,2009,(09):7.
[5]2010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6]周京平.諾貝爾經濟學獎:科技進步貢獻率——與中國經濟理論與實踐[J].經濟研究導刊,2011,(07):9.
[7](美)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責任編輯:牟春野)
Factors Restricting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ath of Realization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Peichu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emerg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and inquires into th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 and its causes dur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solutions for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cluding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stablishing energy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through accelera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balancing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nd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for suppor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actors restricting;ways of realization
F126.4
A
1007-8207(2012)07-0034-04
2012-05-20
張培春 (1956—),男,遼寧鐵嶺人,渤海大學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本文系2012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項目 “馬克思主義可持續發展觀與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2lslktzimks-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