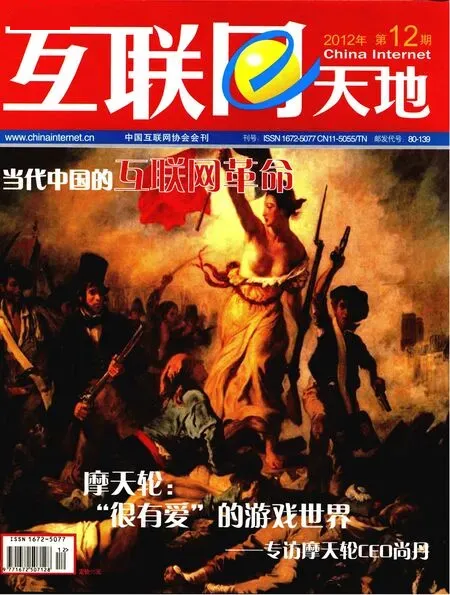未來全球經濟更應看重幸福指數
文 張璐晶
從長期來看,某種全球社會市場經濟的新模式似乎是人類未來唯一理性的選項。這種模式的研究者認為,經濟活動的核心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受利益最大化欲望的驅使,但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了社會凝聚因素。市場的力量必須用以滿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對人民的剝削。因此,社會市場經濟這個未來選項和以損害多數人利益追求少數人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格格不入。
之所以將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全球經濟發展方向,事實上是將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提高到和經濟發展,甚至高于經濟發展的地位上來,是將解決社會矛盾、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作為人類未來最重要的任務。
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失敗
1980年,美國保守派共和黨人里根贏得總統選舉。那時,美國人中最富裕的1%占有美國GDP的9%。在金融危機前夕的2007年,9%上升到了23%。這無疑是一段劫貧濟富的歷史,它與政府對金融市場的錯誤監管、政府肆意的財政政策緊密相關。
近期,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經濟危機的擴散,美國中產階級比例從2001年的54%下降到2011年的51%。難怪美國人正對未來喪失信心。
2008年,有54%的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子孫后代將會享受更高的生活標準。到了2011年,只有43%的美國人有同樣想法。這屬于質變,而且是朝著糟糕的方向。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未來的經濟發展和政策將愈發難以掌控。而陪伴這一切的,恰恰是中國和其他新型經濟體的飛速發展。
至于將手段與目的混為一談的新自由主義,它就是災難的必備要素。人類必須摒棄這種偏執的所謂正統經濟。最近的危機,按理說應該對人們有所警示。但奇怪的是,它并沒有。
世界人口已突破70億,而且在未來35年間將增長至90億。伴隨著廣泛的不平等和矛盾、眾多無法調和的價值觀和理念,那時的世界絕不可能像今天北歐國家現在的樣子。
如果可持續發展能夠得以實現的話,至少那時的世界可以少一些矛盾,多一點進步。我常說:“完美世界雖不可能,但值得去爭取。”
應該看重幸福指數
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可以為很多國家提供借鑒,西方稱之為“北京共識”。然而,中國目前仍高度依賴經濟增長,同時面臨諸多新的問題與挑戰。最大的問題是嚴重且不斷加劇的收入差距。解決這個問題已不應再繼續拖延。這一趨勢必須通過政策手段加以逆轉,因為完全放任市場運作,也會加劇社會的不公。
因此,未來世界共同的經濟發展戰略,既不會是幫助一些發展中國家崛起的“北京共識”,也不是現今過氣的“華盛頓共識”。
新自由主義做了少許妥協,并仍在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繼續發揮作用,更成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的得意主打。但愿他失掉競選,但愿美國也會朝著一個更加著眼于社會的發展戰略邁進。
中國可以向“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學到很多。中國可以從現階段升級演變為一個基于市場、服務社會的新型經濟體,這樣對自身和世界都將大有裨益。
現在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新興市場國家”,一方面應該學習中國,另一方面也應該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盡管這些國家情況迥異,包括巴西、波蘭,甚至加拿大和瑞典。
他們可以甚至應該從彈丸小國不丹取經。不丹的社會和經濟戰略是建立在“國民幸福指數”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這個有趣的概念上的,而非國民生產總值的最大化。盡管并不富裕,但那里的人民幸福指數絕不亞于西方最富有的國家。
向中國學習“實事求是”
未來國家的發展,在方向上應為“關注社會”,在方法上應為“兼收并蓄”。因此,我更提倡根據本國情況來制定發展戰略的新實用主義。從別國學習經驗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必須要考慮各國具體因素:地理位置、文化、歷史、資源、現存結構制度等。萬靈藥并不存在。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的政策是非常實用的:許多問題被一步步地解決,國家的GDP每7年左右翻一番。與此相反,美國的經濟政策遠非務實,并已帶來深重的危機。
正統主流的經濟學都是明日黃花。新實用主義需要汲取各種流派有用之處,不論是新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新制度經濟學,還是行為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抑或是正統自由主義,都可以揚長避短,兼而用之。
如今,越來越多的挑戰已經無法在國家層面上解決,即便對于中美這樣的大國也是如此;也無法在地區層面解決,例如歐盟或東盟。因此,提倡新實用主義,理論上不僅要考慮傳統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也要考量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的超級經濟學。而在實踐中,也需要全球范圍內務實的政策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