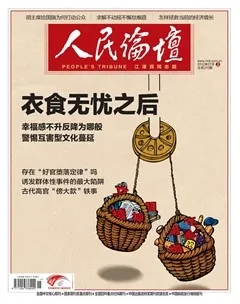“國家資本主義”標簽不能亂貼
2012年4月在瑞士達沃斯,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稱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及其“補貼和扭曲”對中國的貿易伙伴們“非常有害”,美國總統奧巴馬此前在其國情咨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在此以后,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責甚囂塵上,仿佛“國家資本主義”真的就成為了討論中美經貿問題的“標準語言”。
西方對中國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橫加指責
2012年1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集中刊發了六篇一組的“國家資本主義”專欄文章。同月,瑞士達沃斯論壇期間也組織了一場關于資本主義的辯論。這些文章和辯論傳播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即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新興經濟體在搞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借助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控股或參股公司、國家主權基金以及國家支持的私營公司等,積極并購外國企業,爭奪資源。這些國家熱衷于自主創新等經濟活動,嚴重威脅到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具體到中美經貿關系上,一些評論家更是直接地表示,中美的競爭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兩種經濟模式的競爭:市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例如在今年1月份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凱雷集團的大衛·魯賓斯坦就提出了一個得到廣泛認同的觀點,即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在超越美國的市場資本主義。“我們得解決這些問題”,魯賓斯坦說道,“否則,在三、四年內,我們賴以生存并視為最佳的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將會終結”。由此我們看到,原本中美兩國之間正常的貿易摩擦、經濟矛盾、利益分歧被演化成為“國家資本主義”與“市場資本主義”之間命運攸關的競爭了。
在這場被鼓噪得沸沸揚揚的爭論中,當這些西方的經濟學家和政客們不假思索地對中國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橫加指責的時候,卻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中國是一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從來都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和基石。雖然中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就堅定不移地選擇了走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但這與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壯大并不矛盾。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市場經濟的路徑依賴,才使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瀕臨絕境的國有企業絕處逢生、煥發活力、壯大成長。顯然,在這里,西方的經濟學家和政客們簡單地將中國的國有經濟與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劃上了等號。
西方指責令人難以認同
那末,什么是國家資本主義呢?簡單地講,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指與國家政權相結合、由國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種資本主義經濟。它的性質和作用取決于國家的性質。這一經濟形態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運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運用。兩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于所屬國家政權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以及由什么樣的社會主體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國家以絕對的政治權力和強大的公有經濟為前提和基礎,有能力加以限制和規定其活動范圍的資本主義。
相形之下,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重點在“國家”,通過加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政策調控,力圖減少經濟波動和經濟震蕩,應對和化解經濟危機。2007年以來美國政府對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風暴的治理以及當前歐盟政府對于歐債危機的挽救,都是西方國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調控經濟的生動案例。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重點則是在“資本主義”,旨在充分引進和利用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市場、管理經驗等各種要素,通過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富民強國的美好愿景。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確認了我國當前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以后,通過引進外國資本,扶持民間資本發展國民經濟,強國富民,已成為振興國民經濟的基本國策。
然而,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那些西方經濟學家和政客們所談及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我們上面所討論的國家資本主義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近期以來在業內和媒體上西方人所熱衷于談論并對中國橫加指責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指的是我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他們刻意抹煞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征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本質規定,再隨意貼上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進而進行不負責任的討伐,令人實在難以茍同。
要沖破“國家資本主義”偏見的藩籬
將中國的國有企業視為“國家資本主義”,并將中國國有企業的正常發展視為“補貼和扭曲”,反映了美國政界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傳統的思維定式以及認知程度上的無作為。
眾所周知,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獨特之處,首先不在于它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也不在于它是30多年來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而在于它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所謂“中國模式”的政治特征,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持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所有制結構,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物質財富的增長,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
而作為公有制的具體體現,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與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政府通過直接投資、要素分配、政策調控等方式調控國有企業的運行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具體實現方式,是人民利益得以保障的基本體現。這和西方政治術語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根本就是兩回事。
美國的政客們并非幼稚地連中國經濟結構的這點基本特征都不知曉,否則就不會在放寬對華高新技術出口管制、武器出售以及完全市場經濟國際地位給予等問題上設置障礙、公然歧視、不守信諾、出爾反爾,一直到前不久結束的第四次中美戰略與貿易對話依然如此。為什么一看到中國國有企業的成長,就把中國經濟結構的政治特征拋到九霄云外了呢,這難道不是明顯的雙重標準嗎。
應該指出的是,我們強調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與核心作用,與非公企業的發展壯大是并行不悖的。所謂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從單一的公有制向多種所有制結構轉變的過程。這一改革到目前為止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事實上,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公有企業與非公企業數量的消長變化都不是目的,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利根據自己國家的核心利益和戰略目標來實施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安排。就如美國政府在2007年爆發次貸危機和金融風暴以來所實施的一系列強化政府調控和對相關產業進行救助扶持的政策措施一樣。為什么無論是像美國、歐盟、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還是像東歐的轉軌國家都可以在國有化與私有化之間進行頻繁、隨機的政策轉換,而一到中國的場合,便成為了什么“國家資本主義”泛濫呢。顯然,美國政客的指責既不客觀,也不公平。
還應看到的是,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廣大的社會公眾,對于中國國企的行業壟斷和利潤分配問題,向來給予高度的重視,并積極采取切實有效的舉措來打破由于歷史和體制因素所形成的國企壟斷,并不斷增加社會公眾分享的國企利潤份額。中國經濟的崛起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客觀事實,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是中國的幸事,也有利于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的發展。因此美國政府在處理中美經貿關系的時候,必須要有創新思維,信任對方,尊重對方,平等相待,沖破“國家資本主義”偏見的藩籬,才能在合作競爭中開創互利雙贏的新局面。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馬靜 美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