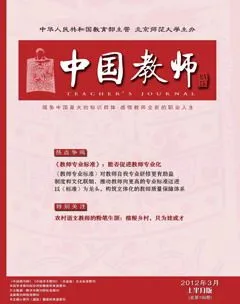教師倫理知識的養成與生長
《倫理型教師》[加]伊麗莎白·坎普貝爾著,王凱,杜芳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文中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引自此書。
近年來,一連串的教育事件和問題將公眾的目光聚焦于教師專業倫理與職業操守。例如,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個別中小學教師“課堂留一手,課外去創收”等有違師德的行為;西安某小學給差生戴“綠領巾”的鬧劇…… 我們不禁要問: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何以屢屢做出違背專業倫理的事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著名教師教育專家伊麗莎白?坎普貝爾(Elizabeth Campbell)的《倫理型教師》(The Ethical Teacher)為我們提供了答案:教師缺乏專業倫理知識,沒有用倫理的透鏡來審視教學行為。
“教師倫理知識如何養成”是坎普貝爾撰寫《倫理型教師》一書的主要議題。該書充滿了真實的、引人注目的案例。作為一名曾經的英語教師,坎普貝爾將關于倫理知識、道德實踐的討論置于教學實踐的具體場景之中,并結合親身經歷與具體案例,闡釋了倫理知識的內容,分析了教育教學實踐中教師面臨的倫理困境,并論證了倫理知識何以“更新教師專業素養的觀念,改變學校文化,改善教師教育”。
一、教學活動的倫理色彩與教師的雙重承諾
在以知識為中心的學校教育中,教學被看做純粹的技術活動,倫理問題往往被人們忽視。然而,在教育教學實踐中,教師不僅傳授知識,更傳遞道德信息,倫理色彩是教學活動的“底色”。因此,作為道德實踐者和教育者的教師,必須承擔雙重義務,做出雙重承諾:承擔道德教育的責任,并首先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1.教學活動的倫理色彩:以倫理的透鏡來審視教學活動
實踐中教師往往從教育技巧、教育策略的角度來審視教學活動,而忽視了其倫理色彩。實際上,“教師在課堂上所采取的所有行動都具有潛在的道德意義”。教育教學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活動,更是一種倫理活動,這就要求教師必須具有“道德的眼光”,學會通過倫理的透鏡來重新審視教學活動。
教育教學的特殊性在于其對象是鮮活的人。透過“交往”來理解教學活動,會發現“道德側度是一切教育活動本身一個內在的、必然的側面”。[1]因此,一旦通過倫理透鏡來審視學校教育中經常出現的“小組活動”“成績排名”等教學活動,教師就會意識到教學活動的倫理色彩,從而“將探尋教學倫理知識,作為自己的職責”,避免讓學生受到倫理上的傷害。西安某小學的“紅綠領巾”事件的出現,其根源就在于教師缺乏對教育倫理的敏銳意識。
2.教師的雙重承諾:一個有道德的人和道德教育者
“教學活動本身充滿著道德意義”,教師應是道德實踐者。與普通人相比,作為道德實踐者的教師更要有一個雙重承諾,“既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又要做一個道德教育者,而且通過將兩者結合起來,當仁不讓地成為美德行為和態度的示范和榜樣”。
“個體美德是通過與具有美德的人交往而習得的”。教師個人的品質、態度和操守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行為。因此,教師個人品質是教師道德實踐的核心,教師必須是一個具備良好美德的人。但是,教師的道德倫理是否要高于普通公民,這是2008年“范跑跑事件”帶給我們的困惑。對這個問題,坎普貝爾認為,教師的專業倫理精神是建立在已經達成共識的一系列美德的基礎之上的。由此看來,當面臨道德情境時,一個普通人都要承擔倫理上的責任,更何況是身為道德教育實踐者的教師呢?
道德教育即道德實踐,二者融為一體。“以倫理的視角看待具體的課堂事件,在每天的學校生活中,教師都不斷地進行著道德教育”。基于教學情境的復雜性,身為道德教育者的教師,即使有強烈的道德信念,也無法避免其具體行動在倫理上產生的問題。例如,許多教師熱衷于懲罰學生抄寫《中小學生行為規范》,殊不知這種無謂的抄寫有百害而無一利,只會增加學生對行為規范的厭惡。可見,教師在工作中經常面臨著專業倫理的挑戰。
二、實踐中教師面臨的倫理難題與困境
坎普貝爾反對道德相對主義,認為教師要“明辨是非”,并提出了教學活動的幾個核心道德原則。即使教師們認同同樣一個道德原則,但對于如何將這個道德原則運用到具體的教學場景中,不同的教師總會有不同的判斷、不同的選擇。學校和課堂生活的這種倫理上的復雜性、不確定性與偶然性,使得教師必須掌握專業倫理知識,以指導倫理決策。當教師倫理知識枯萎時,教師就會面臨各種道德兩難困境、緊張關系和挑戰。
1.不道德的學校行政管理活動引發的倫理困境
坎普貝爾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成為教師意味著必須學會向那些可能在課堂上對學生造成傷害的制度和常規讓步嗎?”教師是無須恪守倫理的專業人員,但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學校管理者、行政命令、教育政策卻常常使教師陷入倫理困境。當學校行政管理活動、校長的行政命令明顯的“不道德”,并可能衍生出一系列問題時,教師會陷入良心與學校規范之間拉扯的倫理緊張關系中,感到被撕裂,道德焦慮感倍增。在這種大氣候下,教師可能會“放棄他們的道德敏感力”,喪失尋求倫理道德的勇氣。
2.家長的卷入給教師增添了道德挑戰
家長是學生的延伸。教師對學生的責任會延伸到對學生家長的責任。隨著家長文化素質的提高與“家校合作”理念的推廣,家長對教學的干預越來越頻繁。教師在承擔倫理職責時,無法脫離家長的影響。但是,家長的卷入無疑給身為倫理專業人員的教師帶來了道德上的挑戰,削弱了教師倫理上的權威。當教師和家長在教學方法、理念和目標等方面出現矛盾和沖突時,教師應該如何處理才能既維護教師專業權威,又照顧家長的感受呢?坎普貝爾指出,“幾乎大多數沒有得到解決的倫理沖突都涉及教師與家長的關系”。實踐中,教師常常面臨一個難題:“是否要將學生的情況如實告訴家長?”如實告知,學生可能會受到家長懲罰,而如果隱瞞和撒謊,又違背了“誠實和對家長負責”的原則。
3.同事忠誠和群體壓力常常成為教師倫理困境的來源
鑒于教師的專業地位,長期以來盛行“教師不應該干預其他教師的事務”的觀點。對此,坎普貝爾并不贊同,她提醒我們,這種信念會使教育教學實踐陷入嚴重的倫理危機。有時教師明明知道同事的行為會給學生造成倫理上的傷害,但是他們因為不愿意成為“內奸和密探”或害怕來自教師工會的懲罰和處分,往往會選擇“綏靖政策”,坎普貝爾將教師的這種狀態稱為“懸置道德”(Suspended Morality)。筆者認為,作為旁觀者的教師,不應該屈服于這種“集體暴政”與教師工會的壓力。因為當學生面臨危險時,同伴忠誠不能成為逃避責任的借口,教師捍衛公眾利益的職責比維系同事關系和個人利益更為重要!基于倫理道德而指出同事行為中存在的倫理問題,應該被理解為一種關心,而不是一種攻擊!教師應鼓起道德的力量,和不道德行為據理力爭,這樣才能堅守專業的尊嚴。
三、成為倫理型教師:教師倫理知識的養成與生長
教師的專業身份已獲得普遍認可。但是,教學情境的復雜性、倫理問題的隱蔽性和不確定性,導致教師時常面臨難題和困境。教師要想以專業自主的名義掌控自己,就必須努力提高專業素養,運用倫理知識指導倫理決策,應對道德沖突。“倫理知識是教師知識的基礎”“專業首先建立在倫理規范基礎之上,技術能力不足以確保專業的行為”。我們必須掌握倫理知識,將其作為一種嶄新的知識結構,使之成為教師專業素養的基礎。
何謂“倫理知識”?倫理知識本質上是個體處理倫理問題所應具備的專業素養。倫理知識讓教師能夠自覺地用倫理眼光審視日常的教學活動,發現其中蘊含的倫理問題。倫理知識讓教師能夠將核心道德原則與復雜的教學情境“對接”起來,建立某種實踐的聯系;同時激發教師的道德勇氣,解決倫理難題。培養倫理型教師的本質就是促進教師倫理知識的養成與生長。
1.在倫理實踐中培養教師的倫理知識
要想確保教師的行為符合專業倫理和精神,首先必須設立教師專業倫理規范和標準。我國教師倫理規范一直沿著“師德—師道—現代專業倫理規范”的路徑演進,[2]卻始終沒有解決現實問題,在指導和幫助教師處理他們工作的道德復雜性時不起作用。我們不能寄希望于倫理規范,幻想一勞永逸地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倫理難題,因為倫理規范是一般性的,而教學情境卻是復雜的、不確定的。坎普貝爾指出,只有在倫理實踐中,才能培養教師的倫理知識。“實踐知識是對倫理知識的適當描述”。在倫理實踐中,教師應當擁有一個共同的倫理愿景——“通過他們的實踐來尊重倫理原則與美德”,從而將抽象原則與具體情境聯系起來,最終增強教師解決倫理難題的能力。
2.培育倫理型學校文化
實踐中,大多數教師都是獨自面對倫理困境和難題,缺乏同事和學校文化的支持。因此必須將“倫理知識帶入到更廣泛的教學專業文化之中”,學會創造倫理型文化。首先,要重視“對話和共享”的作用。教師們共享倫理知識,讓倫理知識成為關注的中心;建立“開放論壇”,讓教師與家長和行政人員共同討論其經歷的倫理困境,為培養教師的集體倫理知識、解決倫理難題提供一個途徑。其次,坎普貝爾重視校長等行政人員的作用,她認為,校長自身應該具有倫理意識,“通過在學校確立和保持倫理基調”,促進教師道德意識的成長。總之,應該培育倫理型學校文化,讓“倫理知識彌散在環境之中”,在學校塑造一個“道德社群”。
3.變革教師教育課程
教師教育是培養倫理型教師、促進教師倫理知識的養成與生長的關鍵階段。但是,目前教師教育課程側重的是教育技能的培訓,在幫助教師解決教學中的倫理困境方面,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教師教育實踐應該成為“培養倫理型專業素養的核心活動”。在教師教育課程中,通過“個案報告系統反思法”,對教學活動進行倫理上的分析和討論,喚醒“準教師”對倫理知識的重視,同時將核心倫理原則與具體教學情境相聯系,提高“準教師”倫理實踐的能力。坎普貝爾關于改善教師教育課程的建議值得我們借鑒。
4.回歸個體:激發教師的道德勇氣
《倫理型教師》的焦點并不在制度,而是作為道德實踐者的教師個體。前面已經提到,實踐中,面對學校不道德的行政命令(如紅綠領巾事件)、同事不當言行(例如體罰學生),很多教師常常不敢抵制或出面阻止。實際上,正如坎普貝爾所說“真正改變的能力掌握在教師手中”,教師作為專業人員,應該是一個自主的道德主體,能夠執行倫理判斷。她勉勵廣大教師,“當制度或學校仍舊頑固地維持不道德狀態時,教師個體要鼓足勇氣,堅持倫理上正當的行為,即使因此遭受人身或專業上的痛苦”。
四、結語
“教師是教育之本”,而教師倫理與職業精神是教師專業素養的基石。目前學校教育的功利化、師德的滑坡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如何培養倫理型教師”成為我國學校教育不能回避的難題。而《倫理型教師》十分及時而貼切提出了“傳承與分享倫理知識”“創造倫理型文化”等真知灼見,對我國的教學活動、學校管理和教師教育變革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此外,《倫理型教師》是一本教育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著作,書中有很多作者的親身經歷和典型教學案例,對于中小學教師而言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倫理型教師》向廣大教師提出了召喚:“在倫理追尋中,鼓足道德勇氣”,促進倫理知識的養成與生長,成為一名倫理型教師,成為你能夠成為的最好的教師。
參考文獻:
[1]項賢明.泛教育論——廣義教育學的初步探索[M].太原:山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