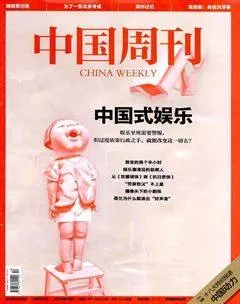“熒屏怒漢”不上星
2012-12-29 00:00:00閆小青
中國周刊 2012年10期

電視主持人鐘山有兩個演播室,在上星的演播室中,他溫文爾雅、傳播正能量;在不上星的演播室中,他抨擊丑惡,被稱為“熒屏怒漢”。
“鈴鐺一響,鐘山開講。”
晚上六點半,湖南經視頻道《鐘山說事》演播廳監控室的LIVE(直播)燈準時亮了起來。每次說完開場白,屬于鐘山自己的一小時,就開始了。
在《鐘山說事》的演播廳里,不用溫吞水地對著提詞器背書,不用阿諛自己不滿的社會現象,說到氣憤可以唾沫橫飛、拍桌子、丟鈴鐺。
“沒有上星的資源和影響力,反倒贏得了更大的空間。”從演播廳回到辦公室,鐘山從煙盒里抽出一根煙,在辦公桌上敲了兩下,開玩笑地說:“現在都有人從北京跑來采訪了,看來我們得考慮生存問題了。”
怒漢走紅
四個月前,在湖南省以外還沒有多少人聽說過《鐘山說事》這檔節目。
2010年12月,湖南經濟電視臺臺長周雄邀請鐘山到湖南經視頻道開辦一檔新聞節目。周雄給鐘山提的要求是保持“怒漢”的風格,而鐘山的要求則是自己做制片人。兩人一拍即合,一個月后,《鐘山說事》開播。
這原本是鐘山設想中的偏安一隅:做一檔能保持自己風格的地方臺新聞節目,說自己想說的話,給百姓辦點實事。沒想到,一期拷問高考制度的節目讓《鐘山說事》闖入公眾的視野。
6月11日下午六點,鐘山穿著T恤衫、休閑短褲走進演播間,拿起搭在提詞器上的襯衣和西裝,一邊換衣服一邊往座位上走,同事上來整理了兩下鐘山的頭發。
“化妝”完成了,一邊等待調機位,鐘山嘻嘻哈哈地跟同事調侃著“熒屏怒漢”不需要花時間在臉蛋上。
“熒屏怒漢”是觀眾送給他的外號,做電視節目主持近十年,鐘山的大多數節目里講的是一些不平事,而面對這些不平事他一定是一臉怒氣地吹胡子瞪眼睛。
離直播還有不到半分鐘時間,演播室安靜了下來。“五、四、三、二、一,開始。”
叮……鐘山搖了搖鈴鐺,“鈴鐺一響,鐘山開講。今年高考剛剛結束了,縈繞在我們周圍有很多讓你感動讓我心酸的事兒。”
鐘山胸有成竹,他要對高考開炮了。前一天晚上,他甚至不用點煙就寫完了稿子,現在他只需要像往常一樣把情緒發泄出來。
鐘山吐字的速度快得像一桿沖鋒槍在掃射。“……我不知道一個考試能有多么重要,能讓父母強顏歡笑,隱瞞親人去世的死訊,甚至不惜讓孩子錯過與媽媽爸爸最后的訣別;我不知道一個考試究竟有多么重要,為了走進考場,甚至不惜讓孩子無奈地離開倒在血泊中生死未卜的媽媽;我不知道一個考試有多么重要,能夠讓母親不顧個人的尊嚴甚至不惜給監考老師跪下只為央求讓自己遲到2分鐘的孩子進場考試!這些事情從某個角度看,人們看到的也許會是感動,但是,換個角度,鐘山我看到的卻是人性的扭曲,沒有人情、沒有親情的癲狂和癡迷……”
十天后,12分鐘的“高考天問”在網上瘋傳,這段沖鋒槍播報被稱為最有血性的主持。一天時間,轉發數過十萬,評論近兩萬,欄目組的熱線忽然間像炸開鍋一樣。
面對突如其來的關注,身兼制片人的鐘山卻顯得格外清醒,“我只是把一些舊聞和數據整理出來拿到電視上說,引起的效果卻好像往糞坑里丟了一顆手榴彈。只不過是觀眾見慣了教條似的主持人,見慣了屏幕里的和諧社會。我全當是拋磚引玉了。”
找個地方“說事”
每次從演播室里走出來,點上一根煙,鐘山就會從各種情緒中恢復平靜。“有這樣一檔黃金時間直播的新聞節目可以說真話,表達自己想表達的,也夠了。”
1995年大學畢業,鐘山成為一名雜志的編輯。之后,他又到電臺擔任午夜主持,節目談的是愛情,而他卻在節目里喜歡放自己寫的歌來慰藉青春。
2003年,鐘山決定正式跳入電視界,以為自己會打開一片全新的電視天空。他只身一人去浙江、去廣西尋找適合自己的地方,卻發現主持人更像是一部讀稿子的復讀機。他只能原封不動地讀別人寫好的稿子,哪怕知道里面說的是假話空話。因為控制不住情緒說了自己想說的話而道歉、寫檢查成了鐘山的家常便飯,好在他的節目收視成績一直遙遙領先,飯碗總算是保得住。
終于有一次他爆發了!
2010年的一天,浙江電視臺錢江頻道《九點半》的演播廳里,鐘山正在談論44.8萬民辦教師被最后清退的新聞,他越說越憤怒,后來就完全不顧已經寫好了出現在提詞器上的字幕。
“身份!身份!什么身份!我就不明白為什么明明是一樣的工作一樣的奉獻,卻因為不一樣的身份就要接受這種極端極端不公平的非人待遇呢!”
鐘山回過神來,他按著提詞器把節目接下去:2009年有媒體報道人力資源和保障部正研究將同工同酬寫進法律,結果后來證明這條報道是假新聞。
他拍案而起,將手里的講稿團成一團,直指屏幕,“老爺們!你們要什么時候才能讓同工同酬真正實現啊……這件事情就五個字:民族的悲劇!”
就是那一次,鐘山得了“熒屏怒漢”的稱號。幾天后,他在收視慶功宴上被領導狠狠地批評了一次。
晚上,鐘山和好友一起去西湖,他指了指前方說,他清楚自己的熱土不在這里。他心中的“熱土”是,“你一想到它就渾身激動,就覺得活著有了意義,全身的毛孔都要張開,所有的血就要噴出來。你離開它就沒法呼吸,你進入它就像鳳凰涅槃,重生了!”
2011年1月1日,鐘山坐早上的飛機離開了杭州,回到老家湖南。
不想上星
他的新東家是湖南電視臺,可主打節目《鐘山說事》的播出平臺,不是全國任何地方都可以收看的湖南衛視,而是只能湖南地區收看的湖南經視(湖南經濟電視臺)。“在地方臺,我可以自由地表達我的這些觀點,你同意的話你就捧我了,你不同意的話你就拍我了。一捧一拍之間,我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總比沒人去碰這個問題,讓它老死發霉發臭的好。”
“高考天問”在網絡大傳播之后,不少同事希望這檔節目影響力更大些,比如在湖南衛視播出。
鐘山從來沒指望這檔節目可以上星播出,“第一要務是活著。這樣的節目別說是在衛視直播,就是錄播也不可能。”
實際上,身兼湖南衛視《平民英雄》主持人的鐘山最清楚上星對《鐘山說事》而言是自尋死路。“《平民英雄》是那種傳遞正能量的節目,在衛視頻道你只能找到這樣的節目”。
起初加盟湖南衛視的時候,有人說希望他犀利的風格可以給節目帶來新的生機。鐘山毫不客氣地說,“這很難”。2006年,鐘山受邀擔任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職場聚議堂》主持,雖然獲得不少好評,但鐘山自己知道他的風格沒有了,他的位置是很多人可以替代的。
《平民英雄》制片人羅典雅看中鐘山是因為他會說故事,“本就是溫暖的故事,如果再用溫水式的方式灌輸出來就沒有看頭了。”
而鐘山自己看來,他在《平民英雄》唾沫橫飛、言辭擲地有聲的說話方式,也許是最合適調動觀眾情緒的富有激情的表達方式。
主持《平民英雄》的時候鐘山是完全放松的,“因為它比較單純,上星頻道需要所有的內容都是陽光的,絕對不會去超越什么限度。”在衛視頻道,鐘山不必擔心自己會犯錯。“而《鐘山說事》是完全不一樣的,它把一些丑惡的東西說出來,當頭棒喝。我腦子里永遠繃著那根弦。不要踩線、不要過度。”
盡管做《鐘山說事》提心吊膽,鐘山仍然覺得自由得多。開播近兩年,臺里領導很少槍斃他的選題,節目的安排也全由他做主,也可以偶爾打個擦邊球。
年初,湖南衛視節目調整,衛視頻道考慮抽調了湖南經視的優秀節目上星。《鐘山說事》的收視率和口碑都很不錯,雖然知道上星的可能幾乎為零,鐘山還是連著幾個晚上睡不著覺:如果上星了,等著它的命運不是被包裝成娛樂節目,就是變成復讀機。
過完農歷年,風聲過去了,自始至終《鐘山說事》沒有出現在考慮范疇內,鐘山松了一口氣。
“生存是最重要的,說話的權利比什么都重要。”
“逆天”
每天下午六點回到《鐘山說事》的演播廳,是鐘山最舒服的時候,“這才是我的地盤”。
當然,也有一些時候因用力過猛超出了他的預料和控制。
8月21日,在國內的大部分媒體與官方保持了一致的步調,“確認”周克華被擊斃的時候,鐘山以“槍響了,出事了,忙活了”為題羅列公眾對重慶警方的質疑,呼吁警方盡快回應。欄目組派了記者到重慶警方擊斃周克華的地點核實公眾對于攝像頭為何沒有拍到畫面的質疑。
質疑、監督這是鐘山做新聞評論一貫的作風。演播廳里,鐘山的怒漢情結又被激發了:“我們的記者現在就在攝像頭的下面,等著重慶警方的一個解釋……無論官員公布的是不是真相,都要懷疑;無論政府推出的是不是善政,都要懷疑……懷疑不是壞事,每個公民都有懷疑的權利,每個人都曾經或正在懷疑,將來還會懷疑。懷疑是因為關心,懷疑是因為有疑,懷疑是因為疑問沒有及時解答!”
但是這一次,《鐘山說事》在博得掌聲的同時,卻把火頭燒到了自己身上。節目播出第三天,網上有帖子稱,這期節目是湖南警方和重慶警方爭功的產物。
看到這樣的帖子,鐘山真的慌了。他原本想借公眾質疑警方的話題講講質疑的權利和公權力的信任問題,卻被曲解為權力斗爭的陰謀。“這等于給節目自掘墳墓呀。”
自從“高考天問”之后,《鐘山說事》不斷地網友貼上各種標簽,其中最常出現的一個詞是:逆天。
“高考天問”,逆天。
“槍響了”,逆天。
“北京雨災——汪洋中的城”,逆天。
“那些與金牌有關的眼淚”,逆天。
鐘山把“逆天”看作是贊揚,他把這個詞看作是肯定節目敢說真話、敢于挑戰權威、有血性。
亢奮時的鐘山,他會跟身邊的人說:“每個媒體、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應該對這個國家會有自己的態度,你愛這個國家,所以才不能容忍這個國家的缺點。問題就在那,你逃避、不去碰它,它就永遠不可能解決。”
當然,平靜下來的鐘山又會跟同事講,諫言是要講究方式的。
8月15日,看到新聞聯播里對釣魚島的明確表態之后,鐘山才把早已經打好腹稿“寸土不讓,保衛釣魚島”敲了出來。
“區別不過是自由的度,沒人逃得脫。”鐘山吐出一口煙,一笑,“既然逃不脫就看誰玩得轉,這叫儈策(湖南方言,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