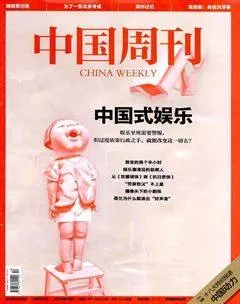風過留痕
風是再平常不過的自然現象了,無論是微風習習、狂風大作、寒風席卷,還是臺風襲擾,都是我們生活里常常會聽到甚至在路上會遭遇的。
自然界沒有一無是處的元素,存在就是合理就是必然。夏季頻仍的龍卷風威脅沿途的交通和民居。甚至摧毀水利工程,但是卻帶來了豐沛的降水,滌蕩了污濁的空氣;冬春季節強寒流吹來的沙塵暴,毀壞了干旱區的良田,卻在它處造就了沃野千里,在海域為漁業提供了豐富的營養物,吸附并洗涮了空氣中懸浮的污染顆粒物。
悟道者認為風過無痕,是把那些久積的憤懣從內心深處帶走。行路者觀風,則往往會被風過的痕跡所感染甚至折服。
走過沙漠戈壁地區的人一定看見過各式各樣的沙丘、千姿百態的風巢崖和千奇百怪的風棱石。寧夏中衛縣的沙坡頭,是世界級的人工治理沙漠的范本,原本由單一風向塑造的新月形沙丘鏈以及規模不等的復合型沙丘,有規律的由西北向東南方向呈雁行式排列,猶如無數列橫臥的火車,在蒼茫大地間,年復一年的在狂風的驅使下,向東南依次推進。智慧的當地人發現,與其想阻擋高空氣流的侵襲,不如堅壁清野,利用易得的秸稈或者藤條。在沙丘上編織密密麻麻的網格,再狂躁的急流也無法輕易推動沙丘的移動。
到過甘肅敦煌鳴沙山的人,可曾想過干旱造就的沙山怎么就與月牙泉這汪淡水世代比鄰而居?干旱與清潤相鄰最極致的景象其實在內蒙的巴丹吉林沙漠。這里有西北風和東南風季節交替而形成的金字塔形沙丘,最高的丘頂高過地面近600米,堪稱世界之最。最神奇的是在上千的金字塔形沙丘間,散布著近150個大大小小的湖泊。夏季晨起或者日暮的光輝,在閃耀著金色的塔頂劃過,剎那間就又投入蔚藍色的湖水,沒有人不對這樣的自然勝景動容。
阿爾金山的小沙子湖及其周邊環繞的復合型沙山,堪稱風在高海拔地帶的又一力作。西風急流掠過4500米的高原面,將其地表的松散沉積物進行主動篩選,細小的沙粒被吹卷積至山巔,僅20年時間,沙山的面積就擴大了一倍,曾經的道路都被掩埋。唯有承壓的上升泉眼四周保持通達,近乎極限狀態的沙坡構成高達200米的圍欄式峭壁。每當斜陽西下,總有威猛的雄性野牦牛帶領成群的妻妾和兒女,來到小沙子泉飲水、集聚和過夜。
風裹挾著沙粒還對裸露的巖石進行鉆蝕,長此以往,崖壁就會出現蜂巢狀景觀。這些巢道都是口小腹大、上緊內疏,蓋因高速風以旋轉的方式致使沙粒嵌入巖石并回旋推進。在新疆的大阪城、青藏線的風火山口、昆侖山的當金山口、新藏線的甜水海都能看到路邊高過百米的這種崖壁,尤其是越是堅硬如花崗巖的地段,巢穴越發達,景觀的氣勢越宏大。南極洲是風暴的故鄉,這類風巢崖壁在南極任何逃脫冰雪控制的地區隨處可見,在中國南極中山站莫愁湖南山,巢道的縱向深度可以達到6米,這就是風的力量。
風過大地,還是地球化學元素產生物理性的分化和淀積。酒泉到敦煌之間有一片上千平方公里的黑戈壁,宛如人工涂刷的黑色油漆,就是風壓導致錳等黑金屬再次富集,這層薄而脆的涂層破裂就會露出戈壁的本來面目。風的摧蝕還會把戈壁灘進行新的排列,在甘肅、內蒙和新疆交界的三角地帶,有片瑪瑙灘,五顏六色的瑪瑙撒滿亙古的荒原,這是風力篩選的結果。定向風還使戈壁石發生迎風面箭矢化的適風現象,這種石頭不僅表明光亮如玉,而且刮削器狀的三棱體征,與舊石器時代的工具無異。
風過的痕跡在海濱、在雪原、在林海,都有不同的景像,這大概就是我們旅行的魅力,就在于不斷的發現未知,永不停步地尋找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