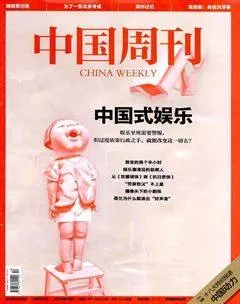頹廢的濃麗,就叫鄉愁
前一陣讀了香港作家陶杰的隨筆,只過心用腦的文字,實在又輕盈。
他說曾經的香港馬路上一道風景是印度女人的各種顏色。她們額頭正中有朱砂,而眼蓋膏常用的是靛藍色,穿著燙金的人字拖,濃艷得像有毒。她們喜歡湖水藍和玫瑰紅,這兩種放在印度女人身上還別有天方夜譚般的異國情調,令人想起克什米爾高原的藍天和果阿海邊的花園。一雙大眼睛,眼神卻冷漠而惘然。多年后,陶先生才明白,她們作為吉普賽人的分支,海角天涯一樣深遠的眼神流露的悲哀。
結尾一句特別好。我的眼光滑過,心里就震顫了。
讀過幾日,卻忘了結尾的那句。書借給了友人,苦思冥想,只能大致意會,好像是無可奈何的濃艷,是一份淡淡的鄉愁之類。
我不能原諒自己的記性。如此震顫的美文,怎么可以忘了?或許目光滑過的激動嚇跑了她?此后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花點時間回憶,像個記憶強迫癥患者。不肯翻閱原作,更拒絕有人提示,只待她自愿回歸與蘇醒。
記性不好,飯還是要吃的。
北方的夏季越來越有南方的熱濕,黏黏的空氣里聞得出空氣和水分。這個時候,無論你身居北方多少年頭,你的胃都會被迷惑,把全球變暖誤讀為重歸故里,沒完沒了地渴望著各色麻辣。
在夏天的北京做一頓蜀國的飯,對一個追求精準的廚房控來說還是充滿挑戰的。首先麻辣的原材料處于青黃不接。紅辣椒是去年的,新的要么尚未采摘,要么還在農戶院里的簸箕里曬著。普通人家廚房里的東西,除了泡菜,只要翻過年頭就剩下的便是折扣了,如同女人過了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一……
再說花椒,剛摘下的是青綠色的,曬過放熟之后逐漸變紅,色澤變化的過程,它的味道也在變化。
還有那個母親打來的電話,她說青花椒下樹了,要不要帶點來?輕描淡寫的一句要不要,勾出了不濃不淡的鄉愁傷感,花椒都熟了,又一年吶。
剛摘下的花椒,青青綠綠的,它給你的麻一點不世故,清澈得很,把你麻得人仰馬翻的時候,還覺得它像王菲,有些天籟的感覺。新鮮的剛曬干的紅辣椒是最好吃的,用它熗鍋炒出來的任何菜都有太陽的味道,率性,不掩飾,足夠辣,但辣得不欺負人,不會鼻涕眼淚的,像個美少年。
夏日北方的廚房真郁悶,把這過了氣的辣椒花椒放在一起,再拌點不咸不淡的鄉愁,怎么做都是欠缺。欠多少,能感知,卻很難把握。這種時候通常就會使勁。比如拼命放麻加辣,再使勁煮,以求口味的飽和。煙熏火燎的陣仗都是底氣不足的匹夫之勇。
朋友嘲笑說,這手藝最多在天橋下面擺個麻辣燙,就像一白遮百丑,一燙抵三鮮。
當然,沉下心來還是能找回些感覺的。
我先買來電扇,放在廚房,清風徐來,有些秋高氣爽。再買兩斤大蔥,拍松,切斷。紅辣椒用石臼略舂。用118元高價買回一只油雞,洗凈,切塊,用水焯一遍,再將雞塊上鍋,中火蒸一小時,取出立即上鹽,放入大蔥,再蒸30分鐘。再取出放入青椒和大蒜,比較多,再蒸30分鐘,再放入花椒蒸30分鐘,再悶30分鐘……繁復的過程,事事兒的。
味道怎么樣?真的,你一定要試一試,才會知道。
友人認真品味,說了一句,口感濃烈,但還是有些頹廢的味道。
我大喊一聲,想起來啦!
陶先生美文那句話是,頹廢的濃麗,就叫做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