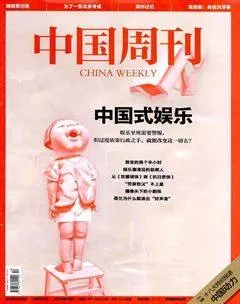鄭州記憶
2012-12-29 00:00:00田野
中國周刊 2012年10期




中原大地厚重的黃土之下,深埋著無數的文明與殺戮,但今天,這一切煙消云散,現代化的進程恍若在一張白紙上重新書寫。
五一假期,我在鄭州給父親置辦了一套新房。父母原本居住的鄭州郊區那個村莊即將要徹底被電廠的煙囪、轟隆隆的鐵路線,還有喧囂的商貿城淹沒了。兒時記憶中那個寧靜富饒的村莊已經不在,也不再適合作為父母的養老之所了。
當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過去,大躍進式的中國城市化進程終于輪到了鄭州這樣的中部城市。那些門類繁多的制造業工廠從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開始往縱深的中國腹地轉移,這些在漫長的農業文明中浸淫了的土地也隨之沸騰起來。對于大多數在這里生活了一輩子的人們來說,這樣的變化帶給他們的多半是興奮。在過去30多年東部沿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他們只是來去匆匆的打工者,如今,工廠終于開到了家門口。
在這場蓬勃展開的城市化運動中,鄭州這座多年前我曾經熟悉的城市變得陌生起來。這些年的異鄉生活告訴我,短暫的興奮過后,它給生活在這里的個體帶來的還會有拆遷、污染,以及并不總是公正的財富再分配,與沿海那些地方經歷過的不會有什么兩樣。
但父輩和兒時親朋們的興奮分明是真切的,我的惆悵也便顯得有些矯情。在糾結中,故鄉一點一點面目模糊起來。
從鄭縣到鄭州
我把父母的新居選在了城北,因為靠著邙山、黃河,很多鄭州人認為,那里是上風上水的風水寶地,但于我,只是因為離黃河更近些。嚴格說來,黃河不能算是鄭州的母親河,淮河才是,因為鄭州人喝的多是淮河支流的水,但地理上的接近,黃河也便成了母親河,更是這座城市的標識之一。
小的時候,是甚少去黃河邊的,光禿禿的黃河大堤漫長而枯燥,野草荒灘,實在沒什么可觀之處,也不招鄭州人待見,那個時候,人們多半認為火車站附近那些巨大的各式農貿市場、商場百貨才是鄭州。記憶中關于兒時鄭州最多的片段,就是跟著父母無休止地在各式零售百貨、批發市場里來回奔波,他們忙著做生意,我則忙于吃,豆腐腦、肉夾饃、冰糖粽子,還有回族人的羊肉串。
我18歲離開了河南,那些熙熙攘攘的市場年復一年地改造著,也消失著,漸漸也就無可懷戀了。偶爾看到關于黃河的影像,倒會不自覺生發出一絲懷鄉之情。地理意義上的景觀總是能最有效地承載人們的某種情感。于是,每次回去,得空總會去那條寬闊的黃河大堤上溜達,那里十幾年如一日的野草荒灘,到了枯水季,河道中厚厚的黃土,隨風揚起,漫天飄散,提醒著這個城市的底色,它建筑于被中華農耕文明史浸染最濃郁的中原腹地之上。
在現代城市的意義上,鄭州的歷史一點也不長。在20世紀之前,它都乏善可陳,直到1928年才正式建市,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拜清政府修建的那條京漢鐵路(如今的京廣線前身)所賜。
京漢鐵路為什么不選擇穿過當時的首府開封,不選擇更聲名遠播的洛陽,卻選在了當時位于這兩大城市之間的小縣城鄭縣?正史野史有很多說法,但比較可信的是《清史稿·交通志》上的記載,在當時工程技術和資金條件下,張之洞設計鐵路具體線路時,把黃河橋看做修筑京漢鐵路最緊要的環節。開封一帶的黃河,是著名的懸河,被稱為黃河的“豆腐腰”,如果選擇從開封建橋,不但投資大,建成后風險也很大。因此,京漢鐵路線路才拐了一個彎兒,從鄭縣附近的花園口穿過黃河南下,至于另外一個名城洛陽則偏西距離稍遠也被放棄。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當年張之洞筆下那道彎開啟了鄭州這座城市20世紀的城市化歷史。1949年以后,鄭州取代開封成了河南的省會,在那個全民勒緊褲腰帶搞基礎工業的年代,人們對于城市的想象便是工廠,鄭州也不例外,八大國營棉紡廠占據整座城市大半塊地方。鄭州最早的一批市民,除了少量郊區前來做小生意的農民之外,便是鐵路局和棉紡廠的工人了。在父輩們的描述中,對于那些能在鐵路、煤礦以及棉紡廠上班的被稱之為“正式工”的人們是艷羨極了的,他們這些來自郊區農村的小商小販頂多是在大工廠的門口賣賣水果蔬菜什么的。
不過,歷史的發展卻相當吊詭。到了1990年代前后,小商小販們的鄭州繁榮起來,而“正式工”的鄭州則日漸衰敗。那些年,鐵路局和棉紡廠區成了鄭州貧民窟一樣的所在,而各式各樣的購物廣場、批發市場則光鮮亮麗,人聲鼎沸,有個叫亞細亞的購物廣場甚至一度成為了這座中原城市最大的招牌,聲播全國。
我讀完大學才發現,我所成長的這座城市的歷史進程與沿海地區原來有著相當大程度的錯位。上海、深圳、廣州等城市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工業化才是城市發展最大的主軸,鄭州逐漸破產的那些原本優質的棉紡廠、自行車廠等等產業都轉移去了沿海城市。
大約經過了十年左右的時間,進入21世紀時,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化已近完成,到處都是林立的高樓,儼然一派世界都市的氣象。而鄭州這時候工業蕭條,幾乎蛻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農貿市場,各色批發市場和長途汽車站占據了城市的中心,終日里是無序的喧囂。也就是那些年,我開始越來越討厭回到這里,不僅僅是因為物理意義上的混亂,更有彌漫在整個城市里的狡詐、市儈和隨時隨地的坑蒙拐騙。
形態低端的商業模式并沒有給這個城市帶來足夠的富庶,卻孕育了最糟糕的社會氛圍,缺少起碼的法治觀念和商業倫理,機場、車站、飯店、商場等人流最多的地方里,那種底層社會間的互相傷害無時無刻不在發生。
那些年,河南人在外的形象相當糟糕,作為省會的鄭州怕是要承擔最大的責任。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想不明白,在鄉土社會的環境中,那么忠誠、敦厚、善良的人,何以進入城市后會變成另外一副模樣?或許這是人們脫離鄉土社會的熟人社區,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需要人際關系再造的環境,一段必不可少的適應期?
作為一個整體的鄭州,這種形象和文化意義上的自愈也是最近幾年才慢慢完成的。鄭州所經歷著的城市化是另外一種原生態的中國式城市化。它從農耕文明最深厚的中原腹地生發出來,撕裂著傳統,鍛造著另外一種形態的文明。
歷史也似乎是跟河南人開了一個玩笑,承載著一億人口的中原腹地,現代化生長并沒有從那些有著悠久城市史的地方開始,而是從一片白紙上起步。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應該歸功于那條京廣線。被這條鐵路線改變命運的遠不止鄭州一座城市,鐵路還塑造了另外一批新興城市,比如新鄉、漯河、駐馬店等。歷史上,中原曾是名城薈萃,比如洛陽、開封、安陽、周口、南陽等等,如今卻都因遠離了現代交通大動脈,而落伍于整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
拆出一個新城市
盡管千城一面的城市化進程已被批得體無完膚,但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以及城市的執政者來說,這一點也不能打消他們對美好城市生活的想象,而那些想象,無不是以已經建成的大都市為藍本的,遠的如紐約、東京、香港,近的如上海、深圳、廣州。
從城市需要高樓大廈、需要公路和立交橋、需要寬闊的廣場,到需要公園湖泊、需要綠樹和文化景觀、歷史底蘊,中國人的城市想象其實也在不斷完善,這些被需要的都要實現,有的就維護,沒有的就人造。
對這種主流的城市想象的追逐,鄭州和很多內陸城市一樣,大約是在2000年以后才開始的。那個時候,在這個城市的東部,政府提出來要建設一個新區,有超過150公里的耕地都被劃入其中,最終選擇的規劃方案是日本當代著名設計師黑川紀章提供的。
2005年,在還是一片荒地的新區,我曾經跟黑川紀童有過一次深入采訪。那時,他的設計方案正在遭受諸多質疑,其中最核心的一點便是他要在這個極度缺水的北方城市挖兩個巨大的人工湖。在我將人們的質疑轉述給他聽時,黑川紀章相當憤怒,“我們不能因為這里缺水,就不去挖湖,就像不能因為這里是沙漠,我們就不去種樹,人類生來本就是要改造世界的。”他說要建設的是一座“共生城市”,這本就要改造自然,甚至是再造自然。
那種改天換地的氣魄,一點也不像外表看起來謹小慎微的日本人,倒讓我想起了新中國前30年的景象。在鄭州的西部,就有一座“文革”期間開挖的人工湖,名為西流湖,取“引黃河水西入鄭州”之意,曾經給這個一馬平川、缺少山水景觀的平原城市帶來過不小的興奮。但是,當我記事起,這個西流湖便已經逐漸干枯萎縮,成了鄭州最著名的垃圾池。
不過,人們改造自然的沖動不會消失,尤其是當他們認為掌握了更加強大的工程技術后。黑川紀童的方案贏得了很多鄭州市民的認可。最近一次回去鄭州,又去了一趟東部新區,如今改名為鄭州新區,那兩個人工湖也已經挖好了,周圍高樓林立,與五六年前相比,恍若跨越了一個世紀,這已經大大超出了已經去世了的黑川紀章的預想。記得當年他跟我說,最擔心的就是政府沒有錢,執行不了他的規劃,從而鬧得個半途而廢。但如今他們又有了更大的造城夢想。
就鄭州而言,不僅僅是東部新區,南部城市邊緣,宏闊的南水北調大運河也即將通水了,北部的黃河灘區則在動工建設一個上千畝的黃河濕地公園,就連西部那個早就干枯了的西流湖也在被重新開掘。一個建筑在平坦耕地上的北方干旱城市,短短幾十年間居然也恍惚有了一派四水環繞的水鄉景象。這樣的變遷讓人不得不感慨,掌握了現代工程技術和經濟發展帶來的財富和政治威權改造世界、重塑文明的能量。
曾幾何時,拆遷是東部城市的專有名詞,但現在,正在向中西部的大小城市蔓延,鄭州也不例外,要拆除的不僅有城中村,為了將那些通往郊區的公路拓展、綠化,政府搞了一個綠色廊道建設計劃,公路兩側30米的綠化帶吞噬了連片的習慣于傍路而居的村莊,那些失去住所的農民也統統被規劃進了城區。
這種現代化的進程在學者和輿論的敘述中是殘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在現實的行進中,也會有極端的案例,但更多時候是以一種更庸常的方式在展開。我的父輩們,他們只會去精打細算賠償的數額,最近的兩年,不斷有兒時的伙伴、親戚會打電話過來或者咨詢或者求助,大多數時候都是跟拆遷有關。于是,我也漸漸了解了許多這個城市關于拆遷的種種標準,在這樣一個經濟體量和社會發展程度的省會城市,600塊錢一平米的拆遷補償標準,在我看來實在有些荒謬,而且這樣的標準,也完全是政府單方面制訂的。很多時候,我會鼓勵他們堅決捍衛財產權,只要你不同意,政府部門就不能強拆。但我那些書生意氣式的建議,在他們看來是萬萬不可取的,他們更想托我找找認識的官府里的人,看能不能多要點補償,真的找不到,也就作罷了,真正起來為自己的利益抗爭的總是少之又少。
最深沉的底色
我18歲以后,求學、工作走過了中國大部分的省區,我發現,對于人情關系的看重、對于官員的崇拜和敬畏,程度上少有能與我的故鄉河南人相比的。
最近一次回鄭州,我找一位多年前就相識的老前輩敘舊。那是一個典型的書生官員,對鄭州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愛,如今,他已經在這座城市身居要職。我的幾位親朋知道后,不厭其煩地向我表達跟他拉拉關系,謀點利益的想法。我自然做不到。但我知道,我曾經的那些同學、親朋,其間發跡者多半是藉此類門路。幾乎每次回老家,我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成了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另類,關系也便疏遠起來。
敬官畏官、順從懦弱,這恐怕是農耕文明中最深沉的底色,而只有快速的城市化和現代化才能將其慢慢消解,又或者這種底色會將現代化弄成另外一副面貌?誰知道呢!
大多數時候,百姓總是最容易妥協的那一方,只要給他哪怕一丁點利益或者說希望,他都會選擇順從,歷史滾滾向前的車輪總是能輕易地碾過他們的身軀,在我的故鄉河南,尤其如此。
在鄭州的北郊,有一個叫作花園口的小鎮,當年抗日戰爭,當日本人逼近中原時,那些掌握著國家武力和權力的精英權貴們帶著槍炮、細軟一潰千里,南逃而去,蔣介石想到的阻敵進軍的方式居然是掘開黃河大堤,用千里黃泛區來抗日。
掘堤處就在鄭州市區的頭頂,泛濫的黃河沒有能阻擋住日本軍隊的南進,卻淹死了89萬中原普通百姓,而當年他們甚至還去掘堤現場幫工。
抗戰結束后,沒有人去追問決策的合理性,人們只是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故鄉,在那一片黃泛區之上重新開墾,房屋、村莊、農田、城市很快就又頑強地從這片土地上生發出來,直至今天的高樓林立、欣欣向榮,那些累累白骨已被深埋以至于再也無從尋覓。
用更長程的歷史視野來觀照這片土地,中原大地厚重的黃土之下,深埋著的還有無數的文明與殺戮。即使是在鄭州這座一直被外界視為新城的城市,也挖掘出了3600年前的商代早期城市遺址,從而被國家確認為中國八大古都,其后劉邦項羽在“楚河漢界”兩側的攻防殺戮、三國時的殘酷的官渡之戰等等,都在是鄭州展開,在漫長的歷史上,輝煌的文明創設與兵禍連結后,留下的白骨填滿了這座城市的地下時空。
但今天,這一切仿佛都煙消云散了,現代化的進程恍若在一張白紙上重新書寫。
多年以后,當我站在新區那個高樓環繞的湖泊邊上,卻又由衷地尊敬起那個年邁的日本設計師了,他費了巨大心血給鄭州留下的這座新城,確如他當年所說,要盡力用現代建筑構造的視覺形象承載著中原文明的厚重。那棟中原福塔、大劇院、湖泊還有與周圍建筑的巧妙布局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實現著他的承諾。夕陽西下時,它們帶給我的視覺感受與北京、上海、廣州等摩天大樓城市有著本質的差異。在遙遠的未來,這或許會成為鄭州一筆難能可貴的財富,因為在這個想象力匱乏的時代,他多少還是能夠讓你隱約感受到那種叫作文明的東西。
至于歷史、文化,還有故鄉,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無處可尋也就不尋了吧。或者說人們終會找到新的故鄉,開啟一段新的歷史。在不遠的將來,黃河之濱或許會崛起一座千萬級人口的現代都市,那里或許不再是我的故鄉,但肯定會成為更多人的故鄉,肯定會讓更多熱切期盼著城市文明的人們所熱愛。
現在,我開始和父親一樣,熱切期盼著那條縱貫中國南北的京廣高速鐵路的通車,這樣從北京回家便只要兩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