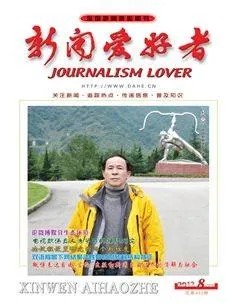明清之際傳教士在華傳教策略探析
【摘要】明清之際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是西方文明第一次與中華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本文力圖通過對此時傳教士在華傳教策略的梳理和分析,探析其傳教策略的形式和種類,以及采用這些傳教策略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動因,并對當時傳教士傳教活動的影響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關鍵詞】基督教;儒學傳統;適應策略;沖撞政策
在西方傳入中國的文明中,基督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基督教流播中國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東西方相當一個時期的主流文化在中國這樣一塊特定的土壤上交會、碰撞,又衍生出了各形各色饒有意味的歷史情狀。西方基督教來到中國,地域各異,文化傳統有別,既有異體間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融合交會、互為補充的一面,又有互相排斥、離異沖突、互為抵牾的另一面。畢竟,中國長期以來是有著悠久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所以,融會與碰撞便成了基督教來到中國的雙重變奏。
明清之際傳教士在華傳教的社會背景
自明開朝至16世紀,中國原有的封建政治統治方式、思想文化觀念和經濟活動模式都成為禁錮社會經濟和人們思想發展的阻礙,中國逐漸進入社會轉型期,首先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商業與工業的萌芽開始出現,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反思。由于商業的繁榮,商人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一舉打破了“士農工商”的等級結構,商人的后代越來越多地通過科舉取士成為“士”,商人與“士”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社會結構發生重大的變化,處于上層的士大夫逐步與大官僚、儒士與大商人融為一體,這成為明末清初社會結構的重要特點。與此同時,理學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理學家進行了更為深刻的反思。特別是新一代的李之藻、徐光啟等大力提倡“西學補益王化”,成為該時重要的論斷。
明清之際傳教士在華的傳教策略
第一,注意適應中國的文化背景,并在其基督教教理允許的范圍內盡量彌合中西兩大不同文化的抵牾與沖突。
明清之際的傳教士企圖歸化中國人不是以西化中國人為前提,而基本上是以他們自身的“中國化”改造與自我適應為出發點。
當傳教士抵達中國的時候,他們遇到了一個與其他傳教區完全不同的民族:這個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古老的文明以及燦爛的科技成果。此外,在政治上,當時的中國是統一、強大與獨立的國家,所以他們進行自我方面的“中國化”改造,注意適應中國的文化背景,并在其基督教教理允許的范圍內盡量彌合中西兩大不同文化的抵牾與沖突。
外貌的中國化。明清時期到過中國的西方人(不論傳教士還是商人)大都抱怨過“中國人以世界上最文明最有禮貌的民族自居”的態度[1]。面對這種狀況,法國傳教士感到他們必須在外貌上——穿戴與言行舉止上進行一定程度的“中國化”改造,以便不被當地居民視為“蠻子”。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法國傳教士極力模仿中國人。首先是取漢名。除了極個別的例外,絕大部分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都有漢名,同時還有表字,一如當時的中國人,如J.Bouvet漢名“白晉”,字“明遠”。在中國,傳教士取漢名不僅是為了便于中國人稱呼,而且還有更深的含義,即盡力獲得一個外表“中國化”的象征或“符號”,以便拉近中西方人士在文化上的差異。其次是著華服。在其他傳教區的傳教士身著黑色的宗教服裝,他們被當地人稱為“黑袍”。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則身穿世俗的中國服裝。當1685年傳道團行至暹羅時,傳教士即已從暹羅國王那里獲得中國服裝,做好了“華化”的準備[2]。因此,當1687年他們在寧波登陸時,他們完全以一種清代中國人的模樣出現在港口上:他們不僅身穿地道的中國衣服,而且還像當時中國人一樣剪剃了頭發[3]。再次是講漢語。幾乎所有進入中國內地的法國耶穌會士都投身于漢語學習之中。在其他方面,傳教士也盡力模仿中國人,如像中國人那樣剪剃頭發、行叩頭跪拜禮[4]、乘轎子[5]等。此外,有的傳教士還爭取在個人趣味方面中國化(如王致誠)[6]。
調和中西文化的抵牾。明清之際的傳教士清楚地意識到要想在中國這樣一個文明悠久、傳統深厚的古老國家里立穩腳跟,就必須將西方的文化價值體系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通融,尤其將其基督教教理與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說相協調。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明清之際傳教士進行了一系列努力,在其教理允許的范圍內盡力彌合中西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抵牾。他們的這一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調和中西紀年的矛盾。根據《圣經》的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人類是亞當與夏娃,他們由上帝所創造。由于他們違背上帝的禁令,偷吃禁果,于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園。若干年后,亞當與夏娃的子孫散布于世界各地,但由于這些人類忘記了上帝,終日沉迷于種種罪惡之中,于是上帝降洪水予以懲罰。在這場大洪水中除了諾亞一家獨蒙圣恩而獲救外,整個人類被毀滅,因而諾亞被稱為人類的新始祖[7]。有關這場大洪水暴發的時間,拉丁文本的《圣經》將之定為公元前2300年。但中國歷史不僅悠久,而且綿延不斷,這使得傳教士十分頭痛。于是一些傳教士如巴多明、宋君榮、馮秉正等采取改用希臘文《圣經》七十人譯本、往上拉長《圣經》紀年的辦法使之與古老的中國歷史相吻合[8]。其次為傳教士調和中西信仰抵牾的活動。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二者在宇宙觀、世界觀、歷史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看法。當這兩種理論相遇時,二者的矛盾與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比較明智而現實的辦法是盡可能溝通二者之間的聯系,并利用甚至“制造”二者之間的種種相似之處,把基督教打扮成一種與儒家學說不相沖突的“異道同歸”的理論。此即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劉應(Mgr 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與皇太子的對答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皇太子問他基督教教理與儒家理論的關系時,他答道:“孔子及中國古圣賢的學說和天主教不僅不相違背,而且還相當類似。”[2]形象派在這方面的活動尤其引人注目。形象派由白晉所創,目的在于從中國古書中尋找所謂的“原始宗教”的痕跡來調和中西信仰的沖突。其成員有馬若瑟、傅圣澤(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和郭中傳(Jean-Alexis de Gollet,1664-1741)。白晉的話明確地表明了該派的行動方針:“世界上最容易促進中國人思想和心靈皈依我們圣教的辦法是向他們指出圣教與他們那些古老原則及合理的哲學相吻合。”[9]該派傳教士沉迷于中國古籍的梳理之中,力圖找到符合他們教理的只言片語。如白晉的《古今敬天鑒》即“上卷以中國經書所載之言,以證符合于天主教之道理,其宗旨在復明上古敬天之原意”,“下卷乃以經文、士俗、民俗印符相對者,以證與天主教之道理相合”[10]。
傳教士上述調和中西信仰的努力的確使一些中國信徒產生了中西信仰的“相似感”,也許正是由于這種“相似感”吸引他們投入了傳教士的懷抱。基督教“教人忠于國王,服從父母,熱愛他人”,“(上帝的)第四戒律要求人們尊重國王、父母、先祖、大人以及一切有權支配我們的人”[10]。
最后是法國傳教士對中國傳統禮儀的態度。祭祖與敬孔是中國的兩大傳統禮儀,二者不僅由來已久,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兩個重要內容,而且還體現了儒家的倫理道德與思想。
當1693年外方傳教會在福建的顏珰主教發布有關中國禮儀的禁令時,在歐洲的李明隨后于1696年出版了其著名的《中國現狀新志》,對中國民族大加贊揚[11]。
第二,融會儒學,借儒學巧妙地傳布基督教,并有力打擊佛教等宗教:驅佛補儒及合儒、附儒、超儒政策。
1584年,利瑪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天主實錄》,這是一本教義問答性質的書,但絕少被中國的士大夫們接受,后利瑪竇就將其改寫為《天主實義》,改寫后的該書大量引用四書五經,直接談基督教的內容很少,通篇只有一處提到耶穌,書的矛頭直指佛教。對利瑪竇有意識地借融會儒學來巧妙地傳布基督教的手段,當時的人們就有體認,徐光啟把利瑪竇傳教法的核心精髓概括為四個字:“驅佛補儒”。很顯然,這種傳教策略,比之調和中西文化抵牾的策略無疑是更進一步;對于儒學,利瑪竇等采取合作政策,對佛教卻不遺余力地攻擊。對此,近代學者侯外廬先生也有總結,他稱利瑪竇的傳教策略為:合儒政策,就是聯合儒家反對佛、道兩家;附儒政策,就是為附和儒學,對天主教義進行某些枝節性修改,比如將天主教義修改為承認中國人的偶像崇拜、祭祖習俗、祖先祭祀等,將“天主”的稱謂多改為中國典籍中的上帝,對基督教的“原罪說”進行某些修改,以接近儒學傳統的“性善說”,從而導出人生具有“人性良能”,但只有信奉上帝才能顯現發掘,終極還是歸于基督教一途;超儒政策,就是以天主教義來修改和超越儒學,這是利瑪竇基督教義儒學化的歸結點。但是由于基督教和儒學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雖然利瑪竇等努力調和,但是該策略還是有一些不可克服的矛盾,以至于最后利瑪竇自己也難以自圓其說。
第三,“科學傳教”,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吸引力進行傳教活動。
這是明清之際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策略的又一特色。由于中國傳統科學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加上當時中國的科技界對東來的西方新知識表現出很大的熱情,比如徐光啟對西方的科學知識就有濃厚的興趣,利瑪竇博學多才,兼通天文、地理、語言、數學等學科,盡量不以西洋教士的面目出現,而是以學者的身份來潛移默化地暗傳福音,是利瑪竇的又一布道方法。借用學術的目的是為了傳教,科學技藝在利瑪竇那里只是一個工具和手段,但對中國人來說,這一工具和手段比之目的才是更有意義的。
利瑪竇利用學術傳教取得成功之后,西方科技知識就成為明清傳教士的一個重要傳教手段。當時耶穌會十分重視派往中國的耶穌會士的人選,注意挑選那些學者型的傳教士。1685年傳道團即是一個典型例子,它由6名法國皇家科學院成員組成,號稱路易十四的“皇家數學家”[12](其中5人到華)。所有這些陸續而來的法國耶穌會士精通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多門學科,他們有的充當皇帝的御前侍講,向康熙講授多種科學知識;有的參加清政府主持的規模空前的《皇輿全圖》的測繪活動(康熙年間大約共有10名傳教士參加,其中法國耶穌會士占了7名,是參加此活動的傳教士隊伍中的主力軍);有的還參加圓明園西洋樓的建造[13]。廣博的科技知識使傳教士很快贏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這也就是為什么這些傳教士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走上層路線,結交士大夫,討好統治者。
“走上層路線”這種傳教策略,在羅明堅在華傳教時期就已備受推崇,在利瑪竇時期更是得以重用,在利瑪竇1609年的最后書簡中,有句話很能說明他走上層路線的傳教思想——“寧缺毋濫”,利氏認為寧可少要一些好的基督教徒,也不要一大批濫竽充數者[14]。他認為上層的紳士們的表率行為具有影響社會和其余人的作用,因此,他大量結交上層士大夫,為了討好他們,他就去主動適應這些文士和統治階層、他們的習慣及學術傳統,以至于使他的全部中文著作都帶有這種適應中國社會的特征。
第五,借醫傳教。
外國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后就開始醫藥活動。利瑪竇開創了傳教與醫療并重的傳教路線,法國傳教士張誠曾用金雞納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馬禮遜也曾在澳門開辦西醫診所,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在華建立了第一所新式教會醫院——“廣州眼科醫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西醫自此正式傳入中國。1837年,伯駕在醫局內向關韜等3名中國人傳授西醫知識,使關韜成為中國第一個“西醫學醫”。從這個意義上講,伯駕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人傳授現代醫學的外國醫生。后來的一些傳教士陸續建立了一些教會醫院,教會醫院在中國非常有名氣,湘雅醫院、齊魯醫院、協和醫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雖然它們的名稱可能已經改了。
第六,以“禮儀之爭”為代表的“沖撞”策略。
1700年,耶穌會士張誠等人就中國祀孔祭祖是否帶有宗教性質這一問題詢問康熙皇帝。康熙答復他們這不過是一種表示崇敬的禮節,并不帶有宗教性質。耶穌會士的反對派諸如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等,便以此為借口攻擊耶穌會,說對于教務問題不請示教皇而訴諸一個教外的異國皇帝,這是不可容忍的嚴重錯誤。1705年,教廷使者多羅攜帶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關于禁止教徒祀孔祭祖等內容的公文來華,康熙拒絕接受。第二年,驅逐多羅出京,拘于澳門(多羅最后死在獄中)。康熙下令,愿意遵守中國政府規定傳教的傳教士登記領取證件,不從者一律遣返回國。后來,又有傳教士介入皇位繼承權的宮廷斗爭中。所以雍正繼位后,禁教更嚴,凡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一律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各國傳教士限半年內離境前往澳門,這道圣旨無異于判處了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死刑。從這以后,清政府奉行了長達百年的閉關鎖國政策,基督教在中國失去了合法公開傳播的身份。
明清之際傳教士傳教策略的分析及其傳教活動的影響
第一,明清之際傳教士傳教策略的分析。
綜上所述,明清之際傳教士的傳教策略可以說非常多元,幾乎用盡其所能。若認真分析,我們會發現,明清之際傳教士傳教的策略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適應”政策,就是傳教士為了適應在中國這個具有獨特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進行傳教,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適應中國現實情況的措施。在這一方面,從羅明堅開始,就已經開始實施,羅明堅非常注重與明朝達官貴人的交往,因為他深知在中國只有結交上層人物才能得到官方認可。在羅明堅逝世后,其助手利瑪竇以及之后的傳教士將此策略推向另一個新的高潮,比如利瑪竇走上層路線,結交徐光啟、李之藻,消弭對抗,湯若望利用學術傳教,以儒學作為盟友,利用西方先進科技吸引上層士大夫、借醫傳教等措施,都是為了更好地適應中國的現實情況,從而使中國人對基督教產生好的印象,更加有利于傳教。這些傳教士早期使用“適應”政策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也就是明王朝,此時國力強盛,科技相對比較發達,再加上統治者高高在上的統治觀念作祟,在伴隨著幾次入侵中國的企圖失敗后,傳教士意識到了中國的強大,不得不使用“適應”政策來向中國妥協,為了傳教就不得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使用盡量適應中國現實情況的政策。
這一階段,這些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行為完全受中國政府控制,他們于傳教方面是失敗的,但在文化傳播方面卻是非常成功的,不僅推動了“西學東漸”,使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中國得以傳播,而且在“東學西漸”方面更是成績斐然,將中國大量的優秀文化傳播到西方,使萊布尼茨等著名的西方學者深受影響,可以說這一時期西方傳教士向中國傳播文化方面,遠不及他們在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方面的成績顯赫,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的國力和文化處于相對強勢的階段。而后1840年的清政府在國力上和科技上完全處于弱勢地位,就徹底無法抵御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了。
第二類可以說是“沖撞”政策,表現最為突出的是“禮儀之爭”。禮儀之爭是中西兩種文化碰撞的結果,廣義的禮儀之爭從基督教傳入中國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開始了。我們所說的禮儀之爭通常是指狹義上的禮儀之爭,主要是指明清之際羅馬教廷和中國朝廷之間圍繞基督徒能否參加祀孔祭祖活動而展開的一系列爭論。爭論的焦點看似僅僅局限在宗教和文化領域,實際上,隱藏在其背后的卻是政權和教權、政權和政權之爭,是國家主權之爭。
第二,明清之際傳教士傳教活動的影響。
明清之際,我國和歐洲的文化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這次交流中,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充當了橋梁和紐帶。一方面,為了傳教的需要,他們將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傳入中國,使中國知識界對“西學”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傳遞書信和翻譯中國典籍等方式,把中國悠久燦爛的文化介紹給歐洲,使歐洲出現了“中國熱”。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對于各自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起著不小的作用。
明清之際的來華傳教士傳播的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也附帶傳播了一些西方近代或準近代的科學技術知識,而后一種文化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參考文獻:
[1]Relations des Jésuites,contenant ce qui s’ est passé de plus remarquable dans les missions d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dans la Nouvelle-France,tome 2,1637,Montrèal,ditions du Jour,1972,p.41.
[2]白晉.康熙皇帝[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3]張誠寫于1686年6月18日和7月1日的信,見Henri Bernard,“Le Voy-age du père de Fontany au Siam et à la Chine(1685-1687)d‘après des let-ters inédites”,Bulletin del‘Universitél‘Aurore,tome3-2,p.258、260,1924.
[4]洪若翰寫于1687年8月12日的信,見上引Henri Bernard,278.
[5]洪若翰寫于1703年2月15日的信,見前Wl65CVNK0jH+gLMu9PdVDQ==引朱書,35-36.
[6]Louis Lecomte,Un jésuite à Pékin:Nouveaux mémor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1687-1692,p.432,Paris,Phébus,1990.
[7]湯尚賢及沙守信分別寫于1701年12月17日與1701年12月30日的信,見朱書,11,12,32.
[8]《圣經》(中國基督教協會,2004年),“創世紀”的有關記載,2-49.
[9]白晉.中國人的智慧與基督徒的哲學,天津出版社,1935:145.
[10]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tome 17,Paris,1717-1774,p15.
[11]Le Comte,Nouveaux mémoires sur l ‘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tome 2,Paris,Anisson,1696,p141。
[12]Camille de Rochemonteix,Joseph Amiotet les derniers sur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caise à Pékin(1750-1795),Paris,A.Picard,1915.p51。
[13]Cl.Madrolle,Les premiers voyages francais à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1698-1719,Paris,Augustin Challamel,1901.p97,p101.
[14]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首次撞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60.
(皇甫曉濤為上海大學影視學院2009級傳播學博士生;廖媌婧為上海戲劇學院講師,上海大學影視學院2009級傳播學博士生)
編校: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