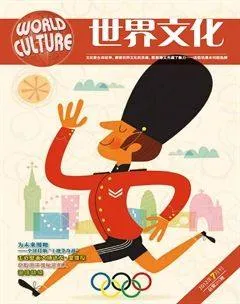死亡:對庸常生活的反抗
2012-12-29 00:00:00李朝君
世界文化 2012年7期

摯愛的倫納德:你要把人生看透徹,一定要真實地面對人生,了解人生的本質。當你終于了解人生,就能真正地熱愛生命,然后才舍得放下。記住我們在一起的這些年,永遠不要遺忘,永遠記得我們的愛,永志不忘生命中的時時刻刻。
——弗吉尼亞·伍爾芙
《時時刻刻》(The Hours)是2002年奧斯卡獲獎影片,這部電影聚集了梅麗爾·斯特里普、茱莉安·摩爾和妮可·基德曼三位當今好萊塢的演技派明星。妮可·基德曼作為片中弗吉尼亞·伍爾芙的扮演者,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桂冠,而三位女演員更是在柏林電影節上一同被授予最佳女主角銀熊獎。
這是一部描寫三個不同時代的女性的電影,她們三人的生活因伍爾芙的小說《達洛維夫人》有了交點,電影集中地呈現出這三個女人平凡卻又危機四伏的一天。她們一個是患有嚴重抑郁癥的天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一個是“二戰”末期的家庭主婦——勞拉·布朗,還有一個則是生活在2001年的女編輯——克拉莉莎·沃恩。交叉進行著的敘事,并沒有擾亂故事的節奏和混淆電影的主題,而是緊緊將三人的人生擰結于一根主線之上:時間是生活的本質,而生活正用它隱形的手,在人們心靈上留下痕跡。
如果說《達洛維夫人》是三位女主人公象征意義上的交點,那么生活便是三人真實意義上的共通點;生活是由連貫的不可倒退的時間堆積而成的,因此它具有了一種不變的特質。不管生活是多么激情澎湃,它終將在周而復始地輪轉里歸于庸常,而庸常的生活是這三位女主人公的牢籠。
倫納德為了使患有抑郁癥的伍爾芙能有一個平靜安詳的生活環境,將家搬到了倫敦郊區鄉鎮——里奇蒙德。表面寧靜祥和的鄉村氛圍,無法撫平伍爾芙激蕩的內心,她因這靜如死水的生活而變得焦躁和局促不安。伍爾芙是一個渴望探知人生本質和洞穿意識潛流的作家,她需要看到世界的模樣,讓紛繁的意象走進她的內心;她需要體驗和感受嘈雜和喧囂,需要這種混亂但鮮活的生活。因為生活就像是一面鏡子,能反襯她的內心,使它豐富與飽滿;只有在這激烈的對抗里,才能讓她體味人生的本質。縱使掙扎和痛苦,縱使隨時都可能死亡,但這才是她真正需要的。在空蕩的火車站,伍爾芙說:“如果讓我在里奇蒙德和死亡之間做選擇,我選擇死亡。”是的,只有她自身能夠明白這選擇的意義所在,因為除卻生的激烈震蕩,便只有死亡能與之媲美。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不是一個選擇,因為伍爾芙已別無選擇。
同樣面臨選擇的還有勞拉。這位看上去過著幸福生活的家庭主婦有體貼的丈夫、乖巧的兒子,肚子里正孕育著家庭的第四位成員。她開始閱讀《達洛維夫人》前,一切看上去很美好和平靜——或許她曾經滿足于平常的生活,將內心的自我緊緊封閉而以慣常的姿態為人處世。然而,《達洛維夫人》恰似一根導火索,擾亂了她的思緒和情感。她在一堆瑣事中漸漸找不到真正的自我,發現在鏡中只看到時光匆匆而過,而自己的一生終將淪為時光的陪襯和犧牲品。她先是要以死亡來作抗爭,然而當死亡的幻覺猶如海水將她淹沒的時候,她驚醒了。唯有死亡才能激發人求生的本能,當死神冰冷刻骨地從你身邊經過,你才會不顧一切去抓住生之繩索。勞拉終于暗下決心,生下第二胎便遠走高飛,去追尋自己的生活。
后來,當勞拉前來參加兒子的獲獎聚會,卻得知兒子已自殺,她與電影的另一位主人公克拉莉莎有了一次交談,她說:“如果我能說后悔就好了,那樣就比較好過,但是當你別無選擇的時候,后悔又代表什么。”也許事情就是這樣,后悔是虛妄的。一旦我們做出選擇,它便不可逆轉;即使可以回到過去,它在那時那刻仍然是你的迫切需要,你能做的選擇仍然只有一種。或許我們此時回頭看,你發現確實有多種可能性存在,但是沒有人能真正站在當下把握所有可能性,我們終究只能走一條路,除此之外并無選擇。
如果說伍爾芙和勞拉是鏡子的一面的話,那么克拉莉莎則是鏡子的另一面。她沉浸在生活之中,忙于各種瑣事。與其說她沒有陷入伍爾芙和勞拉那樣的困境,還不如說作為現代女性的克拉莉莎,她適時地為自己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詩人兼作家理查德·布朗(他正是勞拉·布朗的兒子)。她需要理查德活著,因為只有他活著,她才能從這繁忙瑣碎的生活里抽身出來,因理查德而看到真實的自己。我們目光所及的理查德,已經形容枯槁,他身患艾滋病,已經瀕臨崩潰。理查德活著很痛苦,仿佛是在受刑。正如他所言,他活著只是為了讓克拉莉莎高興。在這里,克拉莉莎所扮演的角色便成為了理查德的牢籠,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無疑是在加重理查德的痛苦。終于,他告訴克拉莉莎:“達洛維夫人。你必須放我走,也放了你自己。”
理查德從高樓跳下,用自盡的方式完成了自我選擇,也給克拉莉莎再一次自我選擇的機會。他用死亡的方式告訴克拉莉莎:畢竟我們才是自己的主宰,我們不能將自己分為幾個人,讓他們貫徹我們的意志,讓他們完成我們自己的追求。我們的夢想必須自己去追求,真實的自我也必須由我們自己去發掘。
當勞拉來到克拉莉莎的家中做客,她們之間的談話讓克拉莉莎最終意識到生活是自己的,你要么選擇死亡來放棄生活(勞拉說她曾經想這么做,但是她選擇了生存),要么你就直面它而活著。這里沒有中間狀態可供選擇,你不能逃避自己的生活,縱然你能逃避一時獲得短暫的平靜,但是你卻不能得到最終的解脫。克拉莉莎終于明白:意識到擁有很多可能性并不是幸福的開始,而是你意識到擁有可能性那一刻,你便是幸福的。克拉莉莎是生活的,她將自己分離開來,靠打理理查德的生活來維持夢想,自己生活在瑣事之中。理查德的死和勞拉的話,讓她終于看清了自己的幸福所在,她的兩面終于合二為一,于是劇終時,我們看到克拉莉莎原本緊張索然的臉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電影中,伍爾芙與倫納德有這樣一段對話:
“為什么一定有人要死?”倫納德問伍爾芙 。
“為了對比,”伍爾芙說,“為了讓活著的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
“那么誰會死?”倫納德又問。
“詩人,”伍爾芙說,“那些心懷夢想的人。”
最后,伍爾芙在自己的口袋里裝滿石頭,緩緩地走向歐塞河河心,河水終于淹沒了她。無聲的死亡沒有波濤,沉靜的河流繼續流淌。自盡成為最后的權利,成為超越表象的自主選擇。是的,只有以死亡作為參照,我們才能體味生命的本質和活著的美好。同時,死亡作為終極意義的解脫,有了自足的力量,我們可能不理解,但是卻必須接受。
每一棵樹,或許它們出生的環境不同,成長中的遭遇也不一樣,然而我們透過表象,關注它的內里時,卻能看到一圈圈蕩開的年輪在訴說相同的光陰故事。我們活著便是在奔赴死亡,杜拉斯說:“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通往死亡的道路卻是筆直的。”在這一致的道路上,我們卻走出了不一樣的步伐,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這或許正是因為我們當中,有人選擇直面人生,有人選擇逃避;有人選擇遵循自己內心的真實,有人選擇茍且而活;有人了解了人生的真義,有人卻漸漸埋葬于歷史的滾滾風塵。
我們的人生不盡相同,對于他人的人生,我們不能妄加指責、評斷。但是,我們都必須面對自己的人生,直面它、了解它,即使是以死亡的方式。只有這樣,我們才有了超越表象的可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熱愛生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尋到內心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