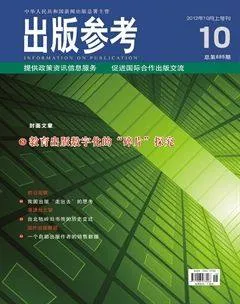在中醫未刊著作里尋找閃光的金子
由筆者策劃的叢書“近現代名中醫未刊著作精品集”(第一輯,8冊,以下簡稱“未刊集”)問世已近一載,日前陸續傳來圖書重印的好消息,這套以學術特色進軍市場的圖書能得到讀者的歡迎,是令我頗感欣慰的。
近年來,中醫類圖書中頻頻出現劉太醫、張悟本等“大師”炮制的“罌粟花”,他們著作的發行量也曾使我們這些中醫學術的守望者“自慚形穢”,我也很想把自己辛勤培育出來的未刊集稱為暢銷書,盡管這是非常勉強的事情。在當前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堅持學術和追求銷量似乎是很難同時企及的事情,在我考量的重心不自覺地偏向后者的時候,讀到了不啻為“當頭棒喝”的吳培華先生的幾句話,“一個出版社要是盡出暢銷書,那這個出版社是沒有什么文化品位的”,“真正的文化精品都不是什么暢銷書。它可能不暢銷,但它的文化價值、精神價值才是一個民族所需要的”,但在警醒的同時,仍會“幻想”著既有品位又能暢銷的好事。
雖然我很想把這篇斷想寫得長一些,以表明自己不是不學無術者,但不能總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盡管這種做法現在髦的合時。于是,便想鄭重地提示同道:中醫未刊著作里,有閃光的金子。
尋找!尋找!發現寶藏!
未刊的含義很簡單,就是沒有刊行過。在十載的編輯生涯中,我接觸過許多沉寂了數十年的原始稿件,便考慮挑選一些,以“未刊”的名義整理出版,當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名詞創造之時,卻在互聯網上發現文藝類圖書里已經有許多未刊先行者,便又覺得自己是坐井觀天的青蛙,又像偏居一隅的夜郎侯。于是,便私心自用,結合中醫書稿特點,將“未刊”圈定為“作者生前其作品未能刊行”。在中醫學發展史上,這類稿件很多,如傳世名著《本草綱目》就是在李時珍仙逝之后才得以付梓的。于此可見,部分未刊著作的學術價值不可低估。在圖書館中,清代以往的未刊著作為數不少。但如要出版,就涉及到古籍整理的問題;一說到古籍整理,我便生敬畏之心,不敢輕易為之。清代儒醫柯韻伯先生曾說:“胸中有萬卷書,筆底無半點塵者,始可著書;胸中無半點塵,目中無半點塵者,才許作古書注疏。”其境界要求,高山仰止,不才淺薄,十不能一。況且,如投身其中,興之所至,不免指手劃腳或信口雌黃。在當下古籍整理領域,急功近利者比比皆是,以致前賢著作傷痕累累,倘古籍能哭,早已“淚飛頓作傾盆雨”了,故當引以為戒。第二個原因,近現代醫家,雖斯人已歿,但余響未絕,讀者往往會因敬其人而購其書,圖書宣傳推廣還是比較容易一些。第三個原因,說起來心里就有些沉重了,那就是“搶救”。前述古籍,雖然還沒有出版,但畢竟還安安穩穩地躺在圖書館里,近現代醫家遺作的處境相較而言,就艱難得多。在我國,近現代曾經活躍過一大批學驗俱豐、在當時享有盛譽的中醫大家,他們品德高尚,醫術精湛,懷丹心以濟世,執妙方以活人,為中醫事業的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然而,他們的許多著作(如手稿等)因種種原因或塵封霉變,或玉殞香消,以致先賢在長期臨床實踐和寢饋深思中積累的寶貴學驗被湮沒、被遺忘,甚至有的已經失傳,這應視為中醫事業的重大損失。
搶救!搶救!時不我待!
在尋覓、整理未刊著作的時候,經常為作者的精神所感動,怎樣防止“感動”變為“沖動”?不妨舉一例。趙桐先生在其著作《傷寒述義》的序言與后記中講,為了寫成這本書,“右手腕貼桌處磨起高繭,無名指筆桿壓迫成了胼胝……在暑假……熱得心跳心慌……可是因為短錢,連冰棍也不知什么味道……我精神百倍,以為人世間沒比我在病中著述醫經再美、再樂、再痛快、再便宜、再高尚、再有價值了”,“嗟!一生精力埋沒在故紙堆中,半百心血收獲的只此幾頁墨痕”,這不正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說一句空”的真實體現嗎?那么對趙先生的著作的學術水平如何判定,在當前還有沒有出版價值?我為此設定了一個基本標準,即:“作品應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臨床指導價值,其學術觀點及臨證經驗等經過作者長期的臨床檢驗才得以提煉,既來源于臨床實踐,又能很好地指導臨床實踐,以目前的中醫發展水平來衡量,仍有其科學性、獨特性、實用性,對中醫工作者和學習者有重要參考意義。”為慎重起見,我還邀請了我國著名中醫學家審閱了部分稿件,在書稿學術水平得到他們認可以后,才最終確立出版書目。實踐證明,此做法是成功的。
目前,許多中醫名家的未刊作品多在其弟子、家人或友人處,另有部分保存在中醫臨床、科研機構或各地圖書館當中,尋覓未刊著作過程是艱辛的,而選擇出版又是對編輯學識的考驗。未刊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意義重大,不才匹馬單槍難有所成,期盼與有志于此者共同努力,使一批批的中醫未刊著作得以問世,使先賢英名不朽,學驗流傳,徽音累屬,慈惠無窮。
(作者單位系人民衛生出版社中醫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