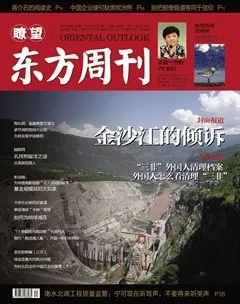緊守調(diào)控底線不動搖
一千多年以前,杜甫已經(jīng)發(fā)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質(zhì)問。
時空變換,住房問題近年來已成最大的民生問題之一,也是每年兩會關注焦點。時至今日,離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方向已有。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了兩條路:一是繼續(xù)搞好房地產(chǎn)市場調(diào)控,二是繼續(xù)搞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用市場調(diào)控限制投機需求,用安居工程提升保障房供給。一壓一提,看起來可以實現(xiàn)房屋供求的平衡,達成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房屋價格。
一些研究也證明了房地產(chǎn)降溫措施的成效,2012年第一季度北京和上海的房價較前一季度僅上漲0.3%。與上年同期相比,中國住房價格還下跌了2.2%。而就在一年前,中國房價的同比漲幅達到8%。戰(zhàn)果可以擴大嗎?或者至少,這樣的成效能夠繼續(xù)維持下去嗎?
中央多次表明厲行調(diào)控的決心,與新的世界格局之下的宏觀經(jīng)濟背景有關。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fā),讓以往新興經(jīng)濟體總是成為經(jīng)濟危機薄弱環(huán)節(jié)及策源地的局面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危機之后的雙速復蘇景觀,更讓其他處于凄風慘雨中的國家,對中國經(jīng)濟有“風景這邊獨好”之嘆。
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就,讓政府有底氣以更加決絕的意志和行動力,來優(yōu)先應對蕭墻之內(nèi)的隱患。高企的房價,及其所助長的不完全公正的再分配趨勢,已經(jīng)關涉民生之伸縮與民心之聚散,是中央政府不得不考慮的頭等大事。關于調(diào)控的密集表態(tài)與行動于是出臺。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fā)展到今天,已經(jīng)超出大多數(shù)人的意料。一年之前,成員國的退出和歐元區(qū)的解體只被認為是概率低于10%的小概率事件,一年之后,媒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歐洲委員會的官員都在提出希臘退出歐元區(qū)的想法。“歐元區(qū)將在混亂中解體”的說法也不脛而走。
面對這樣一種可能波及全球的系統(tǒng)性風險,中國顯然難以自外其事、獨善其身。4月份貿(mào)易數(shù)據(jù)的意外惡化,加劇了各方的擔憂。近日央行突然降息,也被視為對未來外部需求驟降帶來經(jīng)濟下行的提前加油。畢竟中國社會分配失衡的陣痛還需要較為強勁的增長來緩釋。
地方政府已經(jīng)敏銳地感受到了增長放緩的壓力,各地屢屢出臺不同版本的“樓市新政”。統(tǒng)計表明,從2011年8月至2012年5月10日,全國共有33個城市出臺樓市新政。最新的一宗例子是近日石家莊推出的樓市新政。五條措施,其中有一條“人均住房面積低于全省人均住房面積的市民將允許購買第三套住房”,可以說直接挑戰(zhàn)中央的限購限貸調(diào)控措施。
面對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以及地方利益的蠢動,中央還應該或者能夠繼續(xù)維持對房地產(chǎn)市場的調(diào)控姿態(tài)嗎?對此,我們的看法是:緊守調(diào)控這條底線,不動搖。對住房空置率的一些零星的調(diào)查,反映出“我們已經(jīng)擁有了為數(shù)不少的民眾住不起的房子”的事實。
再不堵住投機風潮,社會資源就會愈加涌向非生產(chǎn)性的用途,造成每年GDP不斷增加,但作為存量的社會財富卻不斷減少的吊詭世界。一些建筑年份不到十年的房屋樓堂館所被不斷推倒重來,正折射著“流量突飛猛進、存量不斷流失”的荒誕事實。
從大禹時代起,我們就領會“堵不如疏”的行政經(jīng)驗,知曉只堵不疏的可怕后果。因此,在房市調(diào)控背后,更艱巨且需要更大意志力去踐行的,是調(diào)控市場管制。
投資總是期待回報,資本總要尋求利潤,不讓它在生產(chǎn)性用途上獲利,它就會去非生產(chǎn)性用途上投機。只要在那些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通訊、教育、金融、醫(yī)療、居住、水、電、氣等日常微觀領域,多一些競爭空間,社會資本就會煥發(fā)出更大的創(chuàng)造力來滿足人民,創(chuàng)造財富、技術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