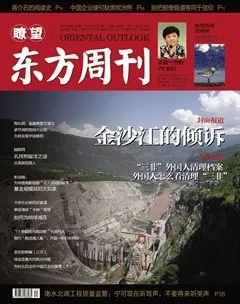“三非”外國人清理檔案
今年5月15日至8月底,北京市公安局集中開展清理“三非”外國人百日專項整治行動。其間,市民可舉報在京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外國人,構成犯罪的外國人將被追究刑責。
“這是一項嚴厲的執法行動,意味著北京的‘三非’外國人問題日益嚴重,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北京理工大學移民法學者劉國福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三非”問題在中國凸顯,客觀上說明了中國國力的上升,同時也要求政府處置能力加強。而“三非”問題不可能完全解決,“這在全球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它是全球發展不平衡的必然結果。”
“三非”已是全國性問題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進入中國的外國人急劇增加。以北京市為例,據《人民日報》5月15日報道,北京市每日實有外國人近20萬,居住地遍布所有行政區縣。
另據2011年公布的相關數據,北京望京小區常駐韓僑約3萬人,占該小區總人口五分之一。韓國人在望京地區經營的餐廳、超市、茶館、美容院等超過500家,望京也因此有“韓國城”之稱。

類似北京韓國城的跨國移民聚集,在中國其他城市也存在著,如上海的日本人聚居區、義烏的中東人一條街、廣州的非洲人聚居區等。
2012年4月25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上,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了外國人入出境及居留、就業管理工作情況。
楊煥寧在報告中說,從入出境情況看,2011年外國人入出境5412萬人次,其中入境2711萬人次。2000年以來,外國人入境人數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遞增。
從居留情況看,2011年近60萬人,主要為三資企業工作人員、留學生、教師、外企駐華機構代表及家屬,親屬團聚人員。截至2011年底,持有《外國人永久居留證》的外國人4752人,其中外籍高層次人才及家屬1735人、親屬團聚人員3017人。
從就業情況看,截至2011年底,在華就業外國人約22萬人,約占在華常住外國人總數的37%,主要為三資企業工作人員、教師、外企駐華機構代表。
外國人違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規的行為主要表現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業(簡稱“三非”)。2011年,全國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查處“三非”外國人2萬余人次。
2011年,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總隊查出的外國人“三非”案件中,違法主體包括臨時來華人員、三資企業人員、留學生等,涉及100多個國家,排名前五的分別是韓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和日本。
非法入境者一般采取偷渡或辦理假證件等各種方式進入中國,大多數會被及時截獲。2012年2月13日凌晨,33名欲取道廣西防城港東興市前往廣東等地務工的非法入境外國居民被截獲。據東興警方披露,當天,東興市公安局城區警務綜合大隊、出入境管理大隊、治安聯防大隊等多警種協作,在東興城區東中碼頭、老樹咖啡店后巷等多處截獲上述33名非法入境者,33名非法入境外國人員均從中越界河北侖河沿岸便道入境,被截獲時身上均未攜帶任何合法證件。
而在北京中心城區,“三非”現象中最多的是非法居留。據公安部統計,“三非”案例中,非法居留的占到80%。其中絕大多數是因不了解中國法律規定而短期逾期滯留等情節輕微者,惡意非法居留占5%左右。長期非法居留者以非洲國家為主,如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和喀麥隆。蒙古國人在京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較為突出。2008年以來,共拘留審查非法居留的蒙古國人98人。
2012年4月9日,一名非法居留長達564天的外國人士艾利遜(譯名)從廣州白云機場被遣送出境。這是佛山三水公安分局首次對“非法居留”的外國人執行行政拘留并遣送出境的處罰。據三水警方公布,該男子通過境外代理機構申請J- 2短期入境簽證,于2010年8月24日從白云機場入境,入境后只允許停留20天,卻一直在廣州廣源路附近非法居留。
在非法居留中,菲傭問題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2012年4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召開了“外國人管理新聞發布會”,當地警方稱“在深圳工作的菲傭全部為非法居留、非法就業”,原因在于目前我國限制菲傭入境服務,在深圳的菲傭使用的均是旅游商務簽證,不能在我國境內長期居留。
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有明確界定不同,非法就業在我國并沒有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其實施細則僅是規定“對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或者其授權的部門批準私自謀職的外國人”,在終止其任職或者就業的同時,可以處1000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并處限期出境。而沒有單獨條款對“非法就業”做出明確的概念界定。
目前在華外國人非法就業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外語教育、涉外演出、涉外家政、勞動密集型產業等方面,多以留學、訪問為由入境后非法就業。
2011年6月,重慶集中開展“三非”外國人的清理整治行動,15名外國人因非法就業被查,涉及美國、德國、印度等8個國家。這些非法就業的外國人主要集中在外語培訓和餐飲業,大部分是因為不了解中國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沒有取得由出入境管理局簽發的外國人居留許可。

廣東從查“三非”轉向為外國人提供服務
在廣東,針對“三非”外國人的清理、管理工作已經常態化。
從1996年起,到廣州打工的外國人數量逐年明顯遞增,到2006年時大量外國人已在地理上集結為各個聚居區,外界熟知的廣州“黑人區”即是典型例子。據中山大學副教授李志剛等于2008年成稿的論文估計,廣州的黑人總量大約為15000~20000人,構成多元,操法語、英語、阿拉伯語和葡萄牙語等不同語言,其中大部分來自西非,另有相當數量來自中非和東非。
2006年底,廣州市公安部門組建查處“三非”外國人機動隊和專業隊。從2007年起,每兩個月在涉外重點區域組織開展一次專項清查行動。2011年3月,廣東省政府頒布《廣東省關于加強外國人管理服務的暫行規定》,此舉被認為開創了地方政府對涉外事務立法的先河。
“剛開始以開展專項行動為主,近年來我們更多是為外國人提供服務。”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申勇強日前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說,目前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十個城市建有106個外國人管理服務站,36個外國人融入社區的示范點。
2008年1月15日,廣州市第一家正式掛牌運作的外國人管理服務站在廣州番禺區洛浦街麗江花園住宅小區成立,其職責包括:對轄區內外國人居住情況和涉外機構進行摸查,提醒外國人到期辦理臨時住宿登記,發現過期未辦理簽證或屬于“三非”的外國人及其他可疑人員時立刻通知當地派出所。服務站還會將所有涉外人員的基礎數據錄入電腦,實施對外國人的信息化管理。
按照申勇強的說法,對于“三非”外國人,廣東省目前已經形成了常態化治理,“我們已經將清理‘三非’外國人納入了全警種的一項工作,要求培訓各基層的公安機關派出所,建立出入境牽頭各警種參加區域行動、周邊聯動的常態清查‘三非’外國人工作機制。”
北京市清理“三非”的做法與此大致相同。北京市公安局透露,接下來的三個多月,將多警種聯動,對外籍人士多的重點社區,如三里屯、五道口和望京等地區進行清查,對重點部位進行定期整治。同時,嚴格審查簽證申請,并以在大街上隨機例行檢查以及入戶檢查等方式展開清查整治行動。

觀念不能停留在“外國人來得越多越好”的時代
2012年5月15日《環球時報》發表文章,呼吁對“三非”外國人要“硬氣起來”,以免問題越拖越深,但同時“要抱平常心,絕不可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動輒冒出排外主義,也應盡可能不引起外界對中國從此會冷冰冰對待外國人的誤讀”。
從政府到社會,怎樣對外國人抱以“平常心”,在實際操作中絕非易事。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此前政策上對于外國人來華一直以“嚴”、“緊”為特點,面對開放的新形勢,各地公安機關對外國人的管理究竟如何開放、怎樣進行改革感到“放不開,拿不準”。
宋廣益1955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任副科長,1981年調入公安部工作,任出入境管理局處長、副局級調研員。1979年公安部組織數名重點地區從事外國人管理工作人員研究起草對外國人管理的辦法,她是參加者之一。
根據宋廣益的回憶文章,“當時搜集了美、英、日、羅、加等20多個國家的法律文本,并摘要成冊,1981年‘外國人管理法’的初稿草就,領導讓我們帶著稿子到沿海開放勢頭強勁的廣東、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
雖然上層已開始研究對外國人的管理對策,但因尚未有明確規定出臺,基層公安機關仍采用老辦法。宋廣益記得1982年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召開會議時,“會議中間,我被各地外辦的同志‘圍攻’,他們紛紛反映,地方公安機關對外國人卡得太死。”
被“圍攻”后,宋廣益決定到幾個重點省、區調查,“我和省廳的同志一路進行‘改革開放’的宣傳。”“公安機關一定要認真執行開放政策,決不當‘絆腳石’。”
1985年全國開放市縣增至107個,至1998年底全國開放市縣已達1392個,來華外國人數與日俱增。1982年來華外國人數為76萬人,1998年達到710萬人,增加約十倍。
政策從嚴緊到開放,對外國人來華的觀念亦從“不希望來得多”到“來得越多越好”,而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2008年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副處長高華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有些部門的觀念仍停留在“外國人來得越多越好”的時代,這給國內的外國人管理工作造成了混亂。
“我國個別駐外使(領)館簽證工作有時把關不嚴,僅審查申請材料,沒有實際調研和人身比對,甚至把原始材料交由國外旅行社代管,簽證核發了多少份、簽發給什么人都不太清楚。”高華達說,國內警方曾多次查處一人持有2份有效簽證的案例。這也導致一些持短期簽證者入境之后,一旦丟失或故意損毀簽證而長期居留,警方在清理時無從掌握其國籍信息,無法快速遣返。
設立“移民局”還不成熟
近年來,在來華外國人劇增的同時,管理外國人的機制并沒有相應夯實。其中尤受關注的問題是,目前我國沒有專門部門管理外國人居留。
2009年北京市政府外事辦涉外處處長高志勇對媒體說,目前對外國人申請在中國居留的問題,決策、發證和查證的職責分屬三個不同職權部門,呈現多頭管理局面。
涉及外國人在華的日常管理部門分散,且部門之間溝通協調機制不完善,信息無法充分共享。如民政部管涉外婚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外國人在華就業,派出所管外國人住宿登記,出入境管理局負責外國人簽證簽發與逾期非法居留的處罰。
而在勞動、稅務、工商、教育等部門對外國人的管理中亦存在真空。以工商系統為例,據2008年3月《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工商局負責外國企業駐京機構的資質審批,但一般情況下只看書面材料,不實地核查,工商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有30%~40%的信息不實,甚至根本找不到相關企業。當時的數據是在京外資企業到工商局登記注冊的有3萬多家,而到公安部門備案的僅12000多家,此外虛假投資、異地辦公、虛假注冊、該注銷的不注銷等現象也較多存在。
為此,2009和2010年,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曾連續提出關于成立國家移民局的建議。
對于建議的結果,葉青對媒體透露:“目前得到人大的反饋是:討論有意義,但目前尚未成熟,還待可行性研究。”
不過在信息共享方面或將迎來突破。2012年4月26日,在北京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分組會議上,常委會組成人員二次審議了《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草案總則第五條中明確規定:國家建立統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臺,實現有關管理部門信息共享。
只罰款是不夠的
在行政長效管理機制建立的同時,法治體系跟進也極為迫切。
1985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了《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1986年至今,除了實施細則在1994年和2010年做了少許修訂之外,變動不大。業界人士普遍認為,26年前定的處罰標準,今天顯得“過輕”,當時預見的移民問題,如今已無法適應現實。
例如,目前《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規定:“對違反本實施細則第十六、十九、二十條規定,非法居留的外國人,可以處警告或者每非法居留1日,處500元罰款,總額不超過5000元,或者處3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情節嚴重的,并處限期出境。”
由此,修法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最近二次審議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是對1985年制定的《中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1986年制定的兩法實施細則以及1995年制定的《出入境邊防檢查條例》的綜合。
關于罰款額度,草案二次審議時,全國人大法律委建議在法律責任中對非法出入境或者協助他人非法出入境,容留、藏匿非法入境的外國人,非法介紹、聘用外國人等行為的罰款數額予以適當提高,并對單位違法相應加大處罰力度。
“對協助他人非法出入境的要加重懲處力度,包括為外國人出具邀請函件或其他申請材料的,收容、藏匿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外國人的,都要重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祖沛在分組審議草案時說,如果按現在草案的規定,對個人罰款2000元,對單位罰款1萬元,“很難起到警誡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侯建國認為,限期離境和遣返也是對外國人處罰方式中重要的一款。李祖沛還建議:“對情節嚴重的行政拘留,加上限期離境和遣返。性質嚴重的,還可以規定幾年內不得入境。”
更新處罰標準和方式之外,《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二審稿也將明確外國人的非法就業問題。法律委建議將草案有關規定修改為,外國人未按照規定取得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證件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屬于非法就業。
此外,移民法學者劉國福認為我國法律還應建立普通簽證擔保制度,豐富處罰“三非”外國人的途徑。“普通簽證擔保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國打擊‘三非’的一項重要制度,無論是傳統移民國家還是歐洲國家的移民法,都設立了不同種類的親屬和用人單位提名/擔保簽證。”
劉國福還認為,應適當放開外國留學生在讀期間和畢業后在中國的就業。“我國目前不允許外國留學生在讀期間和畢業后在中國就業。草案的第二次審議稿也只是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建立外國留學生勤工助學管理制度,對外國留學生勤工助學的崗位范圍和時限作出規定。使用‘勤工助學’,意味著不能規范助學類以外的工作行為,實踐中,完全杜絕留學生從事非助學類工作幾乎不可能。”劉國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