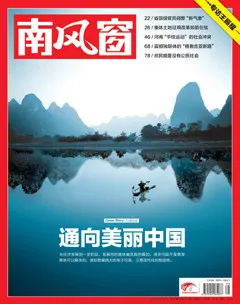期待教育平權的新開始
對于政府來說,今年面臨的最大一次“挑戰”,恐怕就是在2012年的日歷翻過去前,各地關于異地高考的實施方案能否出來。這是給出了“政治承諾”的。
時間已經不多,很多省市還沒有看到動作,使得教育部急了,前段時間通過新華社提出“要集中力量,打好這一硬仗”。
同時,一位負責人還提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在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實際行動中,教育部將會同發改委、公安部和人社部對各省(區、市)開展專項督查,分赴京滬粵等地督促指導落實方案。
傳遞的信號,已經清楚不過。
在學習十八大精神的語境下,就權力結構而言,相信各省市的教育廳都會對教育部有個“交代”。背后的地方政府的利益考量,以及老百姓不一定看得懂的博弈,大抵也會照顧到國家層面的信用和政治壓力。
問題只在于,在矛盾最集中的少數省市,關于異地高考的實施方案就算出來,其功能可能也只局限于有個“交代”,和以前比,有一點“歷史性突破”而已。各種門檻的設定毫無疑問,教育的社會排斥籬笆不可能大范圍撤離。
這暴露的是,在教育平權上,一些地方顯然并沒有準備好。像多地在關于2013年高考報名的通知上,就沒有把非戶籍人口納入。
我們擔心的是:當各地關于異地高考的方案全部出來后,突破了教育的社會排斥的人,對應的往往是他的社會身份,而非他的公民權利。這是兩套不同的邏輯。
在這里,最根本的問題是,從教育部門到在既有不平等的教育資源分配格局中獲益的公民,在對教育平權這一概念的理解和認同上,用一句有中國特色的話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權力自我定位的偏差,和利益結構形成了某種天然的同盟,難以打破。
中央政府部門推進各地出臺異地高考方案的姿態是值得肯定的。遺憾的是,在執行過程中,給人的感覺是,異地高考是各地的事。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背后是公民和國家的政治契約,對應的是國家的義務,應是代表國家的教育主管部門,通過制度、政策、教育資源的平等分配等來兌現。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戶籍這一因素對公民平等教育權進行限制。
十八大報告對“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強調,其實也是對國家義務的自我闡釋。邏輯上它引向的,應該是教育主管部門對于自己該做什么的角色自位。2013年,這應該成為思考和行動的一個新起點。
可以理解各地在成為“解決問題”的主體時的苦衷。同樣也可以理解很多從既有的教育資源不平等分配格局中獲益的公民對于“特權”的本能捍衛,以及對于想要獲得平等受教育權的公民的不滿。不同的教育獲得處境,往往對應著不同的人生前景。
但是在這里,對于公民來說,存在著一個理性的質疑:你的“特權”和他人的沒有權利,都是由一個權力—利益體系進行分配的,那么,這種“特權”在道德上是應得的嗎?他人沒有權利,在道德上是他活該嗎?
在這個理性的質疑背后,還有一個悖論:在A事件中,如果一個人把他的“特權”和他人沒有權利都視為是正當的,那么,他如何防止在B事件上,自己不成為權利受損者?如果這樣,他如何合理地、邏輯自洽地為自己追求權利的行為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