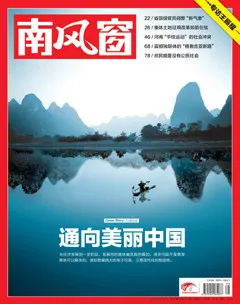王振耀:“院長比司長影響大多了”


北京初冬的清晨,空氣中已經(jīng)多了一份濃重的凜冽。王振耀從位于北京師范大學(xué)西門的家走到京師大廈,正好是與記者約好的時間,8點(diǎn)整,幾乎分毫不差。一落座,他便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院長比司長影響力大多了。”王振耀不止一次這樣說。2010年6月,他棄官治學(xué),再也不用擔(dān)心,自己推動的事情越過職權(quán)范圍,被人過度揣測意圖或無限解讀。他辦各種各樣的論壇,大講公益,甚至提倡讓億萬富翁每年捐款100萬。這如果在司長的位子上,恐怕想都不敢想。
而他也坦言,讓他特別振奮的壹基金轉(zhuǎn)型,也有賴于自己幾十年的從政經(jīng)歷和影響力,是有別于他人的獨(dú)特優(yōu)勢。官與學(xué)的氣質(zhì),在王振耀身上依然交錯在一起,亦如雙生花。
王振耀是主動走出體制的為數(shù)不多的官員,他對體制內(nèi)原則的“解密”或許滿足了公眾對政治去神秘化的欲望。
“低薪高薪都不是公務(wù)員腐敗的理由,只有好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壞官的出現(xiàn)。如果把道德與法律對立起來,甚至凌駕于法律之上,那樣的官德,如何靠得住?”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未必沒道理。“如果我們的文化對每個人的日常需求不給予一定的重視,那么我們的一些政策就難免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有些高尚的口號可能不近人情,甚至違反人性。”
強(qiáng)烈的時間觀念,話語間的干脆利落,思維的敏捷深刻,無不昭示著王振耀在官學(xué)之間的游刃有余。出仕途,入學(xué)界,他認(rèn)為這兩種身份的轉(zhuǎn)變?nèi)缤D(zhuǎn)門一樣自然,而倘若無法能上能下,才不正常。
“慈善一定姓民”
王振耀辭官后,出任北京師范大學(xué)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他失去了公車,損失了正司級所享受的醫(yī)療待遇“藍(lán)卡”,與之作為“交換”的則是二級教授的頭銜。“沒有優(yōu)厚的福利待遇,那些教授還不是一樣活”,在56歲時,他換了個活法。
有人說他“下海”了,亦有人說他“上岸”了。對王振耀來說,大多數(shù)時間就是在幫人家“出主意,想辦法”,只要慈善領(lǐng)域有需求,他就一刻停不下來。只不過這一次是從民間出發(fā)。
在王振耀當(dāng)院長兩年多的時間里,壹基金轉(zhuǎn)型讓他特別振奮。在中國做慈善,民間組織多受身份之困。它需要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又要尋找政府機(jī)關(guān)或黨政部門做主管單位。李連杰的壹基金就一度因“身份不明”而遭到即將中斷的危險。后來,在王振耀的穿針引線下,壹基金終于在深圳拿到了渴求已久的“身份證”。而壹基金與深圳市民政局的合作過程,被王振耀用“巧合”一言蔽之。
壹基金的轉(zhuǎn)型給了全社會一個積極信號,民間組織可以公開面向社會募款。王振耀認(rèn)為,此舉越過了長久以來難以逾越的邊界。但他也坦言,他橫跨政學(xué)兩界的特殊身份,也是促成此事的關(guān)竅。或許從這個意義上說,壹基金的轉(zhuǎn)型僅僅是一個個案,法律不改,民間慈善組織的困局仍舊無法解除。
慈善組織的亦官亦民,引發(fā)了慈善究竟姓官還是姓民之爭。“慈善一定姓民,”王振耀仍堅定地認(rèn)為,“所謂民,既不是與官截然對立,又不能尾隨政府,而應(yīng)該引導(dǎo)政府。”
2011年公益慈善界發(fā)生的大事頗多,王振耀從中看出了慈善回歸民間的大玄機(jī)。
“郭美美事件”在網(wǎng)絡(luò)上被披露并迅速形成輿論,在慈善領(lǐng)域,民間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已成為國家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這讓這位老官員感慨不已:“社會評價標(biāo)準(zhǔn)悄悄地發(fā)生了轉(zhuǎn)移。至少在慈善領(lǐng)域,各級政府對民意的敬畏已成慣例。”
普通公民參與慈善的浪潮波瀾壯闊,甚至開始自下而上影響制度的建立。王振耀說:“鄧飛倡導(dǎo)的免費(fèi)午餐行動,就讓政府也參與了進(jìn)來,160億元學(xué)生營養(yǎng)補(bǔ)助由中央財政負(fù)擔(dān)。這是中國慈善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前民間難以占主導(dǎo),總是抱有圣上英明、皇恩浩蕩的陳腐觀念。近年來,慈善越來越歸于本真,民間完全可以引領(lǐng)政府,只不過這個過程仍然漫長,最需要的還是行動者。
而王振耀卻不喜歡這些行動者以“草根”組織自居。“我當(dāng)司長時,一聽草根組織,第一反應(yīng)就是你沒錢,或許還跟政府有點(diǎn)摩擦。”這一稱謂也許能喚起民間的身份認(rèn)同,但在與政府公關(guān)時卻是極為失敗的形象設(shè)計。歸根結(jié)底,草根與民間仍存在距離,它亟待補(bǔ)上“專業(yè)化”這一課。
有人說王振耀“替窮人說話”,又“替富人說話”。他也因此遭受爭議。“首善”陳光標(biāo)事件后,他一句“原諒有缺點(diǎn)的企業(yè)家”,被無數(shù)網(wǎng)友斥責(zé)為“替富人開脫”;倡議5.5萬個億萬富翁應(yīng)該把每年的捐款定為100萬,引來了“異想天開”的質(zhì)疑聲。
王振耀無暇理會爭議,他憂慮的是,富人的善款如何敲開慈善的大門。
“兩把稅把多少善款生生擋在門外啊!”王振耀緊皺眉頭說道,曹德旺以股票形式捐贈,市值超35億,按照現(xiàn)行制度征稅,須繳納6億左右稅款。對善款征重稅,無疑讓全球通用的股票捐贈在中國遇到了大門檻。一個曹德旺的問題不解決,幾千億的股票捐贈就無法用于慈善。
此外,基金會也要如企業(yè)一樣,每年繳納25%的所得稅。王振耀追問道,對用于社會的善款征稅,那么是否也要對國家的財政收入收稅呢?他認(rèn)為,對前者征稅和對后者收稅一樣荒誕。
過去我們使出各種絆子抑制民營企業(yè),如今同樣的邏輯對準(zhǔn)了民間慈善機(jī)構(gòu),這是個心結(jié)。王振耀說,他們研究院現(xiàn)在就是要幫人們解開這個結(jié),要說清楚太難了,但還得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離開官位看官位
20年的仕途生涯,在王振耀看來,還是干出了點(diǎn)名堂的:推動基層民主選舉制度的誕生和發(fā)展,讓“海選”成為9億農(nóng)民的共識;建立四級災(zāi)害應(yīng)急管理體系,汶川大地震檢驗(yàn)了其效果;把各地民政官員“關(guān)”在京城,落實(shí)低保金;建立涵蓋200余項標(biāo)準(zhǔn)的孤兒最低養(yǎng)育制度。
在任時,王振耀做事的邏輯與其他官員有些迥異,難免讓人在背后說他“另類”。無論他如何不按牌理出牌,也只是變動了行事方法而已。至于規(guī)則,始終未曾改變。而機(jī)關(guān)規(guī)則,既是媒體喜歡追逐談?wù)摰慕裹c(diǎn),又是普通公眾樂于窺探的“機(jī)密”。官轉(zhuǎn)民的王振耀,受一名圖書編輯邀約,索性執(zhí)筆再次回望官場,細(xì)說規(guī)則。
在王振耀擔(dān)任民政部救災(zāi)救濟(jì)司司長期間,他發(fā)現(xiàn),按照災(zāi)情大小,劃分災(zāi)害等級,實(shí)行災(zāi)害分級管理制度,已經(jīng)提了10多年之久,卻一直沒什么地方執(zhí)行。2003年“非典”期間,他和同事發(fā)現(xiàn),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國家實(shí)行該制度。原來“這不是下面對付上面,而是上面的制度設(shè)計出了問題”。
下面抵制或拖延執(zhí)行上面政策的事情,他也不是頭一遭碰到。“說到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真正病灶,就是我國缺乏公開透明的利益表達(dá)機(jī)制,不認(rèn)為地方利益存在著正當(dāng)性,更不習(xí)慣于在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間進(jìn)行公開的談判。”王振耀說。
而在機(jī)關(guān)內(nèi)部,靠投票選先進(jìn)的規(guī)則,也同樣被王振耀認(rèn)為“極為不妥”。這樣評選的依據(jù)可能是人際關(guān)系,而非業(yè)務(wù)水平。王振耀擔(dān)任司長之時,所倡導(dǎo)的考核辦法是將個人一年的工作評價,劃分為10多個項目,然后來進(jìn)行分別評價,最后綜合計算總分。當(dāng)然,領(lǐng)導(dǎo)亦會參與打分,最后司長還會說一些決定性意見,考評委員會是要尊重的。這樣,承擔(dān)了很多工作但原來票數(shù)不多的人總分就上去了。
王振耀對評選先進(jìn)方法的革新并非有意培養(yǎng)“自己人”。由于機(jī)關(guān)的政治化傾向,衍生出了一個普遍的用人規(guī)則,即誰是誰的人,就要聽誰的話。同樣在王振耀從政期間,也有人規(guī)勸他注意用自己人。“誰是自己人?”他得出的結(jié)論則是,職位或崗位的關(guān)系構(gòu)成,異化為“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這絕對是政府機(jī)關(guān)建設(shè)的一大弊端。
與用人同樣敏感的恐怕就是資源分配了,常年擔(dān)任“賑災(zāi)大員”的王振耀深知,政府資源分配在各國同屬敏感問題,只是一些國家的解決方式是公開討論,而我國的現(xiàn)狀則是,行政部門獨(dú)自解決本需社會公開討論的問題,這種體制性的弊端會帶來一系列副作用。“官員也不是神,都有七情六欲,手一偏,心一動,可能就影響到了大事。”王振耀認(rèn)為,推動體制改良才是規(guī)避敏感的良方,但如何具體界定敏感崗位又是一道新難題。
盡管體制內(nèi)外的規(guī)則林林總總,但在已經(jīng)跳出體制的王振耀看來,這兩者有著質(zhì)的區(qū)別。體制外的規(guī)則,也就是社會大眾的規(guī)則,相對公開直接,利益關(guān)系比較明確。“而在體制內(nèi),事實(shí)上是存在雙重規(guī)則的。”王振耀說,一是原則性規(guī)則,另一個則是潛規(guī)則。他深知自己曾被稱為“學(xué)者型官員”,是因?yàn)樗皇煜す賵鰸撘?guī)則之故。
“那些潛規(guī)則不是不可學(xué),而是不能學(xué),因?yàn)閷W(xué)會那個,就會失掉自身,就會將一生的安身立命之本丟掉。”不過王振耀眼中的官場也不是那么黑暗,他在任期間有所作為也是因?yàn)榈玫搅撕芏嗳说闹С趾蛶椭Kf絕大多數(shù)人還是有正氣有理想的,只是有時候體制讓他們有些無奈。
兩大命題
王振耀身上有著典型“77級”的特點(diǎn),喜歡做理論思考,習(xí)慣于不斷追問和反思。王振耀是地道的農(nóng)家子弟,1954年出生于河南省魯山縣的一個村莊。他那一代人幾乎經(jīng)歷了新政權(quán)締造初期的種種苦難和動蕩,養(yǎng)成了他們能忍也求變的品格。
他們那一代人在火紅的年代中,釋放和燃燒著青春,保證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解放全世界2/3的受苦人民,這樣的理想之于他們,那是真真切切的偉大事業(yè)。如果有人“唱反調(diào)”,就要批判、打倒。“當(dāng)時的思維模式是,我們認(rèn)為最好的事情就不允許別人說不好。”王振耀說。
“文革”之后對社會種種問題的追問,讓他們驚覺自己懷揣美好愿望卻做了多么荒唐的事情,至今王振耀還在追問:“把中國折騰成那個樣子,難道我們這一代就沒有責(zé)任嗎?”
他大膽提出了一個命題:轟轟烈烈,原地踏步。這也是王振耀為“中國幾千年為什么老走不出去”找到的癥結(jié)之一。“我們的思維方式就是每一次都想徹底解決問題,革命要徹底,消滅對手更要斬草除根。”王振耀在新書中也寫道,越是所謂的徹底,反而越是以新的方式來恢復(fù)更為陳舊的東西。他們這一代人就是典型,剛剛破除了帝王思想,又來一套“萬壽無疆”。良好的愿望和極端的行動是不行的,最終只有尊重每一個人,才能拿到大國的入場券。
王振耀提出的第二大命題是,知識生產(chǎn)方式轉(zhuǎn)型。他上學(xué)多,考試也多,有一次考試后,一位老教授說,標(biāo)準(zhǔn)答案有5條,他只答對了4條,最后一條是自己創(chuàng)造性的答案。雖然很有創(chuàng)意,但是與標(biāo)準(zhǔn)答案不符,必須扣分。
“這就是我們的學(xué)習(xí)方式,以為背好了標(biāo)準(zhǔn)答案就能直接參與社會管理。”王振耀說,社會急速前進(jìn),對靜態(tài)知識的掌握無疑是在刻舟求劍。郎咸平曾提到,他的助手基本都來自香港;很多外企在內(nèi)地最愁的是招不到熟練的管理者。
如同學(xué)習(xí)方式一樣,研究方式也難逃這個“怪圈”。研究者比寫文章,比對現(xiàn)實(shí)的理解,“意義”、“作用”滿篇皆是,而對問題是什么,如何分類,怎樣解決卻少著筆墨。
“假設(shè)那些為國家設(shè)計宏觀轉(zhuǎn)型的人,是在這種生產(chǎn)方式的固有思維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就不會設(shè)計方案,即便設(shè)計出來也多是在拽詞。”王振耀不無憂慮地說。
轉(zhuǎn)變知識生產(chǎn)方式,我們還忽視了一座“富礦”。王振耀深有感觸,他在哈佛大學(xué)的一位老師曾當(dāng)過18年參議員,而這種從政又治學(xué)的人在美國的大學(xué)里比比皆是。而我們的退休官員,同樣是經(jīng)驗(yàn)豐富的實(shí)踐者,這些財富通常被浪費(fèi)掉了。
都說“旋轉(zhuǎn)門”在中國很難,王振耀則不太認(rèn)同。美國有些兼職教授本身就是官員,他們就是講自己領(lǐng)域中的一點(diǎn)心得體會,而不一定都要去做理論文章。“知識界要先打開封閉的大門,肯定實(shí)踐的心得也是知識,這扇門旋轉(zhuǎn)起來自然就容易了。”</